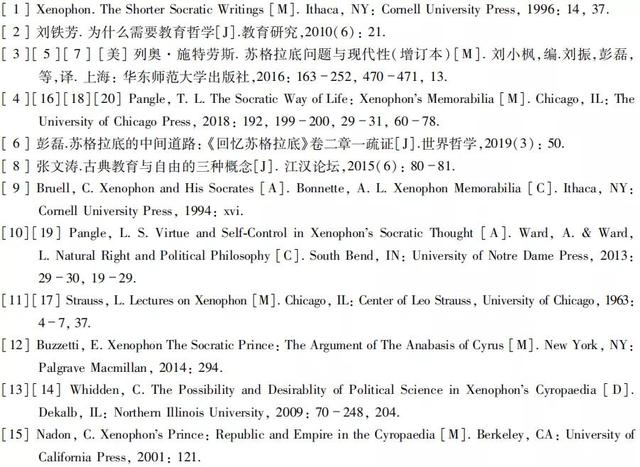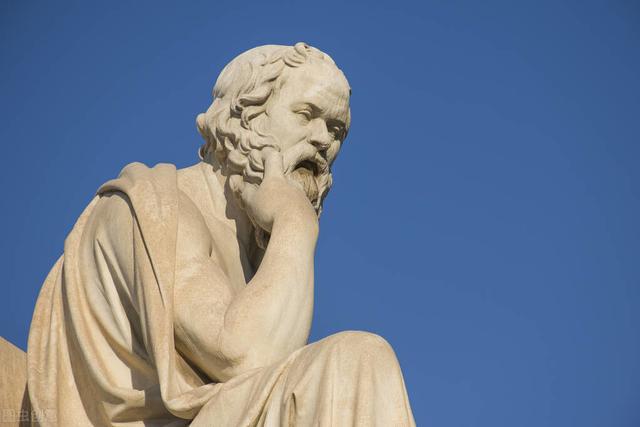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杨志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申辩》中,根据其笔下的赫尔莫艮尼斯(Hermogenes)的回忆,当着雅典民众法庭和众多听众的面,苏格拉底说自己是教育方面的专家,还说教育是“对人类而言最大的善”。[1] 苏格拉底的教育不仅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获——两位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是西方一流的思想家,也给他惹来了大麻烦,甚至最终导致雅典城邦判定他犯下了败坏青年一罪。苏格拉底到底在教育什么,他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竟然使得雅典民众法庭要判定他败坏青年,而又同时让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如此受益和如此仰慕他?
教育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教育的目的以及何为最好的教育,若缺少对教育目的的清醒认识,各种教育手段都难免会失去其灵魂。[2] 反思苏格拉底这位人类历史上极其卓越的教育者的教育内容尤其是其背后的教育目的,或许有助于推进当下关于教育哲学的思考。由于苏格拉底本人述而不作,要认识苏格拉底的教育哲学,主要依靠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相关著作。这不仅仅是指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比如如何理解苏格拉底所引出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以及政治和哲学这两种生活方式所牵引出的何为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如何理解什么是德性这个典型的苏格拉底问题。不难看出,苏格拉底问题难免会涉及教育的目的以及何种教育最佳的问题,因为思考教育的目的难以避开何为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个核心问题。[3] 相较于柏拉图的众多对话,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以下简称“《回忆》”)在适当篇幅内记叙了苏格拉底与相当数量的对话者关于许多内容的探讨,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展示,是理解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教育哲学的重要切入口。
《回忆》涉及苏格拉底的教育内容、教育目的与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这些核心问题。在《回忆》中的苏格拉底的教育里,自制教育引人注目,这种品质在苏格拉底看来是德性(aretē)的基础,也是其教育的重要基础。同时这种品质适用于苏格拉底所有层次的同伴,涉及面广,是讨论苏格拉底教育哲学的重要切入点。
拙文基于对色诺芬的《回忆》和其他重要著作的分析,选取自制教育作为切入点,以自制教育的内容尤其是其目的为例,初步思考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尝试根据《回忆》的具体语境相对全面地分析自制和节制的定义及两者的关系,进而分析自制教育本身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两方面分析自制教育背后的教育目的,从而具体展现苏格拉底的教育哲学及其生活方式,希望有助于推进关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教育哲学的研究,抛砖引玉。
01
《回忆》的谋篇与教育方式
色诺芬的写作极其讲究修辞,而且《回忆》有其表面上明确的写作目的,在进行主题分析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回忆》的谋篇和教育方式。《回忆》全书四卷共三十九章,前两章意在反驳苏格拉底遭受的两项指控,即“苏格拉底行了不义,在于他不信城邦所信的诸神,还引进其他新的精灵;他行了不义,也在于他败坏青年”(《回忆》1.1.1)。苏格拉底的“不义”可归结为他败坏青年,因为如果他不与其他人打交道,即便内心不信雅典城邦神,他也不会遭到起诉。他必须与青年打交道,即他必须教育青年,无论是通过言辞还是通过行动,才有可能败坏青年。随后三十七章回忆苏格拉底如何通过行为和交谈来进行教育,从而施益而非伤害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从正面反驳雅典城邦的指控。这一谋篇提醒我们在分析《回忆》中有关苏格拉底的相关看法时,有必要注意色诺芬明面上的辩护意图,以及他借此引导我们思考的一些引而不发的重要问题。[4]
由于《回忆》里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天性各异,对话能力不同,其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可能会随之变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在面对不同的对话者就同一个问题所说的话可能会有出入或相互补充。按照色诺芬的说法,苏格拉底的对话分两种类型:当对话者就某事进行反驳而没有给出清晰的论证时,苏格拉底便会把整个论证拉回到其论证前提,从而在获得对话者同意的基础上,让真理自身向反驳者显明;当对话者只是倾听而不进行反驳时,他便根据最受认同的意见来进行对话,因为他认为这是安全的做法(4.6.13-15)。[5]
除了要考虑到直接的对话者之外,苏格拉底对旁观者的旁敲侧击的教育方式同样不可忽视。由于他的很多对话都有旁观者,色诺芬明确说过自己至少亲自旁听过其中的几次对话,因而需要考虑如下这种可能性: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回答不仅是针对直接对话者,甚至是针对当时的旁观者,更是针对色诺芬著作的后世读者的,《回忆》的写作本身就预设了读者的参与。也就是说,读者要想象自己就在雅典的市场上或雅典的其他地方围观旁听苏格拉底与某个人的对话。这种旁敲侧击的教育方法和上文提及的两种对话差异,提醒我们在思考苏格拉底的对话时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卷二第一章中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的对话很有可能针对的是阿里斯提普斯本人以外的听众。[6]
02
自制的含义与自制教育的潜在问题
每一个读过《回忆》的读者难免会对苏格拉底本人近乎禁欲的自制印象深刻。色诺芬在为苏格拉底辩护时说,他是在性乐和食欲方面最自制的人,最能忍耐严寒酷暑和辛苦劳动,他还教育自己克制需要,以至于他拥有的很少,却非常容易满足(1.2.1)。色诺芬还在多处提到他的自制,也多次展示他通过言辞和他的生活方式以身作则地教育自己的同伴要自制,从而让他们受益。色诺芬还说,苏格拉底本人在行为上比在言辞上更自制(1.5.6)。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自制,这种自制的含义是什么?
(一)自制的含义及其与节制的关系
根据自制在《回忆》出现的语境来看,自制的含义大致如下:在吃喝、性乐和睡觉等身体快乐和金钱快乐面前可以克制自己,同时可以忍受身体方面的辛劳和痛苦。简而言之,就苏格拉底进行自制教育的语境而言,自制一般是对身体方面的快乐和痛苦的恰当回应,尤其侧重面对与身体有关的快乐的恰当回应。但自制并不等于禁欲,就连苏格拉底本人也并非禁欲主义者(如1.3.5,1.6.5,4.5.9),虽然苏格拉底身上的自制近乎禁欲,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提倡禁欲,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处用法比较特别,即色诺芬在盛赞苏格拉底时说,他“如此自制(enkratēs),从而永远不会选择更快乐的东西来代替更好的东西”(4.8.11)。就此例而言,在这个与苏格拉底的自制教育无关的语境里,苏格拉底本人的哲人式的自制似乎并不仅仅局限于身体层面的快乐,更像是指一种面对所有类型的快乐时的品质。在《回忆》里,需要区分苏格拉底哲人式的近乎禁欲的自制与他在自制教育中教育同伴去践行的自制,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后者。
苏格拉底有时把自制(enkrateia)和节制(sophrosunē)当作几乎同义的语词使用(如3.9.4,1.2.23),的确,自制与节制之间有一定的紧密联系,这两个语词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同义使用(这时的节制一般意为克制身体欲望的自制),但在色诺芬的整体著作里,这两种品质远非一致,节制与实践智慧不可分,比自制的等级更高。[7] 一般而言,自制在《回忆》中的含义比节制更窄。根据节制在《回忆》的使用情况来看,节制大致有如下几种用法:对于诸神的节制,即不做和不说不虔敬的事情,尊重传统宗教,但似乎不包括不想;节制包含了自制和判断力,这种品质需要持续地习练,容易因受身体快乐影响而消逝;节制与肆心(hubris)相对;节制与自我认识有关,坦诚地承认自己的无知、需求和局限,因此避免自我吹嘘(1.7整章的主题),而缺乏自我认识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疯癫,这并非通常理解的疯癫(3.9.6);节制与实践智慧不可分离(3.9.4)。因此,相对节制而言,自制是更基础的伦理品质,自制是节制的基础。由此可见,在苏格拉底的自制教育里,自制这种品质本身并不复杂。我们在此更需关注的是自制教育的潜在问题和教育目的。
在苏格拉底的自制教育里,“自制是德性的基础”(1.5.4),这话一语道破自制在苏格拉底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用卷四的主要对话者欧蒂得莫斯(Euthydemus)的话来说,“那些被身体快乐征服的人没有任何德性可言”(4.5.11)。必须注意的是,色诺芬及其笔下的苏格拉底从未说过自制本身是一种德性,它顶多算得上是一种既美又好的所有物(1.5.1),即灵魂层面的财富。苏格拉底认为,自制本身不高贵,但对于要行高贵之事的人而言,它是必需的也是好的。自制的这种含义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现实生活尤其是当时有欲望自由倾向的雅典民主社会中[8],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制其实非常难以做到,苏格拉底近乎禁欲的自制更是让人惊叹。因此,在苏格拉底的同伴之间,在接受自制教育时,苏格拉底式的极端自制有成为德性或卓越本身的潜在危险。
(二)自制教育的潜在问题:自制的自足性
苏格拉底极端的自制太过耀眼,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能力之外,这已足以让他吸引别人的崇拜乃至模仿,甚至有可能使得一些追随者把这视作苏格拉底身上最大的财富,反而有可能忽视苏格拉底的自制及其自制教育背后的真正目的,如色诺芬笔下的安提斯忒内斯(Antisthenes)。从《回忆》(3.11.17)和色诺芬的《会饮》(1.3和4.44)等处可知,安氏是苏格拉底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非常穷,但此人在《会饮》中说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便是自己的财富——他灵魂中的财富(对勘《回忆》1.5.1的“所有物”),他从苏格拉底那获得的财富,即自制(《会饮》3.8,4.34-44)。能学习到近乎苏格拉底式的自制,这难道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吗?按照常人的标准,这的确非常难。但苏格拉底并不如此认为。在《会饮》里,苏格拉底听到安氏如此表露心声,随后找了个机会,语带玩笑地批评安氏“爱的是他[苏格拉底]美丽的身体而非灵魂”(《会饮》8.4-6)。色诺芬在《回忆》表明,苏格拉底在此所说的美丽身体其实是指他的自制。[9]
难道苏格拉底是在暗示安氏被他吸引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自制,而不是因为看到了他美丽的灵魂?但安氏曾明确表示,自制给他带来了最优雅的所有物即闲暇,从而他“能看那些最值得看的,听那些最值得听的,还能闲暇地与苏格拉底度过一天——这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会饮》4.44)。由此看来,安氏似乎并非完全是因为苏格拉底的自制而受到他的吸引。但为何苏格拉底还要说安氏爱的是他美丽的身体而非灵魂?这当然可能有玩笑的成分在,但如果只是将其当作玩笑看,或许我们会太过轻易地放过这个疑惑。
安氏的自制意在能够“闲暇地与苏格拉底度过一天”,难道这在苏格拉底看来还没有触及他的灵魂层面?难道安氏只是追求与苏格拉底这种极其自制的人的肉身在一起而已,也就是喜欢他那因极度自制而“美丽”的身体?考虑到苏格拉底圈子里每个人的天性差异和能力差异,苏格拉底很可能是在暗示,安氏虽然把“闲暇地与苏格拉底度过一天”视为最有价值,但自制的安氏并没有像苏格拉底本人那样真正地关切灵魂。也就是说,安氏的自制并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式的自制,两者的内在动因不同,即“灵魂”不同。在此,苏格拉底这个“身体—灵魂”的比喻极其形象。
安氏所代表的这类学生很可能更多看到的是苏格拉底的自制及其自制教育的表面,而没有抓到其内在核心,得其形而不得其意。苏格拉底开安氏的玩笑,很可能在暗示安氏为了自制而自制,也就是说,安氏的生活方式以极端自制为最高追求。苏格拉底很可能通过这句玩笑暗示安氏以及那晚参加会饮的其他听众(色诺芬也在场),虽然自制很重要,但自制本身并非苏格拉底式生活方式的目的,也并非苏格拉底自制教育的目的。
更危险的是,这种为了自制而自制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变成一种新的不节制而不自知,从而忽视了自制教育背后的目的,这也表明自制本身的不足。由于自制教育对于多数人而言的确不容易,当逐渐看到自己在自制教育上不断进步时,会切实体会到进步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快乐。进步所带来的快乐一方面会激励我们继续提高自己,但同时这种快乐值得警惕。苏格拉底在与智术师安提丰对话时说,当看到自己在自己选择的任何一种追求上“高贵地进步着”时,最大的快乐就会出现(1.6.8)。此外,苏格拉底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说,“那些最好地关切如何变得尽可能好的人活得最好,而且那些最能察觉到自己正在变得更好的人活得最快乐”(4.8.6),而色诺芬在其“苏格拉底颂词”(4.8.11)中大力赞扬苏格拉底是如此自制,因为他“永远不会选择更快乐的东西来代替更好的东西”。由此可见,活得最好和活得最快乐之间的鸿沟甚至在苏格拉底的生活中可能都没有完全弥合,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以及苏格拉底的绝大多数同伴而言,这种鸿沟必然更大,因为在我们能够容易或不那么难就可以获得进步的那些追求上,我们不一定能从中获得对我们灵魂最好的东西。[10] 就自制教育方面的进步而言,它会给我们带来进步的快乐,但进步者却容易迷失在自制本身而不自知,把自制视为最高的德性成就,自以为已经在德性上有所成就,从而忽视了自制背后更高的德性追求,即可能会成为苏格拉底所说的“只爱其身体而不爱其灵魂”的人。
因此,必须追问苏格拉底为什么如此重视自制教育。虽然苏格拉底在教育自制时经常提到所谓的“自制的快乐经济学”,即自制是为了从最简单的欲望满足中获得最大的享受,或者说只有等到欲望最强烈时,才能从欲望满足中获得最大的快乐(如1.6.5-8,4.5.9),但他教育同伴要自制,除了规劝那些正在受到身体欲望奴役的同伴之外,最主要还是为了让他们摆脱身体欲望的奴役,更自由地去追求比身体快乐更有益、更高贵的东西,关注如何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让自己变得更好,而非让他们为了自制而自制。
03
自制教育的目的:好的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变得更好,那么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按照色诺芬全部著作的内容,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分为两大类:政治与哲学——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代表政治生活一端,苏格拉底则代表哲学生活一端。[11] 色诺芬的人生经历包括了这两类更重要的事情,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能够以政治统治者的身份深入体验现实政治生活(见《居鲁士上行记》第三卷至全书结尾和《希腊志》全书),又有幸接受过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教育。[12]
(一)自制、政治教育与好的政治生活
苏格拉底在阐明自制的重要性时,时常会提到自制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如1.5.1,1.6.9,2.1.1-7,4.5.10),以此教育当时正在对话或旁听的有政治抱负的同伴,比如阿尔喀比亚德(1.2.12-16)、欧蒂得莫斯(4.2.11)以及我们的作者色诺芬。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自制的人才有可能学习和关切既美又好的事情,这些事情使得人可以高贵地管理自己的身体,高贵地齐家,变得有益于朋友和城邦并且征服敌人(4.5.10),其中后两者更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与阿里斯提普斯讨论进行政治统治的资格时(2.1.1-7),苏格拉底以公民—哲人的身份向在场旁听的同伴表明,使人有能力进行统治的政治教育必须包括自制教育,即在吃喝、睡眠、性乐、吃苦耐劳和耐热耐冷方面的自制训练。这种强调自制的公民教育见于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第2章)与《居鲁士的教育》(1.2.8),当时的希腊强邦斯巴达的政治教育便以此为特色。
虽然自制并不是好的政治教育的充分条件,但色诺芬在谈论极有政治野心的阿尔喀比亚德时说,“各种快乐和灵魂一起在同一个身体里生长,它们劝说灵魂不要节制,而是尽可能快地满足它们自己和身体”(1.2.23),由于身体欲望本能强大而顽固,因此需要自制甚至是持续不断的自制来抵抗这种强大的欲望诱惑。色诺芬这句关于人性的判断所出现的语境暗示,自制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而言更为重要,因为相较于普通公民以及有哲学爱欲的人,政治领域的人会面临更多的欲望诱惑。对于好的政治教育而言,自制可以时刻提醒政治受教育者在政治生活中要持续警惕各种身体欲望和各种物质带来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在色诺芬看来,由于人的德性并非一旦获得就可以一直有效,各种欲望的侵蚀容易松动德性,在此意义上,自制的训练意在巩固人的德性,同时提醒政治受教育者留意自身强烈的堕落倾向(1.2.22),以更清醒的态度去监督自身。
好的政治教育需要自制,真正好的政治生活也离不开自制,由于自制主要针对各种身体方面的快乐,因此好的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点在于它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这些快乐。由于《回忆》的题材限制,故在这方面没有给出相应的例子,不妨看看色诺芬其他著作的相关说法,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制对于好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在色诺芬的所有著作里,除了苏格拉底之外,还有两个人在面对身体欲望方面有着同样惊人的自制品质,即《居鲁士的教育》的主人公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以及《希腊志》里的忒萨利僭主伊阿宋(Jason,见《希腊志》6.1.6和6.1.16)。居鲁士从小在波斯共和国接受极其严格的自制教育,尤其是饮食方面的自制教育(《居鲁士的教育》1.2.8),而且他在性乐面前极其自制,即使他随时可以拥有“全亚细亚最美的女人”(《居鲁士的教育》5.1.2-17)。然而,正是这个有着惊人自制品质的统治者在第一次带兵出征前肆无忌惮地向手下一千名接受过自制教育的波斯贵族发表颠覆传统波斯德性观的演说,其中的一句话值得引用:“我认为,人践行任何德性(aretē),不是为了让那些变好的人所拥有的东西不比那些无价值的人更多。毋宁说,那些避开眼前快乐的人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永远不享受快乐,而是凭着当下的自制(enkrateia),准备在未来享受[比现在]多得多的快乐……为自己和共同体获得大量的财富、幸福和巨大的荣誉。”(1.5.8-9)这种享乐主义底色的自制教育诚然有利于居鲁士在创建帝国的过程中有效调动手下的积极性,但同时给居鲁士建立帝国之后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既然帝国已经建立,居鲁士就得兑现之前的享乐承诺,也为居鲁士死后波斯帝国的急剧堕落埋下了最初的祸根。[13] 居鲁士的政治统治向其臣民承诺的实质上是普通人(anthropos)而非男子汉(aner)的幸福,即身体快乐、物质利益、安全和虚假的荣誉,在色诺芬看来,这是一种羊群式的幸福(《居鲁士的教育》8.2.14)。[14][15]
这种为了身体欲望享乐而自制的自制教育并不是真正的自制教育,如果政治生活所追求的目的最终不外乎是更大程度的身体欲望和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这种政治生活即便拥有自制的外表,也没有自制的实质,只是走了更远的路,以求更大程度地满足最初的身体欲望。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好的政治生活需要真正的自制作为其高贵政治追求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政治共同体要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毋宁说,好的政治共同体意在引导人们朝向比欲求身体快乐更好的追求。
(二)自制作为哲学生活的基础
令我们惊讶的是,苏格拉底还提出了自制教育的另一层目的:自制的人才有可能考察何为好与坏的事物,从而根据种类在言辞和行为上选择好而避免坏(4.5.11)。这是苏格拉底与没有哲学爱欲的欧蒂得莫斯谈论自制之必要性时所说的最后一个论点。能分辨好和坏的事物而不只是寻求最快乐的事物,是使得人有别于那些毫无思想的畜群的因素。这看起来与哲学教育没有关系,因为日常生活一样涉及基于意见的好坏区分,但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恰恰是把好等同于快乐,这种好坏与快乐的区分需要超越日常意见。更值得注意的是,紧跟这句话之后,色诺芬突然以自己的名义转到关于苏格拉底的问答式论辩术(dialegesthai)的解释:一群人聚在一起集体思索,根据种类区分(dialegein)事物(4.5.12)。这种对dialegesthai的解释是色诺芬的原创,不见于之前的作家笔下。这种解释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色诺芬在《回忆》卷一第一章所说的“苏格拉底本人总是就属人事物进行交谈,考察什么虔敬,什么不虔敬,什么高贵,什么可耻,什么正义,什么不正义,什么是节制,什么是疯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城邦,什么是治邦者,什么是对人的统治,什么是高明的统治者,以及其他事物”(1.1.16)。这两处一起暗示出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的理解。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式论辩术或者说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教育便成了自制教育的最高目的,这在之前关于自制教育的讨论中都没有出现过。[16]
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教育为何需要自制?在接受哲学教育之前,如果受到身体的各种欲望的干扰,则无法专注地进入自由思考。[17] 此外,这种哲学教育一开始会质疑和反思日常意见,由此才有可能持续根据种类深入区分和思考各类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摆脱意见是相对简单的,而且给人一种新颖的快乐。但随着思考的深入,思考者需要持续高强度的自制和专注,以始终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以及在这些方面持续获得进步。此外,由于色诺芬并不赞同所谓的“德性就是知识”[18],也就是说,在人的灵魂所获得的理解达到极其清晰的程度之前,在人的灵魂所进行的精神习练足以深入灵魂从而克服身体的强大本能进而认为满足身体等方面的快乐成了累赘之前,哲学教育或许都需要持续的自制,以好的习惯来进一步维持巩固灵魂在哲学教育过程中逐渐取得的收获。就此而言,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涉及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这种生活方式转变的成果并非最终可以一锤定音,而是作为一种长期的身体和精神锤炼,长期对更高的快乐和善的追求。[19]另一方面,自制作为哲学教育的基础还可以削弱哲学教育可能的失败所造成的危害。对于日常意见的质疑和反思,如果缺少自制作为基础,一旦哲学教育半途而废,经过一定启蒙的人很有可能沦为那种鄙视和贬低日常伦理意见和规范的自以为是的享乐主义者。
最后,我们值得看看色诺芬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教育。色诺芬在《回忆》卷一第六章曾记叙苏格拉底与智术师安提丰的精彩对话,此处给我们了解苏格拉底真正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提示。在对话中,苏格拉底驳斥了安提丰认为哲学思考的幸福在于享受好的物质生活的粗俗哲学观和幸福观,这种智术式的哲学教育更多地沦为一种满足身体欲望的精致手段,甚至给身体欲望的享受披上了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高傲。而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之所以对这些快乐不感兴趣,是因为他有比这些更快乐、更持久有益而且使人更能够持续关切灵魂的快乐。在苏格拉底看来,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并且获得更好的朋友,这是比那些身体快乐都要大得多的快乐(1.6.9)。其他人的爱欲或是针对一匹好马、一条好狗或一只好鸟,而苏格拉底的爱欲是针对好的朋友,即有好天性的人(4.1.2)。“要是我拥有某种好,我就教给[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人——我认为他们在德性方面会从这些人那里受益。从前那些智慧的男人写在书中留下来的财富,我跟朋友们一起细细翻阅,要是我们看到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摘出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彼此成为朋友,那是巨大的收获。”(1.6.14)与同样有哲学追求的好天性的朋友一起快乐地阅读前人的经典,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与他们一起追问“什么是……”的问题,共同实践他所说的dialegesthai。在此过程中,这种小型的爱智慧共同体生活的友爱会给其中的受教育者提供自制方面的相互鼓励和相互扶持,这使得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教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20] 因此,色诺芬以自己的名义说,“我觉得他本人是幸福的,他还引领听众趋向了高贵和好。”(1.6.14)
这次交锋清楚地展现出苏格拉底并非禁欲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制而自制,他有自己的快乐。因此,苏格拉底大力规劝其同伴或学生自制的原因跟他本人自制的原因不一样,因为苏格拉底并不是故意避开身体快乐,它们对他而言已是累赘的烦心事,这也是苏格拉底的自制近乎禁欲最重要的原因。
04
结语
苏格拉底的自制教育作为其基础性的教育,不仅展现出苏格拉底在教育过程中如何进行旁敲侧击式的启发教育,还体现出苏格拉底在教育过程中极富弹性地教育不同层次的学生,努力引导他们朝向符合各自天性的美与好,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指向了苏格拉底教育哲学的核心——在不忘关切日常意见的同时,时刻关注人的灵魂的卓越。他不辞辛劳地引导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关切比身体欲望更高的追求,从而不仅造福受教育者自身,还造福政治共同体。对于当下的教育哲学思考而言,苏格拉底的自制教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制教育背后多层次的教育目的,重新反思流行的所谓成功学类型的自制教育。毕竟,自制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我们在欲望横流的现代社会进行自制教育时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