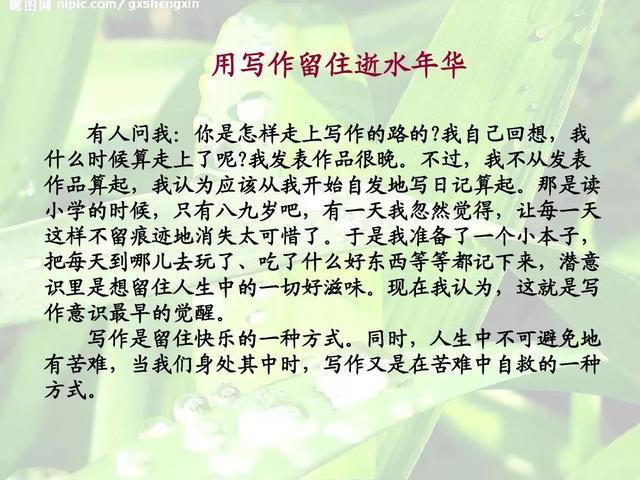
1
创造的快乐在于创造本身。对于我来说,写出好作品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至于这作品能否给我带来好名声或好收益,那只是枝节问题。再高的稿费也是会被消费掉的,可是,好作品本身是不会被消费掉的,一旦写成,它就永远存在,永远属于我了,成了我的快乐的不竭源泉。由于这个原因,我当然就不屑于仅仅为了名声和稿酬写作。我不会为了微小的快乐而舍弃我的最大的快乐。我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情做,活的有意义或者似乎有意义。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为了应付发表的需要而炮制虚假的文字,因而不再有暇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锤炼语言的功力。这就好象一个母亲忙于作为木请协会的成员抛头露面,因而不再有暇照料自己的孩子。我爱我自己的体悟远甚于爱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知识。我的追求:表达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体悟。
一流作家可能写出三流作品,三流作家却不可能写出一流作品。 可以剽窃词句和文章,但无法偷思想。一个思想,如果你不懂,无论你怎样抄袭那些用来表达它的词句,它仍然不属于你。当然,如果你真正懂,那么它的确也是属于你的,不存在剽窃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模仿苏格拉底的口气说话,却不可能靠模仿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倘若有一个人,他始终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思考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承认他是一个思想家,甚至就是苏格拉底,而不仅仅是一个模仿者。”
一种人用平淡朴实的口气说出独特的思想,另一种人用热烈夸张的口气说出平庸的思想。我的目标是写得流畅质朴而且独特,而不是写得艰涩玄妙以造成独特的外观。有的文字用朴素的形式表达深刻的内容,有的文字用华丽的形式掩盖肤浅的内容。然而,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我的人格理想:成熟的单纯。我的风格理想:不张扬的激情。

2
要创新,不要标新。标新是伪造你所没有的东西,创新则是去发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尚未被自己发现,创新之路无比宽广。趣味的形成有种种因素,包括知识、教养、阅历、思考、体验等等,这一切在趣味中都简化成了一种本能。在文学和艺术的欣赏中,良好趣味的形成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它使一个人本能地趋向好东西,唾弃坏东西。对于创作者来说,良好的趣味未必能使他创作出好东西,因为这还需要天赋和技巧,但能够使他不去制作那些他自己也会厌恶的坏东西。
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是以他的心灵为仓库的。不管你曾经有过多么丰富的经历、感受和思想,如果你的心灵已经枯寂,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就不再有意义。哪怕你著作等身,它们也至多能成为心灵依然活泼着的别人的精神财富,对于你却已是身外之物了。这是另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流行的小散文模式: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给人一点儿廉价的小感动,一点儿模糊的小感悟。这种东西是害人的,它们使读者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趋于肤浅,丧失了领悟生活的真相和实质的能力。别人说过的尽量少说,自己想说的尽量说透。艺术天才们不是用言辞、而是用自己的作品给美下定义,这些作品有力地改变和更新着人们对于美的理解。
书太多了,我决定清理掉一些。有一些书,不读一下就扔似乎可惜,我决定在扔以前粗读一遍。我想,这样也许就对得起它们了。可是,属于这个范围的书也非常多,结果必然是把时间都耗在这些较差的书上,而总也不能开始读较好的书了。于是,对得起它们的代价是我始终对不起自己。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在所有的书中,从最好的书开始读起。一直去读那些最好的书,最后当然就没有时间去读较差的书了,不过这就对了。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如此。世上可做可不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永远要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
因为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在两性亲昵中,从温言细语到甜言蜜语到花言巧语,语言愈夸张,爱情愈稀薄。达到了顶点,便会发生一个转折,双方恶言相向,爱变成了恨。真实的感情往往找不到语言,真正的两心契合也不需要语言,谓之默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不独爱情如此。在最深重的苦难中,没有呻吟,没有哭泣。沉默是绝望者最后的尊严。在最可怕的屈辱中,没有诅咒,没有叹息。沉默是复仇者最高的轻蔑。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为了应付发表的需要而炮制虚假的文字,因而不再有暇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锤炼语言的功夫。这就好像一个母亲忙于作为母亲协会的成员抛头露面,因而不再有暇照料自己的孩子。
法国作家列那尔说:“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称作经典作家。”
我对此话的理解是:惟有那些出于自身生命需要而从事写作的人,才能够攀上文学的高峰。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他人,仅仅为了自己,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并且真正使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这样的作品也就有可能属于一切人,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品。
我相信列那尔的意思并非说,凡业余作者都是经典作家。事实上,多少业余作者都是把文学当作职业来追求的。前提是巨大的才能,而源自生命需要的创作冲动本身就是天才的征兆。列那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这样的天才的一个警告:在他们成功之后,一旦他们仅仅出于职业习惯而写作,他们便不再是经典作家了。
写作是永无止境的试验。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不得不度过不断试验的一生。
我很想与出版界断交一段时间,重返孤独和默默无闻,那样也许能写出一些好东西。写作时悬着一个出版的目标,往往写不好。可是,如果没有外来的催迫,我又不免会偷懒,可能流失一些好东西。当然,最好的东西永远是由内在的催迫产生的。
有一家出版社筹划了一套“名人日记”丛书,向我约稿,我拒绝了。我对生前出版日记、书信之类总是感到犹豫,倒不是怕泄露隐私,因为在编辑时是可以把不想公开的内容删去的。我是怕从此以后,写日记写信时会不由自主地做作,面对的不再是自己和朋友,而是公众。我想对自己和朋友还是仁慈一点吧,不要把仅剩的一小块私人生活领地也充公了。
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就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应受到怀疑。
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说到底,一种没有内在动力的写作只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易受这种技艺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可怜复可怜的。最重要的是灵魂的认真和活泼,是内在的精神生活的连贯性,而不是写作。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生活,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自然探险、社会活动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做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一天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
如果我现在死去,我会为我没有写出某些作品而含恨,那是属于我的生命本质的作品,而我竟未能及时写出。至于我是否写出了那些学术著作,并不会如此牵动我的感情。
我应该着眼于此来安排我的写作的轻重缓急。
我的天性更是诗人而不是学者,这也许是因为我的感受力远胜于记忆力。我可以凭勤奋成为学问家,但那不会使我愉快。我爱自己的体悟远甚于爱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知识。
我的追求:表达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体悟。不拘形式,学术研究和人生探索,哲学和文学,写作和翻译,皆无不可。在精神生活的深处,并无学科之分。人类和个人均如此。
有时候,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养成了严格的工作习惯。
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新大陆,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世界,否则无权称为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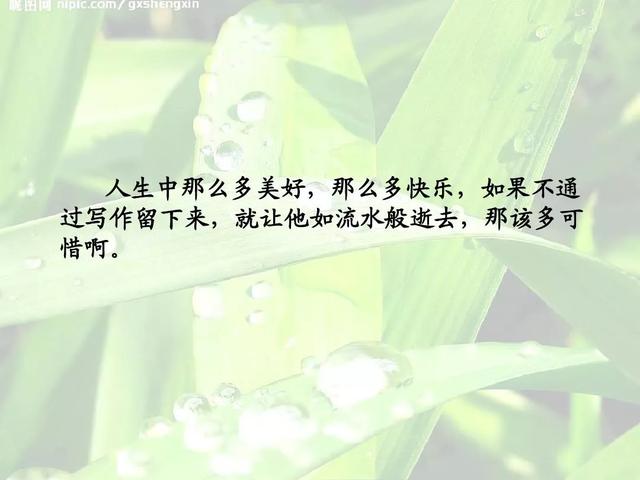
3
任何精神创作惟有对人生基本境况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一个作家的价值不在作品的数量,而在他所提供的那一点新东西。
一流作家可能写出三流作品,三流作家却不可能写出一流作品。
最好的作品和最劣的作品都缺少读者,最畅销的书总是处在两极之间的东西:较好的,平庸的,较劣的。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读者群,从读者的层次大致可以推知作者的层次,被爱凑热闹的人群簇拥着的必是浅薄作家。
几乎每个作家都有喜欢他的读者,区别在于:好作家有好的读者,也有差的读者,而坏作家只有差的读者。
写自己是无可指摘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不过,这个自己有深浅宽窄之分,写出来的结果也就大不一样。
可以剽窃词句和文章,但无法偷思想。一个思想,如果你不懂,无论你怎样抄袭那些用来表达它的词句,它仍然不属于你。当然,如果你真正懂,那么它的确也是属于你的,不存在剽窃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模仿苏格拉底的口气说话,却不可能靠模仿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倘若有一个人,他始终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思考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承认他是一个思想家,甚至就是苏格拉底,而不仅仅是一个模仿者。
一种人用平淡朴实的口气说出独特的思想,另一种人用热烈夸张的口气说出平庸的思想。
我的目标是写得流畅质朴而且独特,而不是写得艰涩玄妙以造成独特的外观。
有的文字用朴素的形式表达深刻的内容,有的文字用华丽的形式掩盖肤浅的内容。然而,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
我的人格理想:成熟的单纯。我的风格理想:不张扬的激情。
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格言家。格言乃神的语言,偶尔遗落在世间荒僻的小路上,凡人只能侥幸拾取,岂能刻意为之。
在你的诗里有太多的感情的下脚料。
一个好思想,一个好作品,在成形之前,起初只是一颗种子。这种子来自人类生活的土地,然后如同柳絮一样在人类精神的天空飘荡。倘若它落到了你的心中,你的心又恰巧是一片肥土,它就会在你的心中萌芽和生长,最后有希望发育成一棵好的植物。
精神的创造当然是离不开外部的环境的,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环境。满天柳絮,阳光明媚,水分充足,可是倘若你的心是一片瘠土,你的心中仍然不会绿柳成荫。一颗种子只有落在适宜的土壤上,才能真正作为一颗种子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创造的过程的确是一个自然过程。只要你有适宜的内部环境,又获得了一颗好种子,那么,不管你的躯体在外部世界上做着什么,哪怕你是在做着奴隶般的沉重劳动,这颗种子依然会默默地走着大自然指定的路。伟大作品之孕育未必是在书斋里,更多地是在风尘仆仆的人生旅途上,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各种琐事的时候,而书斋至多只是它一朝分娩的产房罢了。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个好的内部环境,一片沃土,一个好子宫。
要创新,不要标新。标新是伪造你所没有的东西,创新则是去发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尚未被自己发现,创新之路无比宽广。
趣味无争论,这无非是说,在不同的趣味之间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在不同的趣味之间肯定有高低之分。趣味又名鉴赏力,一个人的鉴赏力大致表明了他的精神级别。趣味的形成有种种因素,包括知识、教养、阅历、思考、体验等等,这一切在趣味中都简化成了一种本能。在文学和艺术的欣赏中,良好趣味的形成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它使一个人本能地趋向好东西,唾弃坏东西。对于创作者来说,良好的趣味未必能使他创作出好东西,因为这还需要天赋和技巧,但能够使他不去制作那些他自己也会厌恶的坏东西。
朋友相聚,欢声笑语,当时觉得趣味无穷。事后追记,为什么就不那么有趣了?肯定是遗忘了一点什么:情境,心境,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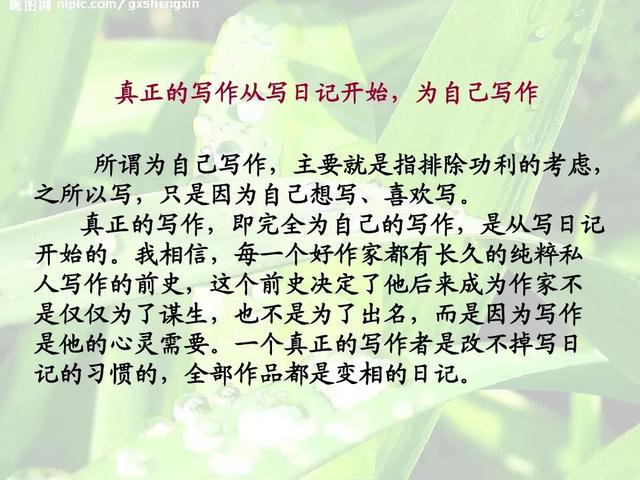
4
事过境迁,记录事实是困难的。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如果不能同时传达出当时的意味,写出的就不是当时的事实了。
我用语词之锁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打开锁来,发现感觉已经死去。
文字与眼前的景物、心中的激情有何共同之处呢?所以,写作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工作。
愈是酣畅的梦,醒后愈是回忆不起来。愈是情景交融的生活,文字愈是不能记叙。
精神仍在蓬勃生长,肉体却已经衰老,这是某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是以他的心灵为仓库的。不管你曾经有过多么丰富的经历、感受和思想,如果你的心灵已经枯寂,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就不再有意义。哪怕你著作等身,它们也至多能成为心灵依然活泼着的别人的精神财富,对于你却已是身外之物了。这是另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流行的小散文模式: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给人一点儿廉价的小感动,一点儿模糊的小感悟。
这种东西是害人的,它们使读者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趋于肤浅,丧失了领悟生活的真相和实质的能力。
现在我觉得,经常发表散文和随笔之类是有害的,这会妨碍积累和酝酿,使我变得肤浅。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思想和感觉多储藏一段时间,酿制成更浓烈的酒,组织进更大型更成熟的作品里。
当一个思绪或感觉突然浮现时,写作者要善于随时随地把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隔离出来。这时候,一切人、一切事物都不复存在,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思绪、感觉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写作者是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辛勤的搜集者。为了及时记下它们,他必须克服懒惰(有时是真正的疲劳)、害羞(例如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和世俗的礼貌(停止与人周旋)。
某人写了一本书,上门求教。书出版后,他来信表示感谢,说是根据我的意见缩减了篇幅,并复述了我的意见:“别人说过的尽量少说,自己想说的尽量说透。”我忘记我说过这话了,但觉得很有道理,亦可作为自己写作的指南,录下备忘。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弄。
质朴是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相反,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只有质朴的东西才能真正打动心灵。浮夸的东西只会扰乱心灵。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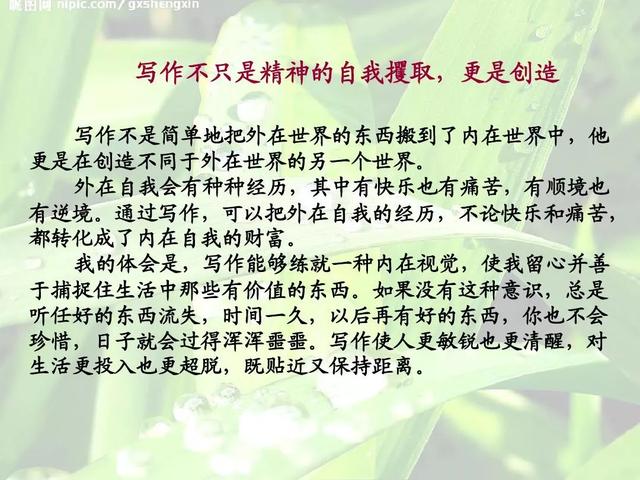
5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它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它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它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耕作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叫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亦即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它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真实不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是我们终于为自己找到的一种生活信念和准则。
从一个人的读物可以大致判断他的精神品级。人们总是想知道怎样读书,其实他们更应当知道的是怎样不读书。在才智方面,我平生最佩服两种人:一是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一是有出色口才的人。也许这两种才能原是一种,能言善辩是以博闻强记为前提的。我自己在这两方面相当自卑,读过的书只留下模糊的印象,谈论起自己的见解来也就只好寥寥数语,无法旁征博引。自我是一个凝聚点。不应该把自我溶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而应该把大师们的作品吸收到自我中来。对于自我来说,一切都只是养料。有两种人不可读太多的书:天才和白痴。天才读太多的书,就会占去创造的工夫,甚至窒息创造的活力,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白痴读书愈多愈糊涂,愈发不可救药。好读书和好色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不求甚解。
有人写作是以文字表达真实的感觉,有人写作是以文字掩盖感觉的贫乏。依我看,作品首先由此分出优劣。语言是一个人整体文化修养的综合指数,凡修养中的缺陷,必定会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来。好的文字风格如同好的仪态风度一样,来自日常一丝不苟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