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和朋友碰面,总会打招呼问:“最近在追什么剧?”、“新发现了哪家餐馆?”,或者:“去了哪里旅游?”
很少有人会问:“最近在读什么书?”
而这句话,却是美国作家威尔·施瓦尔贝最爱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但能帮助彼此找到共同话题,拉近距离,更能解答“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互联网时代还需要读书吗?阅读对于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威尔在《为生命而阅读》一书的序言中给出了自己的思索和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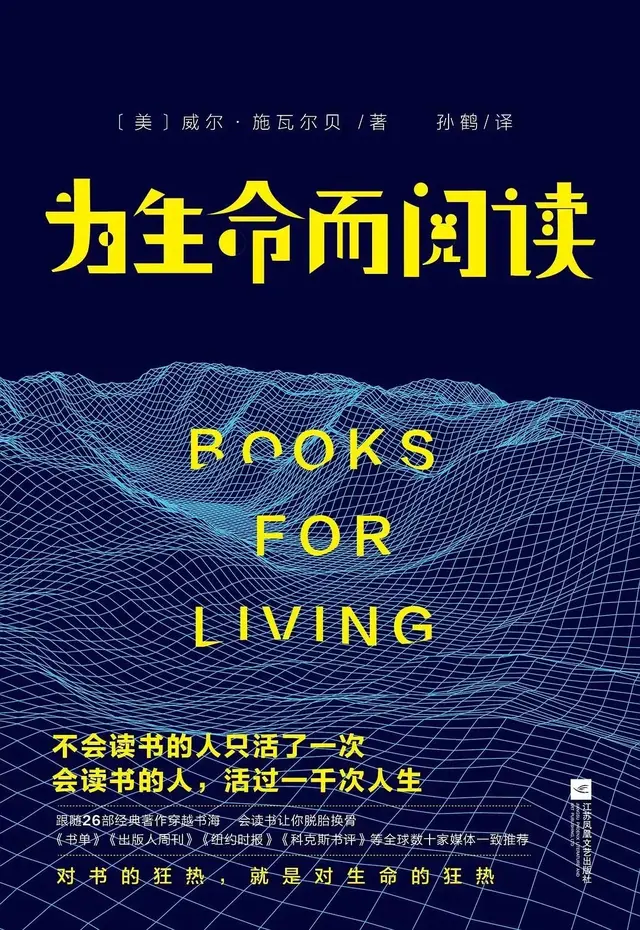
- 威尔·施瓦尔贝《为生命而阅读》
我时不时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我称之为读者的噩梦。
在繁忙的机场里,我的航班快要起飞了,但我离登机口还有很长一段路。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时间,几分钟之后通往登机道的大门将关闭,飞机就要飞走。
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在飞机上将无书可读。没有任何书。我原地打转,眼睛在疯狂地寻找着书店。但一家书店都没有看到。我在机场里跑起来,穿过卖洋酒香水的免税柜台,穿过箱包店和时尚精品店,穿过颈部按摩店。我仍然没有找到机场书店。
现在我的航班正在播放最后一次催促登机的广播:“飞往珀斯的97次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办理乘机手续的乘客请务必现在办理登机。”他们甚至叫了我的名字。我开始恐慌起来,意识到自己肯定要误机了。但一想到要飞几个小时没书看,简直难以忍受。所以我跑,继续跑,四处寻找着书店——至少是有简装书架的书报摊吧。但我在机场里仍是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开始尖叫。
然后我醒了。
我不会做与食物、电视剧、电影或是音乐有关的梦。我的潜意识并不会因为想到要在天上飞速移动的金属管子里待几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节目看或是没有音乐听而感到不安。多个小时没有书籍相伴这种想法会让我在冷汗中惊醒。
回顾我的一生,我一直因各种原因向书寻求帮助:希望它安慰我,逗我笑,能让我分心,带给我知识。但你知道,你可以在书中找到一切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轻易在刚刚好的时间找到合心意的那本书。
在人生某些时刻,当我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需求时,我会寻找一本书来解决它。找到正确的那本书并不那么容易。当然,当那个迫切的需求是学习如何做菠萝蛋糕时,我会找《蛋糕圣经》;或是当我需要在芝加哥找餐厅时,我会选《查格指南》;又或者是当我需要自己诊断发炎的皮疹时,我会向《梅奥诊所家庭健康指南》求助。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当我需要这类信息时我的首选不是书——而是网络,或是社交媒体。
然而,有些问题显然是网络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一些大问题,作家们几千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关痛苦、意义、目的和幸福的问题,有关如何生活的问题。
没错,网络试图帮助我们——正如我们可以说任何无生命的东西都在试图帮助我们一样。有一些数字频道喜欢播放鼓舞人心的会议演讲,人们在这些会议上把自己的见解打包成简短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大部分会搭配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和一些难忘的故事。但其中最好的部分通常只有一些简单摘要——或是广告——为演讲者写的书或是为正在写的书做宣传。
但和大部分励志演讲不一样,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演讲大多数情况也都只涉及自身,但大部分好书却不是孤立解决这些人生大问题的。伟大的作家会在时光的长河里互相对话。写书的人大多都是读书的,而大多数书里都留着丝丝缕缕成千上万本作家下笔前读过的书的痕迹。
这也是为什么书可以在数百年内不断留下回响直至未来的原因。即使是一本只有十几个人读过的书也可能留下非凡影响,只要它其中一个读者写下的书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即可。
苏格拉底在即将宣判他死刑的审判上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读书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学习如何审视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法。比比看自己做过的事和别人做过的事,自己的想法、理论、感受和别人的想法、理论和感受,你会愈发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是少数几个独自完成却让人感觉不那么孤单的事;阅读是一个连接他人的个体行为。
54岁的我和为《神曲》做最后润色的但丁年纪差不多,和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中的主人公冯·奥森巴哈一个年纪。(我最近才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迷恋美少年和他逝去的青春的男人,其实正值中年;因为没有仔细阅读开头部分,我一直以为这个让酒店理发师把他头发染得乌黑发亮,把脸涂得花里胡哨的“老”人至少有七十岁了。)
五十多岁正是思考这些大问题的好时候。除非我是少数能活过一百岁的人,不然剩下的时光肯定没有我活过的时间多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任何年纪都是思考这些大问题的好时候。我曾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问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好问题——恰好合适,因为解答问题正是学校的作用。我曾在生活的困难时期问过其他一些大问题——没有什么年纪是可以免遭不幸或是感觉不那么敏锐的。而我希望也期待可以一直问到最后。
我知道在帮助我找到正确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寻书之旅上我并不孤单。因为我在出版业工作,写过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我遇见过许多读者。各个年龄层的读者都告诉过我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书单来引导他们。
我听过有人想读经典名著,有人只想要基础入门书,有人想读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书。但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在乎是什么类型、什么时候或是谁写的书——他们只想读那些能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路,同时能带给他们愉悦的书。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在一次从纽约飞往拉斯维加斯的漫长而又颠簸不已的航班上,我坐在一个十九岁西点军校新生的旁边。我们开始闲聊,很快他谈起他最喜欢的一些书;保罗·科埃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其中之一。我告诉他我也很喜欢这个牧羊少年跋涉到埃及寻找宝藏的寓言故事。我们的对话很快从客套话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
飞机在空中颠来颠去,我开始兴奋地聊起其他启发过我的书。这个军校学员说他愿意用一顶货真价实的西点军校棒球帽来交换我最喜欢的书的书单。我很喜欢那顶帽子;希望他也喜欢那些书。
然后我要说说我九十六岁的朋友埃尔丝,她总是极度渴求好书推荐。最近,我向她推荐了露丝·尾关的《不存在的女孩》。2013年出版的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作家在太平洋西北岸捡到一些被海水冲刷上岸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十六岁东京少女的日记,她在学校里被各种欺负,不想再活下去了。小说在作家的故事、少女的日记以及和日记附在一起的信件中切换。书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是少女一百零四岁的曾祖母,一个有着迷人过去、充满魅力的禅宗女僧,当少女难以独自承受生活的重压时,她为少女提供了物质和情感上的庇护。
埃尔丝也同样充满巨大的魅力,但她的魅力要更有活力一些。(这么说吧,她经常飙脏话。)她也同样有着不可思议的过去:少年时期从纳粹德国逃离,后来成为电影音乐编辑。
埃尔丝愉快地读完《不存在的女孩》,有许多话想说。但她最想谈的是这个一百零四岁的女僧。埃尔丝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宣布女僧是她读过的所有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中遇到的最令人惊叹的人物——可以这么说,她在现实中也无人能及。“现在我知道我长大想成为谁了”,她高兴地向我宣布,边笑边拍手。
对我来说,我在寻找——一直在寻找,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一辈子都在寻找——能够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的书,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帮助我思考那些生命中无比重要的问题的书,以及解答一些我正巧遇到的小问题的书。
我知道那个西点军校学员、埃尔丝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寻找,一场我还未出生就已经开始一直到我去世后也不会结束的寻书之旅。
我们有摘抄诗歌和歌词优美部分然后使用的光荣传统。数百年来,人们一直有做“摘录本”的习惯:在日记本里手抄名言名段。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么一点点摘樱桃似的,摘抄任意一本书里的奇怪段落,然后用这些摘抄来指导生活。
有些人认为小说和剧本里的语句是依赖具体语境存在的——东挑西选一些奇怪句子出来是很不恰当和自私的,特别是当某句话是出自某个角色之口,那就很可能和作者本身的想法毫无干系。
我不这么认为。这种想法完全忽视了人类大脑收集、折射、整理、合并信息的能力。我们对意义的探寻并不仅限于那些被创造出来然后被塞入诗歌或是可轻易摘取的大段文字中那些有意义的思想。我们可以在任何事物中寻找到意义——一切都是公平的。实际上我们的大脑才是最终的摘录本,你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储存在大脑某处,时刻准备着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的意识中。
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从大脑中收集书籍和句子:我特意去找的书和偶然遇见的书,我强迫自己死记硬背下来的句子和自然而然记住的句子。
在家,我是个图书管理员,永远在管理我的收藏。离开公寓,我是个书商——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推销我喜欢的书。
有一个名字可以用来形容我这样的人:读者。

你正在读的这本书可以算是某种宣言——我的宣言,为读者发声的宣言。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读书,需要成为一名读者。
我们把日程排得太满,然后不停地抱怨自己太忙;我们不停地买着不需要的东西,然后感觉自己被周遭的杂乱压迫着;我们总是睡不好或是睡不够;我们拿自己和杂志上看到的人造身体做比较,和电视上夸大的生活做比较;我们看着烹饪节目却吃着快餐;我们担心生病而办了健身卡却从来不去;我们有成百上千的联系人却很少与最好的朋友见面;我们用视频、邮件和短信狂轰滥炸着自己;我们甚至打断我们自己打断的东西。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买什么或怎么度过闲暇时光时,我们总期待多一个选择。为了从那么多人为制造的选择中做出决定,我们把整个世界变成一本无穷无尽的供人“挑挑拣拣”的目录,只要是不让人觉得大开眼界的东西都被视作是无用之物。我们不再明褒实贬——我们明贬任何不能给我们带来狂喜的东西。爱恨成为默认值——要么五星要么一星。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恐惧的问题——害怕自己会错过什么。不管我们身处何处,总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做着看着吃着听着更好的东西。
我渴望逃离这种生活方式。我想如果有足够多的我们成功逃离,这个世界也许会因此变得更好一些。
联通性是互联网时代最大的便利之一,它让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可能。敲几下键盘我能得到整个世界的讯息;我可以在网上买卖、交易和分享东西;当我在陌生的地方开车时,一个知识渊博的声音会给我指路,当我走错路时会“重新计算我的路线”。简直难以数清我们的生活被互联网改变的地方。
但联通是一回事,持续的联通则是另一回事。当我想要“断网”几天,有时只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会提前警告其他人;其含义是除非你另外收到消息,不然你可以假设我这段时间都不上线。持续的联通可以变成一个诅咒,鼓励着我们天性中不那么善良的一面。古典时代的九位缪斯女神可没有叫焦躁或分心的。
在这个有着无穷无尽联通性的世界里,书正是独一无二最适合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与节奏的关系和我们日常习惯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打断书,所以我们只能在读书时打断自己。
书是个体或一群个体的表达,不是蜂巢思维或集体意识的表现。书与我们对话,是体贴地一对一的对话。书要求我们关注它,要求我们暂时搁置自己的信仰和偏见,听听别人的信仰和偏见。你可以大声抱怨一本书,在页边空白处胡写乱画,甚至随手丢到窗外。但你仍然无法改变书中的一字一句。
书的技术是真正天才的技术:虽然不管是在书页还是在屏幕上,书中词语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但阅读的速度却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当然,这让你可以加快速度跳着读,也让你可以慢来下,品味沉思。
我们经常互相问候:“你去哪里度假了?”“你睡得怎么样?”或是,我最喜欢问这个,当我眼巴巴看着朋友甜点盘上最后一口巧克力蛋糕时,我会问“这个你还吃吗?”
但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互相多问一些,那就是“你在读什么书?”
这是一个简单却很有力的问题,它可以改变生活,为被文化、年龄、时间和空间分割的人们创造一个共享的宇宙。

我记得有位女士曾经跟我说她很高兴当奶奶了,但有些难过和孙子不怎么联系。她住在佛罗里达州。孙子和他父母住在其他地方。她会给他打电话,问问他学校怎么样,今天过得好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挺好的,没什么,没事。
但有一天她问他在读什么书。他说他刚开始看《饥饿游戏》,苏珊·柯林斯 写的一部反乌托邦的青春系列小说。我遇见的这位祖母决定看看第一册,这样下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就可以和孙子聊一聊这本书。她并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但随后发现自己在开头看到凯特尼斯·伊夫狄恩自愿代替她妹妹和其他被选中的少男少女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生死之战时就被迷住了。
这本书帮助这位祖母打破粗浅的电话聊天,和她孙子一起讨论人类需要面对的关于生存与毁灭、忠诚与背叛以及善与恶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它也帮助她的孙子能够和她一起讨论同样的话题——不是作为一个需要教育的孩子,而是作为同样的追寻者。它给了他讨论他一直沉思的问题的共同语言,不用去解释到底为什么这些话题让他感兴趣。
当他们讨论《饥饿游戏》时,他们不只是祖母与孙子:他们是两个走在同样旅程上的读者。现在当她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的孙子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和她讨论——跟她说他读到哪儿了,问问她读到哪儿了,然后一起推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饥饿游戏》激发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深入探讨,为他们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的提示。这本书甚至引导着他们讨论经济不平等、战争、隐私和媒体等话题。随着他们继续一起读书和讨论其他书,他们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在不断扩大:他们的“词汇”由所有他们一起读过的书中的人物、情节和描写组成,他们可以自由运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情。
此前除了家庭问题,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现在他们有了。这个渠道就是读书。
当我们问别人“你在读什么书?”时,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相似之处,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同的地方,有时我们会发现隐藏的共同爱好;有时我们会打开探索新世界新想法的大门。
当怀着真诚的好奇心时,“你在读什么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其实是在问“你现在是谁?你正在变成谁?”
正如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医生可能会通过你的童年来解读你的欲望和动机,我觉得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在孩童时读过的书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读书。
但不仅仅是孩童时期读的书在我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位置,有时我读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我读过所有书中最重要的那本——直到下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出现为止。一开始觉得新鲜的东西总是可以看到更多深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因为不断的共鸣这些新意会在我大脑中打折。
其中一些作品我并不会列入我最喜欢的书中,但它们都是在我最需要时找到的(或许是它们找到我的),或是促使我记住什么、意识到什么,或是让我用全新的方式看世界。每个读者都可以这样列出一张表来,而这张表可能每年甚至每周都不一样。整理然后不断修订这种书单是我非常推荐的一种锻炼方式:这是构筑你自己的实践哲学的方法。

有些人会有一本一读再读的书,一本包含所有答案的书。但最通常的情况是,这会是一本关于某种信仰的中心的书:也许是《圣经》、《薄伽梵歌》、《古兰经》或其他。我对能找到一本可以解答我所有问题的书持怀疑态度。相反,我更愿意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帮助我解答众多问题。我怀疑永远不可能找到一本像忍者刀一样多功能的书。不管是烹饪还是阅读,我都享受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特殊工具和器具的乐趣——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使用的。
有时当我开始读书时,我会有这么一种特殊期待。也许,只是也许——尽管有悖于我到现在为止的所有阅读经验——我能遇到一本能给我需要的所有答案的书。它也许会出现。我的忍者刀。我的圣杯。
那也许会是我在跑去登机门路上,在机场书店里随手抓起的那本书,那本我在几秒间做出决定,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感兴趣的书。
我确实相信我的书的圣杯还在某个地方等我——我会一直读下去,直到找到它。当然,即使找到它我也会一直读下去,因为——好吧,因为我爱读书。我也相信书的圣杯不会是世上最伟大的书——我很确定没有这种东西。我想那会是一本在我最需要它的瞬间与我对话,最贴合我心,在我的余生也将继续与我对话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