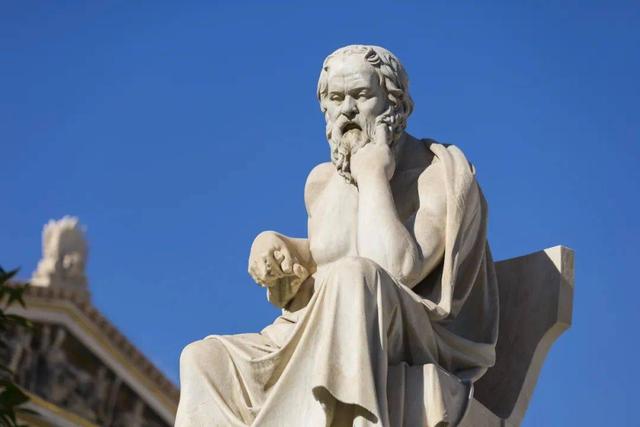
苏格拉底接着说:“西米啊,所谓勇敢,是不是哲学家的特殊品格呢?”
西米说:“准是的。”
“一个人不受热情的激动,能约束感情而行为适当,通常称为节制。自我节制,只有瞧不起肉体、一生追求哲学的人,才有这种品格吧?”
西米说:“应该是的。”
苏格拉底说:“假如你仔细想想,一般人的勇敢和节制,其实是荒谬的。”
“苏格拉底,这话可怎么讲呀?”
苏格拉底说:“哎,你不知道吗?一般人都把死看作头等坏事的。”
西米说:“他们确是把死看作头等坏事的。”
“勇士面临死亡的时候并不怕惧,他们是怕遭受更坏的坏事吧?”
“这倒是真的。”
“那么,除了哲学家,一般人的勇敢都是出于害怕。可是,勇敢出于怕惧和懦怯是荒谬的。”
“确是很荒谬。”
“关于节制,不也是同样情况吗?他们的自我克制是出于一种自我放纵。当然,这话听来好像不可能。不过他们那可笑的节制,无非因为怕错失了自己贪图的享乐。他们放弃某些享乐,因为他们贪图着另一种享乐,身不由己呢。一个人为享乐而身不由己,就是自我放纵啊。他们克制了某些享乐,因为他们贪图着另一些享乐,身不由己。我说他们的自我节制出于自我放纵,就是这个意思。”
“看来就是这么回事。”
“亲爱的西米啊,我认为要获得美德,不该这样交易——用这种享乐换那种享乐,这点痛苦换那点痛苦,这种怕惧换那种怕惧;这就好像交易货币,舍了小钱要大钱。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或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享乐、怕惧或其他各种都无足轻重。没有智慧,这种那种交易的美德只是假冒的,底子里是奴性,不健全,也不真实。真实是清除了这种虚假而得到的净化。自制呀,公正呀,勇敢呀,包括智慧本身都是一种净化。
——文/斐多,杨绛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