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教育价值的认知是知识获取(从学生角度)和知识传授(从教师角度)。目前的应试教育,更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因为考试的基本目的就是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学生的职责是学习知识,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这些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小孩回到家里,家长通常问的问题是今天你学了什么新知识?具有工作经验的人再回到学校学习,目的是为了更新知识。
事实上,知识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中国,知识又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就是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样把知识与个人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
在当今中国,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派生出一系列学生学习知识的特点和方法。首先是学生学习知识投入的时间多。研究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平均每天多两个小时。当然,这会产生挤出效应,由于用在学习知识上的时间多了,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时间就少了。
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下,学生为掌握知识点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于文科题目,“死记硬背”是传统方式。而理科题目,当然可以死记硬背公式和概念,但是解题就不容易了。不过,学生们也开发出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大量做题”来识别题型,记住解题技巧,最终达到解题的目的。
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一种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通常也是以知识为核心的,表现在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特殊培养,主要体现在“学早一点”“学多一点”“学深一点”。这里仍然是对知识而言的。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经历中发现,中国留学生往往在硕士和博士头两年的考试中领先全班。但是在此之后,当到达了知识前沿需要自己探索新知识的时候,中国学生的优势通常就没有了。这似乎同时印证了"因材施教"方法的长处和短处。
这种对知识点掌握的重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知识就是力量”本身是有道理的。知识确实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而教育就是人力资本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测评PISA中表现优秀,以至于近期一些发达国家聘请中国中学教师去教课。大量中国留学生被发达国家大学接受读硕士和博士。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教育有它的长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在近期被人诟病的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正是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够,这里的知识就是指各种学科的知识。
不过,中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可能正好与美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相反。虽然我们重视知识,但是我们存在另外的、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太简单地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教育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呢?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他对教育也有很多深刻见解。我最常引用的爱因斯坦关于教育的一句话是:“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当他到达波士顿后,一个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上找到答案,没有必要记住。随后就讲了上述这句名言。
爱因斯坦这里说的事实就是知识。知识当然重要,但是知识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他在这里提出了有关教育价值的一个新命题,就是教育的价值不是记住很多知识,而是训练大脑的思维。这就提出了教育价值超越知识的另一个维度——思维。而恰恰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中国教育是薄弱的。学生的思维发展正是我们教育中的短板。
思维或思考(thinking)通常被称为能力。能力有别于知识,这样便于区分两者,思维或思考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交集,但是并不完全相同。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教育是一个目前在世界范围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受到重视的话题,而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
批判性思维教育
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Derek Bok)在2006年出版Q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一书,中文翻译版是《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这本书基于他对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观察和反思,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提出诸多批评和改革建议。在我看来,他在书中对美国大学生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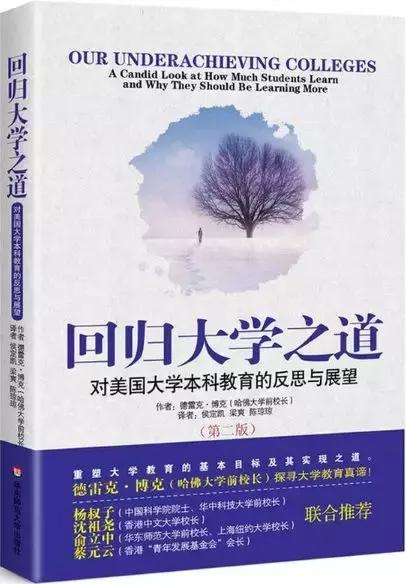
根据对哈佛学生的观察并且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博克在书中把大学本科生的思维模式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Ignorant Certainty”,即“无知的确定性”。这是一个盲目相信的阶段。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新生,往往都处于这个阶段。在中学,学生认为学到的知识是千真万确的,这个确定性来源于学生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是一种无知下的确定性。
第二阶段是“lntelligent Confusion”,即“有知的混乱性”。这是一个相对主义阶段。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各种对立的学派。虽然学生的知识增加了,但是他们往往感到各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
博克观察到大多数本科生的思维水平都停留在第二阶段,只有少数学生的思维水平能够进人第三阶段,就是“Critical Thinking”,即“批判性思维”阶段。这是思维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在各种不同说法之间,通过分析、取证、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断,论说出哪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高级阶段,它有两个特征第一,批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同解释和判断。这两个特征正是分别针对“无知的确定性”和“有知的混乱性”的,因此批判性思维不同于这两种思维方式。
在这两个特征中,第一条是会质疑即提出疑问。能够提出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据说犹太人小孩回到家里,家长不是问“你今天学了什么新知识”,而是问“你今天提了什么新问题”,甚至还要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中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条是在提出疑问之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力”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能力(skillsets)。第二个层次是“心智模式”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mindsets)。
首先,批判性思维的第一层次是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包括统计学内容。
2018年中国高考全国II卷中的作文题,也是一个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题目。
题目:根据以下材料写一篇作文。“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沃德(Abraham Wald)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之前也是经济学教授。他是统计决策理论(startistical decision theory)和序贯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的创始人之一。上面的故事是他在“二战”期间帮助美军分析的一个例子,它说明了统计分析中的“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问题。那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能够飞回来的飞机,而看不到那些被击落而没能飞回来的飞机。所以,只是根据“幸存者”的数据做出的判断是不正确的。这是基于统计推断的思维,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能力。这种测试题超越传统的知识范围,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训练、可测试的。但是如果认为批判性思维只是这些内容,那就错了。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称之为心智模式(mindset)。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和“问为什么”(ask the why question)。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层次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走进思维“盲区”。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是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也可以通过诸如有关批判性思维的测试题来测试。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如何)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如何)的,但很少是关于“why”(为何)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但不求甚解。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创造性思维教育
批判性思维教育是一个普遍的教育问题,而创造性思维教育更多地为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所关注。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要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即创造性人才。中国教育的优势表现在学生整体水平比较高,但是中国教育的弱点是突出人才太少。我曾经用一个统计学术语刻画这个特征,那就是“均值高”“方差小”。
这个教育特征对经济发展有双重含义: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模仿追赶阶段,它并不是坏事,至是优势,因为比较整齐、平均水平比较高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执行和管理。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阶段,缺少突出的、有创造力的人才,对经济发展会很不利。这就是为引么培养创造性人才在今日的中国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基本原因。
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的核心是人的创造性思维。人的创造性思维是指新的思维、与众不同的思维,它是产生创造力的源泉。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创造力的核心是“新”,发现新规律,发明新产品,运用新方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
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一般、更具准确性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不是没有,为什么这么少?
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有3600多万,高校在校生2700多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均为全球第一。相对于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受教育者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在中国产生的创新不是没有,确实太少。
近年来,我们也有不小进步。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占全球总量的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间,共有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1个。数学的菲尔兹奖是另一个指标。中国内地至今还没有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中国香港、越南、伊朗都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我们当然不能以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为唯一指标,但是它们有标志性。“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创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么?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三因素假说:创造性思维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决定。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而这些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把乔布斯(Steve Jobs)描写为“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企业家,是指科学与艺术的跨界。马斯克(Elon Musk)的本科专业是商业管理,同时修物理学第二学位,而物理学对他的创新创业有很大影响,这是科学与商业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识层面,我们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狭隘的专业知识的范围,更多地强调跨学科和跨界知识。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人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几年前,清华大学物理系邀请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在探讨他们为什么取得科学成就时,清华学生提出的词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等。然而,这四个人回答是一样的,不是这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说好奇心最重要。
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他还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只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他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识以外的因素,这正是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视的方面。
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经济学家都是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并以此测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不像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那么简单了,非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下,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长,教师和学生越努力,虽然学生的知识增长了,知识点掌握多了,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被扼杀得得系统而彻底。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创造性思维=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作为两者乘积的创造性思维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单纯上升的形状。
这就形成了创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力,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力。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造性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不那么确定,但是却能为解释一些辍学大学生很有创造力提供了空间。
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那么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当前影响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态和环境。个人和社会都想在创新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各种评价机制多是追求奖励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创造性和长远的成果往往难度量、难量化。
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讲话中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因斯坦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的信念是“简洁思维”,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简洁的理论解释,并可以用简洁的公式表述。他说过,“如果你无法简单地解释,就说明你知道得还不够多。”
乔布斯的创新也是来自一种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维”。面对IBM这样的大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乔布斯相信我要与你不同。长期以来,IBM的座右铭是其创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维),这就是ThinkPad名称的来源。1997年,当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正处于低谷。他为苹果公司精心设计了一个划时代的广告“献给疯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在展示出包括爱因斯坦、爱迪生、毕加索等杰出人物(“疯狂的人”)之后,广告推出的主题是苹果公司向这些人致意,与他们为伍,并针对IBM的“Think”推出苹果公司与这些“疯狂的人”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Think different”,即“不同思维”。正是这个“不同思维”,成就了苹果公司贡献给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产品。
一般来说,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体到当前情况,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这些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的结果。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这些需要长期才能见到成效的结果。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由于一种内在动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是为了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更幸福。这种内在价值是一种心态,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普朗克、爱因斯坦、乔布斯这样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具有第三类动机,是最高的境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其哲学和科学的产生是最为纯粹的基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在古希腊,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无知,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正是古希腊的那种对智慧的纯粹热爱,那种完全的非功利主义、不追求任何有用之回报的价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辉煌的哲学和科学。当然现代社会的情况不同于古希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受到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