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人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有资本肆意挥霍,享尽人生的荣华富贵。
叔本华不这样认为,他在《人生的智慧》中提出人们应过一种“适度的幸福生活”。“适度”就是节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愤怒。
世上有许多令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只能得到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许多祸患却更有可能降临在我们头上。人要回归自身,追求精神思想的乐趣,对生活做好最坏的打算,在众多不如意中选择最小的那个。为了外在的名声,牺牲自己内在的安宁、闲暇和独立,是愚蠢的行为。对自己适时的小小约束,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避免许多外在的桎梏。约束自己比起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效地使我们避免了外在束缚。
叔本华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减少不幸的生活,获取幸福的错误方法是花天酒地,幸福快乐的源泉是孤独和内在丰富,最高级、最恒久的乐趣是精神思想的乐趣。生活的准则是放弃和忍受,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生活了一辈子但又没有承受过什么巨大的精神或肉体的痛苦,而不是曾经享受过强烈无比的欢娱。谁要是根据后者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度过幸福的一生,那便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标准。
叔本华把人的内在丰富比喻为——在冬天的晚上,在漫天冰雪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愉快的圣诞小屋。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对于外在世界确实别无他求,除了这一否定特性的礼物——闲暇。他需要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
他的要求只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每时都可以成为自己。当一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印记留给整个人类,那么,对这个人就只有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可言——那就是,能够完美发掘、修养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否则,如果受到阻挠而不能这样做,那就是他的不幸了。
除此之外的其他别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都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人物都把闲暇视为最可宝贵的东西;因为闲暇之于每个人的价值是和这个人自身的价值对等的。“幸福好像就等同于闲暇”,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狄奥根尼斯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珍视闲暇甚于一切”。与这些说法不谋而合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探究哲学的生活称为最幸福的生活。他在《政治学》里所说的话也与我们的讨论相关;他说:“能够不受阻碍地培养、发挥一个人的突出才能,不管这种才能是什么,是为真正的幸福。”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谁要是生来就具备、生来就注定要发挥某种才能,那他就会在发挥这种才能中找到最美好的人生。”

但拥有闲暇不仅对于人们的惯常命运是陌生的、稀有的,对于人们的惯常天性而言也是如此,因为人的天然命运就是他必须花费时间去获得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赖以生存的东西。
人是匮乏的儿子,他并不是可以自由发挥智力的人。因此,闲暇很快就成了普通大众的包袱。的确,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各种幻想的、虚假的目标,以各式游戏消遣和爱好来填塞时间,到最后,闲暇就会变成了痛苦。
基于同样的原因,闲暇还会给人们带来危险,因为“当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难以保持安静”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拥有超出常规配备的智力却也是反常的,亦即违反自然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禀赋超常的人,那么,闲暇对于这一个人的幸福就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闲暇对于他人来说只是一种负担和麻烦。因为缺少了闲暇,这种人就犹如被套上木轭子的柏加索斯那样闷闷不乐。但如果上述的两种特殊反常的情形碰巧结合在一起——拥有闲暇属于外在的特殊情形,而具有超常禀赋则是内在的反常情形——那就是一个人的一大幸运。因为这样的话,那个得天独厚的人现在就可以过上一种更加高级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活免除了人生两个对立的痛苦根源:匮乏和无聊。换句话说,他再不用为生存而忧心忡忡地奔忙,也不会无力忍受闲暇(闲暇也就是自由的生存)。人生这两种痛苦,匮乏和无聊,也只有通过其彼此抵消和中和,才使常人得以逃脱它们的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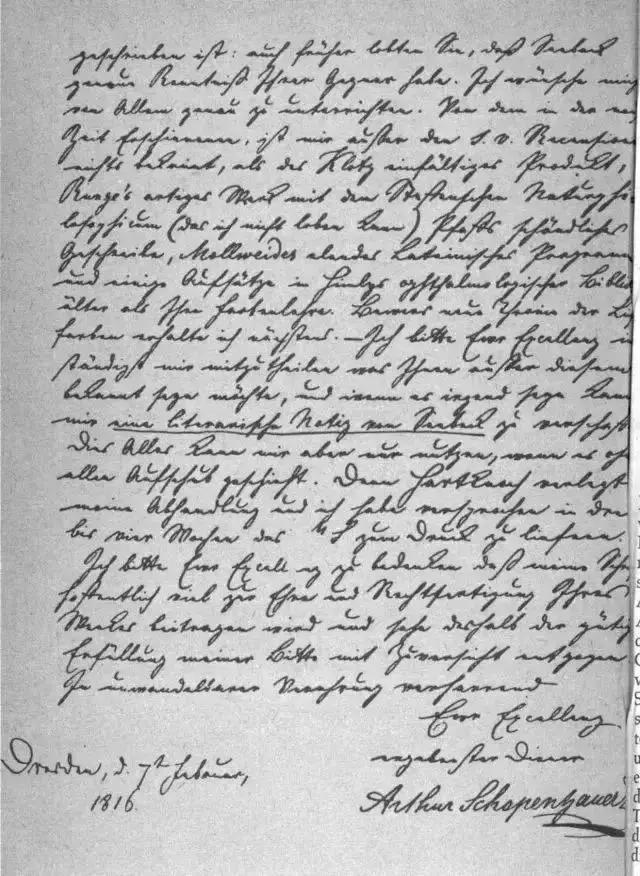
虽然如此,我们却要考虑到:一个具有优异禀赋的人由于头脑超常的神经活动,对形形色色的痛苦的感受力被大大加强了。另外,他那激烈的气质——这是他拥有这些禀赋的前提条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事物和形象的更加鲜明、完整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使被刺激起来的情绪更加强烈。一般而言,这些感觉情绪总是给这种人带来痛苦多于愉快。最后一点就是巨大的精神思想禀赋使拥有这些禀赋的人疏远了他人及其追求。因为自身的拥有越丰富,他在别人身上所能发现得到的就越少。
大众引以为乐的、花样繁多的事情,在他眼里既乏味又浅薄。那无处不在的事物均衡互补法则或许在这里也发挥着作用。确实,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并且似乎不无道理的说法就是:头脑至为狭窄、局促的人根本上就是最幸福的,虽然并没有人会羡慕他们的这一好运。我不想让读者先入为主,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是索福克勒斯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就表达过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
头脑聪明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是主要的。又要过最轻松愉快的生活莫过于头脑简单。
在圣经《旧约》里,贤哲们的说法同样令人莫衷一是: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
越有智慧,就越烦恼。

在这里,我得提及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由于仅仅具备了那常规的、有限的智力配给,所以,他们并没有精神思想上的要求,他们也就是德语里的Philister——“菲利斯特人”。
这名称源自德国的大学生词汇。后来,这一名称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虽然它和原来的意思依然相似;“菲利斯特人”指的是和“缪斯的孩子”恰恰相反的意思,那就是“被文艺女神抛弃的人”。
确实,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我应该把菲利斯特人的定义确定为所有那些总是严肃古板地关注着那并非现实之现实的人。不过,这样一个超验的定义却跟大众的视角不相吻合——而我在这本书里所采用的就是大众的视角——所以,这样的定义或者不会被每一个读者所透彻理解。
相比之下,这名称的第一个定义更加容易解释清楚,它也详细表现了菲利斯特人的特质及其根源。因此,菲利斯特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
根据我提及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就可以推断:首先,在他们的自身方面,菲利斯特人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乐趣。他的存在并没有受到任何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这一强烈欲望的驱动,也没有要享受真正的美的热切愿望——美的享受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密切相关。但如果时尚或者权威把这一类快乐强加给他们,那他们就会像应付强制性苦役般地尽快把它们打发了事。

对这种人来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是感官上的快乐。牡蛎和香槟就是他们生存的最高境界。他们生活的目的也就是为自己获得所有能为他们带来身体上安逸和舒适的东西。如果这些事情把他们忙得晕头转向,那他们就的确快乐了!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好东西大量提供给他们,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而为了对抗无聊,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舞会、社交、看戏、玩牌、赌博、饮酒、旅行、马匹、女人,等等。
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赶走无聊,因为缺少了精神的需求,精神的快乐也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菲利斯特人都有一个奇异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副呆滞、干巴巴的类似于动物的一本正经和严肃表情。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们愉快、激动,能提起他们的兴趣。感官的乐趣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由同样的菲利斯特人所组成的社交聚会,很快就变得乏味无聊,纸牌游戏到最后也变得令人厌倦。不管怎样,这种人最终还剩下虚荣心。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享受虚荣心所带给他们的乐趣,那就是:他们尽力在财富或者社会地位,或者权力和影响力方面胜人一筹,并藉此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崇。又或者,他们至少可以追随那些拥有上述本事的人,以沐浴在这些人身上折射出来的余辉之中。从我们提到的这些菲利斯特人的本质,可以引出第二点:对于他人,由于菲利斯特人没有精神上的需求,而只有身体上的需要,
所以,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会寻求那些能够满足自己身体上的需要,而不是精神上的需求的人。因此,在他们对别人的诸多要求当中,最不重要的就是别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头脑思想。当他看见别人具有突出的头脑思想时,那反而只会引起菲利斯特人的反感,甚至憎恨。因为他们有着一股可憎的自卑感,以及呆笨的、不为人知的嫉妒心——他们小心翼翼地试图把它们掩饰起来,甚至对自己也是这样。但这样一来,这种嫉妒有时候就会变成某种私下里的苦涩和愤怒。因此,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要对卓越的精神思想给予恰如其分的尊崇和敬意;他们一心一意地把尊崇和敬意留给拥有地位、财富、权力、影响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眼中才是真正优越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出风头也就成了他们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这一事实:他们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