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个哲学貌似繁荣昌盛的时代讨论哲学的危机,有“盛世危言”之嫌。毫无疑问,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我们这个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繁荣”——虽然我们都对哲学的发展、地位和影响等等心怀不满,但是从事哲学工作的人、哲学的产品、学习哲学或者学过哲学的人(这也意味着受到过哲学影响的人)……比过去不知道多出了多少倍,何言哲学的危机?
我想在作为一个学科的哲学与作为哲学的哲学之间做一个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越是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或学科,哲学就越不是哲学——哲学迷失于它的“科学情结”。不恰当地说,哲学越是像科学就越不像哲学,越是像哲学就越不像科学,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赵敦华教授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一版结束语“西方哲学的危机与出路”中概括了哲学的四次危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的泛滥使得希腊人追求知识的愿望遭遇挫折,激发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哲学转向了人生哲学,最终败给了基督教;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经院哲学衰落,笛卡尔走上了哲学舞台;19世纪黑格尔之后,哲学失去了自己的研究领地,数理逻辑和现象学方法使哲学获得了新生……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危机”有内外两个方面。所谓哲学的内部危机,指的是哲学的演变由问题推动,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哲学问题需要一揽子的整体规划,这就要求每一位哲学家都必须彻底解决哲学问题,但是实际上都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而已,哲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以至于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范式。就此而论,哲学始终在危机之中,危机是哲学的常态。与此同时,哲学的这种内部危机也是造成它的外部危机的原因之一——
哲学的外部危机意味着哲学这个学科的存在出现了问题,亦即人们所说的“哲学的终结”。以哲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而论,科学之求真与哲学相同,甚至可以看作是哲学之求真的体现。由于近代以来科学与技术相结合成为推进物质文明进步的“第一生产力”,以至于哲学的很多工作都由科学“接管”了,这就是霍金所说的:“哲学已死”,貌似哲学家的工作都转交给了科学家——
霍金:《大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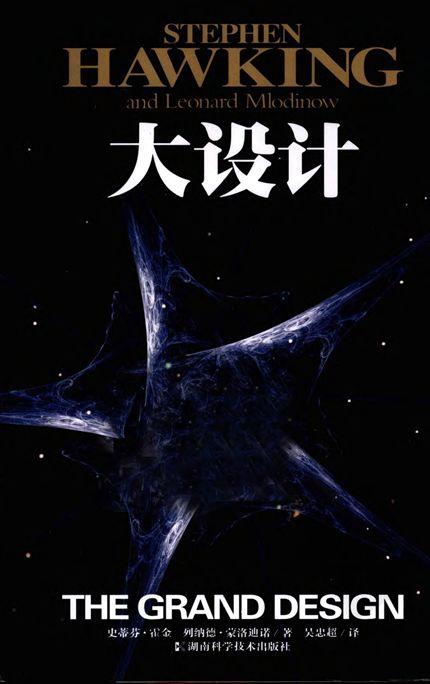
宣称哲学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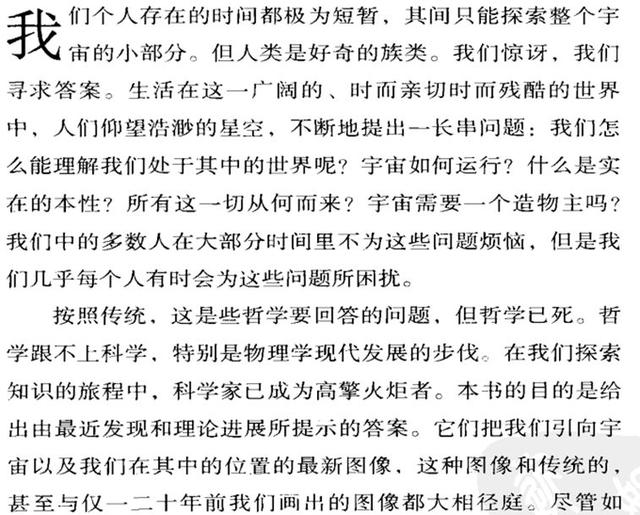
霍金的说法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不过的确符合一部分事实,20世纪以来“哲学的终结”之声始终不绝如缕,而且往往出自哲学家之口。例如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章《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就认为哲学终结于科学和技术,因为科学和技术已经完美地实现了哲学要合理地解释世界的理想,不过他仍然给“思”留下了“任务”。
我们今天讨论“哲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关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哲学的危机始终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我看来,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看作哲学与自身的关系问题。在此我想引入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求真,而技术实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笼统地把希腊人追求的知识称为“哲学”,那么科学(理论科学)体现的是哲学中求真的因素,只不过科学的问题在希腊人那里是以哲学的方式回答的——当时哲学和科学不分,都是“自上而下”地解释世界的普遍方式。应该说,这种解释世界的方式在东方文明中也存在,区别在于其中缺少科学的因素。
技术则有所不同,技术源于经验,以实用为目的,不过也往往停留在经验层面。简言之,东方曾经在技术层面上长期领先于西方文明,18世纪以后因为西方人把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开辟了现代化的道路,从而确立了西方文明的领先地位。不过,也正是因为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得哲学与科学和技术最终分道扬镳了。
当今时代哲学的危机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哲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其二是哲学失去了自己的问题,从而在轴心时代的没落这一大背景之下,自觉地退出了回应终极关怀问题的竞争。这两个方面有相关性。
一、哲学的诞生
二、哲学的繁荣
三、哲学的危机
一、哲学的诞生
世事并非必然如此,哲学的产生便有其偶然性,须知在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更新过程之中,只有希腊人创制了哲学。就此而论,我们没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等古代文明没有产生哲学,应该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希腊人创制了哲学?
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之为“轴心时期”,在此期间各大文明相继产生了原创性的思想:中国先秦之诸子百家、希腊哲学、印度《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犹太先知。
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解释框架。
轴心时代是人类各大文明的“更新”,主要原因是此前的“传统”出现了危机。按照雅斯贝尔斯,它所体现的特点是,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面对这些问题,不同的文明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哲学是希腊人的创造。
我个人的意见,希腊人创制了哲学,在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出现的是宗教,先秦诸子百家则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宗教。就其产生了半宗教或非宗教性质的“天”、“道”等观念而论,先秦思想具有自上而下普遍地解释宇宙的因素,不过主要目的是以此来解释和规范社会礼仪制度,并没有形成对自然本身的科学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人创制了哲学实属意外,东方古老文明关注于实用性的技术是正常的。用比埃尔·韦尔南的话说:“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
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
从神话到哲学

希腊的科学精神:学以致知
按照H·弗洛里斯·科恩(《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希腊人形成了两种认识自然的方式,他称之为“雅典”和“亚历山大”,前者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后者则更倾向于纯粹的数学研究。区别于东方文明“学以致用”的实用精神,希腊人形成了一种“学以致知”的科学精神。对于古代文明来说,这种无用的“屠龙之术”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的。为了维持庞大帝国的存在可以举国之力发展技术,但恐怕不会发展哲学-科学。
哲学=科学思维方式
哲学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或者说,科学思维方式是在哲学中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不再用神话的或者宗教的方式理解和解释自然,而是要求按照自然去认识自然,以自然的原因合理地解释自然的事物。这种基于好奇而求知的理性活动虽然试图认识和解释自然,不过由于自然科学尚未成熟,所以是哲学的认识方式,即从最高原理出发自上而下地解释自然。希腊人的哲学-科学并不实用,也没有帮助希腊文明得以延续,在版图、军事实力、财富包括技术方面远不如罗马人,这种精神能够存活下来应该说是奇迹。
哲学≈科学
叶秀山先生在《科学·宗教·哲学》的序中称哲学在源头处是一种“科学”的形态,实际上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科学在其源头处是一种“哲学”的形态。亚里士多德主张哲学起源于“好奇”或“惊异”,他对此的说明很有意思——
哲学起源于好奇(thaumazein)
显然,在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解释哲学的起源的问题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只不过在古代世界解决科学问题的方式主要是哲学的,体现为自上而下解释世界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人有认识世界的愿望却没有改造世界的野心,所以即便是从经验观察出发,也只是停留在对经验的理论解释上,并没有形成某种“实验科学”,所以并没有“实用性”。
戴维·伍顿在《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中研究了很多与科学相关的概念的起源和演变。按照作者的分析,近代科学产生之初虽然不可能摆脱古代知识的束缚,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它既不是“科学”(science)也不是“哲学”,因为这两个概念都与古代哲学密切相关,代表的是传统的陈旧的知识。1748年,狄德罗匿名发表了一篇色情小说《轻率的珠宝》,第29章的副标题是“也是这章故事最好、最少被阅读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章没有色情的描写,而是描述了主人公的一个梦——
在梦里,他骑着一匹鹰头马飞向悬在云里的一座大厦。有一群畸形的人围着一个站在蛛网做的讲道台上的老人,他一言不发,只是吹气泡。他们都赤身裸体,身上只挂着几块布,这些布条是苏格拉底长袍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正身处哲学的殿堂。突然——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孩子迈着缓慢但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他头小,身瘦,胳膊软,腿短。但是,随着他的前进,他的四肢越长越大,通过不间断地飞速成长,他向我显现了很多不同的样子。 看见他把一架长筒望远镜指向天空,借助一个钟摆测量一个落体的速度,用一个充满水银的管子称量空气,用手里的一面棱镜分解光。他变成了一个巨人……巨人摇晃殿堂,殿堂倒塌了”。这个巨人显然指的是近代科学:他提到了伽利略、梅森、巴斯卡尔和牛顿。不过,狄德罗并没有把这个巨人称为科学或哲学,而是称为“经验”,也许我们称之为“实验”更贴切,即理论与经验的结合。
H·弗洛里斯·科恩在《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中借用培根关于蚂蚁、蜘蛛和蜜蜂的比喻,把希腊人认识自然的方式称为“理智主义的”——蜘蛛,把中国人认识自然的方式称为“经验主义的”——蚂蚁,而近代科学的产生则是两者的结合——蜜蜂。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希腊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的结合产生了近代科学,近代科学是欧洲的产物,而是一种比喻。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近代哲学之初人们都在嘲笑亚里士多德,但如果没有希腊人的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不会有近代科学的产生。
实际上,希腊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具有自上而下地解释宇宙的特点,因而都可以看作是哲学。只不过希腊哲学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而中国哲学则不具有科学的因素。道理很简单:科学不实用。古老的东方文明都没有产生科学,希腊是一个例外。当然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人无论如何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理解自然的,只不过希腊人基于城邦制度的视角所理解的自然碰巧比中国人基于“礼仪天下”的视角所理解的自然,更接近于自然本身。
如前所述,希腊人认识自然的方式可以区别为“雅典”和“亚历山大”,前者自上而下地解释自然,后者关注于纯粹数学的研究。这两种方式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了复兴,不过在哥白尼日心说提出之后,人们意识到希腊人错了,由此而产生了通过精确的观察而认识自然的第三种认识方式:真理不能从理智中导出,而是要到精确的观察中去寻找,目的是实现某些实际的目标。于是,原本在希腊人那里无用的科学开始有用了,最终催生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
达·芬奇在遗作《绘画论》中写到:“如果不能够进行数学证明,那么全部人类的研究都不能被称作真正的科学。如果你说始于头脑、终于头脑的科学是真实的,那么它就不能被承认,只能因为众多理由而被否认。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头脑练习缺乏经验的检验。如果没有经验的检验,那么一切都不可能是确凿无疑的”(转引自戴维·伍顿:《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在达·芬奇的心目中,科学=数学+经验。
17世纪科学革命最重要的影响是科学理论与技术的结合。原本在希腊人那里纯粹的理论爱好引起了技术上的进步,技术有了理论基础,使得西方文明后来居上,超越了东方。然而,当自然科学逐渐形成统一的范式的时候,哲学仍然坚持自上而下构建一个理想世界来解释现实世界的思路,而当哲学试图以哲学的方式成为科学的时候,哲学与科学便开始分化了。其结果是哲学“学科”的繁荣。
二、哲学的繁荣
我在这里说的“哲学的繁荣”指的是哲学这个学科的繁荣。实际上,哲学的繁荣也是哲学的危机: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对社会的影响成反比。
12世纪开始出现的大学是中世纪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不过在漫长的中世纪,大学的核心是神学,哲学一般在神学院,18世纪以后才从神学院中独立出来(以康德为例)。一般认为1810年正式开学的柏林大学是大学从中世纪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的标志,实际上在此之前哈勒大学已经开始了转型。于是,哲学开始独立于神学,逐渐成为了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标准配置,而从事哲学工作的人则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时代。
对哲学这个学科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哲学本身来说,很可能是最差的时代。迄今为止,哲学学科已经成了任何一所像样大学的“标配”,哲学的从业人员之多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相比的,甚至超过了以往2000年之总和的很多倍。例如20世纪末,仅美国哲学协会的会员就超过了8000人。然而,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泛滥将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哲学逼回了象牙塔,另一方面哲学的职业化、专业化使得哲学自己划地为牢,将哲学圈外的广大人群拒之门外。所以哲学学科越繁荣,哲学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小。
我们现在有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而没有哲学家,我们甚至拒绝哲学家的称号,把它拱手让给了“民哲”。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开始说到:“对有些学者来说,哲学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这本《导论》不是为他们写的。他们应该等到那些致力于从理性本身的源泉进行探讨的人把工作完成之后,向世人宣告已经做出了什么事情”。很遗憾,我们的哲学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变成了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缺少哲学层面的思想对话。
我并不是反对把哲学史当作一个专业来研究,哲学在中国是西学,而对于在中国研究西学的人来说,西方哲学的确是一个专业。但是如果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仅仅被当作研究哲学家著作的某种专业,研究哲学就变成了研究哲学史,哲学也就变成了历史博物馆。
研究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的朋友可能有不同意见,在英美被看作是“当代主流哲学”的语言哲学,不再是哲学史的研究,而且变成了某种“自下而上”的类似自然科学的学科——语言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也可以成为科学。然而,且不说哲学能否成为科学,仅就哲学成为一个专业化的学科而论,其结果是一样的——
仅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哲学是一级学科,下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哲学虽然不是科学却也走上了分工越来越细的“科学”道路,然而学科划分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哲学研究者之间已经无法相互理解,更何况哲学圈子外面的人;其二是研究哲学的人貌似越来越多,不过研究的只是哲学的某一分支而已,哲学本身却反而没有人去研究了。直接的后果是哲学对现实社会失去了影响力。
哲学与科学影响社会的方式不同
自然科学和技术也是高度分工的,不过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是通过共享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我虽然不会设计和制造高铁,但这并不妨碍我坐高铁。哲学却不行,因为哲学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发挥作用的,一篇哲学论文,一部哲学著作,如果人们读不懂,它就不起任何作用。所以,哲学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越高,它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小。有人会说,过去哲学家的著作人们也读不懂,的确如此。不过在过去哲学作为精英文化毕竟是文化的代表,而现在代表文化的是大众文化。
我并不是主张哲学不要专业化,不过一旦专业化的要求等同于社会意义方面的要求,哲学就等于退出了社会,实际上我们的学术责任越来越重,而社会责任却越来越轻,或者说以学术责任代替了社会责任。一个项目的设计和施工要用到科学和技术,如果其中出现了问题,科学技术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哲学家则没有类似的社会责任。于是,我们貌似在哲学领域里解决了很多理论问题,我们也热衷于乃至满足于在哲学领域里解决问题,而出了哲学的学术圈子,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真正令人忧虑的是,当哲学越来越向着一个“学科”发展的时候,这并不能使哲学成为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那部分功能已经剥离于哲学之外了,而哲学作为哲学的那部分功能却大大萎缩了——哲学不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才是哲学的真正危机。
三、哲学的危机
轴心时代的没落
形而上学的终结
哲学的危机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虽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仍然不失为关于人类文明的一个解释框架。如果说轴心时代之前是轴心时代的传统,轴心时代则是我们的传统。自轴心时代以来,各大文明的传统观念对世界的影响持续了2000多年,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中国人则时常要回到先秦诸子百家去,但是自17世纪以来,这些传统观念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影响力,由此而引起的哲学的危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轴心时代的没落
轴心时代的没落源于欧洲从17世纪开始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17世纪之前,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基本上都属于“向后看齐”的: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宗教改革要回到原始基督教的信仰去。然而此后发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则是指向未来的,从而颠覆了传统,激发了社会变革。
17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是迷信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发生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已远非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往上回顾,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没有发现一个与我现在看到的变化相似的变化。过去已经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P882)。
托克维尔这句话大有深意。180多年前托克维尔根据他对美国的考察,触及了现代性的核心亦即无限开放的未来,一方面由此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向未来开放而不再靠过去的指引,已经找不到先例,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探索。有道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现在我们重新沦入黑暗。
现代性文明超越传统社会各大文明的一般之处是什么?按照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它在于由传统决定的社会逐渐转向了由未来决定的社会。简言之,创新和进步乃是现代性的核心。我们今天已经普遍接受了发展和进步的观念,而在世界历史之中,或许除了中华文明而外,文明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进步倒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在我看来,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朝代的兴亡更迭周而复始,也不是靠进步维系生存的)。
轴心时代的没落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
形而上学的终结
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希腊哲学以形而上学回应虚无主义的问题,以“存在”作为所有存在物的基础和根据,在2000多年中精心编织了一个超感性的完美的理性世界(本质世界)来解释我们面前的可感世界(现象界),这种方式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峰。
自哲学在公元前6世纪诞生以来,直到19世纪上半叶,哲学的重心是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自从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概念,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将“存在”转变成了存在物的“是什么”即理念,及至亚里士多德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做了区别:科学分门别类地研究存在物是什么,哲学研究的则是存在物之整体存在的分类即范畴,这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逻辑学》。然而随着黑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完成,形而上学也走向了终结。
轴心时代没落的标志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不要以为“上帝死了”与我们无关,鉴于西方文明波及全世界,我们同西方人一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说,按照海德格尔,“上帝死了”标志着用一个超感性世界解释现实世界的方式彻底衰落了,这意味着轴心时代所有的文明理念都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诞生于希腊的哲学也不例外。
上帝死了=超感性世界的崩溃
“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同时,这个‘基督教上帝’还是一个主导观念,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海德格尔:《尼采》,P671)。
在轴心时代产生的希腊哲学也是应对虚无主义的一种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以理性把握事物的本质亦即存在来为我们面前的现实世界提供基础和根据,这就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形而上学基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别而思存在者的存在,而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想乃是通过抽象出存在者的普遍共相即本质的方式而实现的。由此,存在问题被转换为存在者的存在的问题,存在本身不再是问题。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哲学的开端之处,在形而上学以存在为对象之初,我们就已经遗忘了存在。
哲学的根本理想是以一个超感性的理想世界为我们面前的现象世界提供合理的说明和存在的根据,我们可以称之为“柏拉图主义”。近代哲学与科学实证主义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颠覆了柏拉图主义,其结果是没有两个世界,超感性的世界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世界即我们面前的物理世界。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倾向自不待言,让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近代哲学上。近代哲学发端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对于科学知识的基础的解释最终导致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康德以“知性为自然立法”为科学知识提供先天条件,在当时雅各比就意识到了其中的虚无主义的危险——物自体不可知意味着自然的意义是由主体赋予的,自然本身没有意义。
不恰当地说,尼采是康德的继承人,只不过他比康德更彻底而已。尼采自称是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以往的哲学以超感性世界作为现实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和根据,现实世界自身没有意义,其意义存在于那个超感性世界之中。尼采颠覆了超感性世界,意图把意义还给感性世界。然而,当尼采试图以超人为现实世界赋予意义之时,他仍然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航道”之上,所以不可能克服虚无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哲学同样行进在这一“航道”上——
看起来,19世纪下半叶哲学发生的危机,经由数理逻辑和现象学方法而使哲学满血复活,越来越向着专业学科的方向发展,似乎度过了难关,实际上并非如此。哲学并没有找到形而上学的替代之物。
轴心时代的没落起源于哲学中的科学因素与技术结合而导致的科学革命,由此开启了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自那时起,全世界相继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便与传统说再见了。问题是,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理念的目的是为了抵御虚无主义,现在形而上学这副铠甲分崩离析,我们重新暴露在虚无主义的威胁之下。
这让我想起了佛教的《箭喻经》:一个人中了毒箭,他不断在追问的是,谁射的箭,谁造的箭,谁涂的毒……而这个时候真正应该做的是救命。我们关于造箭,射箭,制毒……写了一部部研究著作,唯独没有救命的书。
哲学的出路--首先取决于仍然有属于哲学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亦即虚无主义的问题,植根于人的有限性与超越性的冲突,这应该是人类始终面临的永恒的难题。
就我个人意见而言,我仍然相信哲学的目的或意义是解释和证明世界的合理性,因而哲学具有理想性。传统的哲学总是关于一个相对、偶然、不完善的世界的完美的解释和说明,它要用一个理想的世界模型为现实的世界提供某种基础和根据。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身处“上帝死了”,乌托邦崩溃的虚无主义的时代,哲学的理想性顺理成章地遭到了质疑和嘲笑。如果哲学解释世界的方式不够科学,我们还需要哲学吗?
如果哲学解释世界的方式足够科学,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哲学了。如果科学解释世界的方式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就还需要哲学。
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在一个貌似哲学繁荣昌盛的时代讨论哲学的危机,有“盛世危言”之嫌,实际上我心中所想的是——这其实不是“盛世危言”而是“衰世危言”:对科学和技术来说也许这是盛世,但对哲学来说这是衰世,哲学的危机就在于此。在我看来,哲学的危机并不只是哲学自己的事,归根结底乃是人类文明的危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