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邦雅曼·贡斯当的著作《1787年的法国》(第6卷,第1款:论政治上的反作用)中,第123页包含着如下说法:
法国哲学家在第124页以如下方式反驳这个原理: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义务的概念与法权的概念不可分割。一种义务是在一个存在者那里与另一个存在者的法权相符合的东西。在不存在任何法权的地方,就不存在任何义务。因此,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但是,没有人对伤害别人的真话拥有法权。
在这里,首要的错误就在于这个命题:“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
首先要注意,“对真话有一种法权”这个表述是个没有意义的词。人们毋宁必须说:人对他自己的真诚,亦即在他的人格中对主观的真话有一种法权。因为客观上对真话有一种法权,就会等于是说:一般而言就“我的”和“你的”来说,一个被给予的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取决于他的意志;这就会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现在第一个问题是:人在他不能回避用“是”或者“否”来回答的场合里,是否有权限(法权)不真诚。第二个问题是:他是不是完全有责任在一种不义的强制迫使他作出的某个陈述中不真诚,以便防止一个威胁着他的、对他或者对一个他者的犯罪行为。
人们不能够回避的陈述中的真诚,是人对每个人的形式义务,不管由此是给他还是给一个他者带来多么大的坏处;而且尽管我在伪造陈述时并没有对以不义的方式迫使我作出陈述的人行事不义,但我毕竟通过这样一种由此也(虽然不是在法学家的意义上)能够被称为说谎的伪造而在一般而言的义务的最根本部分上行事不义,也就是说,我在事情取决于我的时候使得陈述(声明)一般而言没有获得任何信任,因而也使得所有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法权被取消,丧失其力量;这是一般而言的人性所遭受的不义。
因此,说谎在仅仅被定义为有意对另一个人作出不真的声明时,并不需要补充说,它必然伤害一个他者;就像法学家为定义它所要求的那样(说谎是损害另一个人的谎言)。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在伤害一个他者,即便不是另一个人,但毕竟是一般而言的人性,因为它使得法权的源泉变得不可用。
但是,这种好心的说谎也可能由于一种偶然而变成可按民法来惩罚的;不过,仅仅由于偶然而逃避惩罚的东西,也能够按照外在的法律被判为不义。也就是说,如果你以一次说谎阻止了一个现在要去凶杀的人的行动,则你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要负法律责任。但是,如果你严守真诚,则公共的正义不能对你有所指摘;不管无法预见的后果会是什么。毕竟有可能的是,在你真诚地用“是”来回答凶犯他所攻击的人是否在家的问题之后,这个人不被察觉地走出去了,就这样没有落入凶犯的手中,因而行动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你说谎,说他不在家,而且他确实(尽管你不知道)走出去了,凶犯在他离开时遇到了他,并且对他实施行动,则你有理由作为此人死亡的肇事者而被起诉。因为如果你尽自己所知说真话,则也许凶犯在家中搜寻自己的敌人时会受到路过的邻居们的攻击而行动被阻止。因此,谁说谎,不管他这时心肠多么好,都必须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甚至是在民事法庭前负责,并为此受到惩罚,不管这些后果多么无法预见,因为真诚是一种必须被视为一切能够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义务之基础的义务,哪怕人们只是允许对它有一丁点儿例外,都将使它的法则动摇和失效。
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地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

在这里,贡斯当先生关于对这样一些严厉而且据说迷失在不能实行的理念之中的、但由此而是应予谴责的原理的叱骂所作的评论,是好意的,同时是正确的。——“每次(他在第123页下面说),当一个被证明为真的原理显得无法运用时,其原因都在于,我们不了解包含着运用手段的中间原理。”他(在第121页)提出平等学说来作为构成社会链条的第一环:“(第122页)因为没有一个人不能通过这样一些法律来约束,他一起参与了一些法律的形成。在一个结合紧密的社会中,这个原理可以直接运用,而且并不为了成为通常的原理而需要任何中间原理。但是,在一个人口十分众多的社会里,人们就必须还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原理附加上一个新的原理。这个中间原理就是:个别的人都能够或者以自己的人格或者通过代理人参与法律的形成。谁要把前一个原理运用于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不为此采用中间原理,就肯定会造成这个社会的堕落。然而,仅仅见证了立法者的无知或者笨拙的这种状况,不会证明任何东西来反对原理。”——他在第125页的结束语是,“因此,一个被承认为真的原理必须永不被背离,无论在这里存在的危险多么显著”(不过,善良的人由于无条件的真诚原理给社会带来的危险而自己背离了它,因为他不能发现用来防止这种危险的任何中间原理,而且这里也确实插不进任何中间原理)。
如果人们想保留这里所提及的人格的名字,则“法国哲学家”把某人由于说出自己不能回避其承认的真话而伤害另一个人的行动与他行事不义的行动混为一谈了。陈述的真诚伤害家中的居住者,这纯属偶然,而不是一个自由行为(在法学的意义上)。因为从他要求另一个人应当为他的好处而说谎的法权中,会得出一种与一切合法性相冲突的要求。但是,每个人不仅有一种法权,而且甚至有一种极严格的义务在陈述中真诚,哪怕这种真诚会伤害他自己或者他人。因此,他真正说来并没有借此伤害由此受难的人,而是偶然引起了这种伤害。因为既然真诚(在他一度必须说话时)是无条件的义务,每个人在这一点上都根本不是自由地选择的。——因此,“德国哲学家”将不把“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这个命题接受为自己的原理:首先是由于该命题不清晰的程式,因为真话并不是财富,能够肯定一个人对之有法权,却否认其他人对之有法权;但尤其是由于真诚的义务(这里惟一说的就是这种义务)并不在人们对之有这种义务,或者人们对之也能够宣布放弃义务的人格之间作出区分,而是由于它是在所有的关系中都有效的无条件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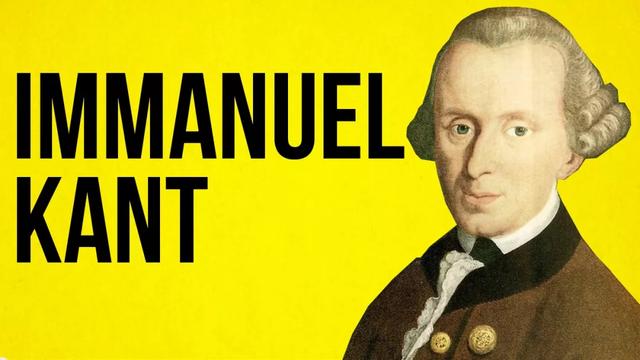
而今,为了从一种法权形而上学(它抽去了一切经验条件)达到一个政治的原理(它把这些概念运用于经验场合),并凭借这个原理达到依照普遍的法权原则对政治的一个课题的解决,哲学家将给出:1.一个公理,亦即一个无可争议的确定的命题,它直接产生自外部法权的定义(按照普遍的法律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与每个人的自由协调一致);2.一个公设,即外部公共法律的公设,作为所有人按照平等原则联合起来的意志,没有平等就不会有每个人的自由;3.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得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中还按照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保持和睦(亦即凭借一种代议制),这就将是政治的一个原理,政治的活动和秩序如今将获得从人的经验认识得出,仅仅以法权管理的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如何合目的地建立为目的的法令。——法权永远不必适应政治,但政治却必须任何时候都适应法权。
作者说:“一个被承认为真的(我补充:先天地被承认为真的,因而无可争议的)原理必须永不被背离,无论在这里存在的危险多么显著。”只是人们在这里必须理解的不是伤害的危险,而是一般而言行事不义的危险。如果我使完全无条件的,并且在陈述中构成至上法权条件的真诚义务成为一个有条件的,还从属于其他考虑的义务,并且即便我由于某次说谎事实上没有对任何人行事不义,却毕竟侵犯了在所有一般而言必不可免的陈述上的法权原则(在形式上行事不义,尽管不是实际上行事不义),就会发生后一种情况;这比对某一个人行事不义更加糟糕,因为这样一种行为并不那么总是以主体中的一个原理为前提条件的。
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对他提出的质问,即他在自己现在应当作出的陈述中是不是愿意真诚,并不是已经由于借此对他表示的怀疑而感到不满,而是请求允许自己想一想可能的例外,这个人就是一个说谎者了(潜在地),因为他表明自己并不承认真诚是义务自身,而是为自己保留对一个规则的例外,而这个规则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有例外的,因为它在这种例外中完全与自身相矛盾。

一切法权实践的原理都必须包含着严格的真实性,而且这里所说的中间原理只能包含它们(按照政治的规则)运用于出现的事例的进一步规定,但绝不能包含着它们的例外,因为这些例外毁掉了普遍性,而他们只是因为普遍性才享有原理之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