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希腊诗人赫昔俄德将人类历史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是一个逐渐衰变的过程。根据赫昔俄德的说法,黄金时代繁荣和谐、物资丰富、风调雨顺,在神的庇护下,人类可以不事劳动就享有美好生活;最糟糕的是黑铁时代,一个由人类主宰世界的时代,当宙斯在这个世界注入了生老病死以及尔虞我诈后,原有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人类不再能毫无戒备地安享美好。因为脱离了神的庇护,黑铁时代的人不得不进入各行各业从事生产劳动,竞争生存资源,但与此同时,宙斯也害怕人类最终会因混乱而走向集体灭亡,于是将正义送往人间。有了正义的加持,人类社会恢复了秩序。
但这样的叙事策略经常无效,因为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例证广泛弥漫于社会各部门之内,一个兢兢业业、认真工作的员工会因为公司上级领导的错误决策而丢失工作,一名救落水儿童的军人因体力不支而被洪水冲走。反面案例也有不少,比如靠干非法勾当发家致富的商业大亨,屠杀无辜百姓稳坐权力宝座的暴君。在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看来,这些例子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行为带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选择,而是因为运气所致。问题来了:既然做好人会遭厄运,做坏事也可以岁月静好,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好人?

为什么做好人?
柏拉图尝试用“幸福叙事”替代“神话叙事”以回应这一问题,他的说法是:幸福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做好人有助于幸福,所以我们要做好人。但是,对于“何谓幸福”和“如何实现幸福”这样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如果有人相信做坏事也能提升幸福,那么幸福叙事就会和神话叙事一样面临破产风险。所以从策略上来说,要人们接受“做好人有利于幸福”需要克服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让人们对幸福形成共识;第二,如果实现幸福有诸多手段,如何把“做好人”当作最优项。
这里的问题是,“幸福”是一个复合型概念而非单一型概念,区别是复合型概念抽象模糊,单一型概念清晰明确。为了克服模糊性,柏拉图采取还原论策略,因为还原论可以将复合性概念转变成单一型概念,他在早期作品《普罗泰戈拉篇》中将幸福还原成快乐。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快乐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感受,虽然造成快乐的原因和手段各种各样,但对于快乐的体会,却是无差异、同质的,而且人们在表现快乐时也高度相似,比如满脸笑容等,所以将幸福还原成快乐能成功解决第一个问题。
但第二个问题依然没解决好,即快乐导向并不能保证“做好人”成为最优选择。原因有三:第一,追求快乐有较为明显的功利性,对于快乐的追求是由个体对未来的期望所驱动,但好目的并不必然蕴含好手段,如果偷盗能带来快乐,那么偷盗也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第二,快乐属于私人感受,无法传递给他人,在追求过程中会体现出一定的排他性,尤其在广泛的零和游戏中,一个人获得快乐往往需要以剥夺另一个人的快乐为代价,所以以快乐为导向很多时候会产生冲突;第三,快乐有一定时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但做好人是一项需要持久投入的行为,既然持久的投入只能带来暂时的快乐,人们也没充分理由将“做好人”坚持到底。
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柏拉图在中期作品《理想国》中升级了还原论,指出“好生活的最终目的不是感受,而是活动”,直接把幸福还原成行动状态,以“作为理智生活的幸福”代替“作为快乐感受的幸福”。所谓的理智生活,是一种不断进行哲学洗礼、致力于内心平静与和谐的沉思生活。因为沉思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生活,它能实现充分的自足性,所以柏拉图宣称,通达幸福的唯一道路就是过理智生活。
柏拉图的论证可被重构为三步:第一步,他将心灵活动划分为理智和非理智部分,并指出理智部分的功能是认识、追求智慧,非理智部分的功能是制造情感和欲望,两者性质不一,但会相互影响,当非理智部分干扰理智部分时,人的认识就会发生偏差;第二步,他指出没有人有意过一种坏生活,一个人之所以过上坏生活是因为他受到了情感和欲望的影响,将坏生活误以为是好生活,有些人虽然行动上是在过坏生活,但心里一直以为自己过得是好生活;第三步是他的结论,既然情感和欲望会导致误解,所以只要把他们剔除掉,好生活的样板——即追求智慧的沉思生活——会自然浮现于眼前,成为个体的必然选项。

在柏拉图的语境中,做不做好人、行事时是否应该正当,与其说是选择问题,不如说是认识论问题,因为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只要能认识好,他就必然会选择好,又因为好的形式只有一种,所以只要能看到,共识就会水到渠成。就这点而言,用“作为理智生活的幸福”代替“作为快乐感受的幸福”能顺利解决上述提及的“共识问题”和“选择问题”。
非理智要素能被剔除吗?
其实柏拉图的方案极为激进,因为他要求改造人性。我们从未见过太阳冲撞地球,也不曾听说过地球与月亮摩擦,但知道三者遵循物理学机制,在特定位置上安静地运行。正是基于对自然界其他事物的考察,柏拉图才提出了驱除非理智要素的方案,因为一旦能成功剔除,人类就能像星星那样“和谐、美好以及幸福”的公转与自转。可这种剔除方案不会成功,因为非理智要素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从现代脑科学角度讲,“人性”是指基于大脑运作机制而涌现出来的心智现象以及与心智现象相匹配的行为模式。所谓的理智、情感和欲望都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是无数个特定的神经元细胞在共同协作时所产生的显性特征。所以,要剔除非理智要素意味着必须搞开颅手术、切除特定细胞团、打断特定的神经链条。这样的操作若要具备可行性与安全性,就必须以清楚认识大脑运作机制为前提。
然而,大脑是有机体而非机器。机器是基于特定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工具,但大脑却是一个在自然环境中经历过无数刺激后逐渐演化出来的有机体。机器无论是在结构还是材质方面均一目了然,其功能可以通过零部件的组合来实现,如果机器老化,也可以通过更换零部件来翻新。对于人而言,机器是可知的,但大脑却是一个黑箱,其运作机制只能通过对照组实验以及溯因的方式推测得知。但是,实验只能做到外部测试而非内部测试,所以大脑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可知,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可知。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充足理由相信人可以通过特定手段摆脱生物学机制的约束并改造自我。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那种作为动物性特征的情感和欲望并非负担,而是在经历无数个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后所保留下来的、有利于人类物种繁衍下去的必要条件。早期和中期的柏拉图并不承认这一点,所以相信只要通过哲学洗礼就能剔除人类自身的动物性、降低人类生活中的不确定。但是,后期的柏拉图却改变了这一立场,在《斐德罗篇》中承认非理智要素的积极作用,具体给归为三条:
第一,理智能帮助我们认识事物,但认识并非凭空而起,如同地图能帮助我们了解地形和方位,但并不促使我们上学,除非有像求知欲那样的非理智因素在背后助动;第二,实现目标是一个累进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激励,如同开长途汽车需要多次加油,若没有持久渴望,理智活动也多会半道折返,所以作为理智活动对立面的非理智因素也是理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非理智要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成分,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冲突,理智活动虽然能通过详尽的分析将它们一一理清,但总有一些需要非理智因素提供润滑剂功能,比如夫妻间吵架,讲道理没用,但因爱采取的退让却有效。

如何拯救我们的生活?
我们想拯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害怕意外风险会将自己拉入深渊。但风险是一个中性词,既意味损失和冲突,又蕴含机会和惊喜,屏蔽损失意味着放弃机会,渴望惊喜则必须直面冲突。如果以对风险的态度来划分,柏拉图是风险规避型选手,主张通过自我修炼来实现自足性,因为他相信自足性是免于意外伤害的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则是风险敞开型选手,相信风险总是存在,人虽然能增强抵抗力,但无法彻底摆脱灾难与意外,所以与其想着躲避,不如学会适应。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所倡导的自足性是一种只有当人将自身的社会性完全剥离后才有望获得的结果,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一种社群动物,时刻处在交往关系中。事实上,所有生物体都以社群形式存在,因为只有生活在种群内,繁衍才能继续,才有机会将生命延续下去,个体一旦落单,其生存能力将会迅速减弱。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克里纳伯格就曾研究过离群索居者的死亡案例,他在作品《热浪》中指出,1995年7月芝加哥爆发持续高温天气,有超过700余人死于酷暑,这些人本来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暑,比如去各种公共场所、亲戚朋友子女家,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空间里,已经丧失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以至于当热浪来袭时无处可去,唯有等死。“热浪”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在柏拉图那里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柏拉图并不认为身体上的伤害是伤害,正如他在《理想国》中所声称的那样,“好人不会受到伤害”,所以即便好人遭遇身体上的伤害也可以视而不见。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这一点,他相信求生、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倾向,只要是人,必然会害怕肉体上的痛苦——即便有人愿意承担肉体上的痛苦,也并非因为不害怕痛苦,而是因为有某些更宏大的目标在做牵引,另其愿意去承担。我以为,两者的分歧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如何看待“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柏拉图把人看得比动物高,但亚里士多德仅仅把人视作动物的一支。
纳斯鲍姆认为,如果我们认同亚里士多德式的人设立场,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人本身的脆弱以及与生俱来的生存欲望。如果有机会面对那些在芝加哥热浪中幸存下来的离群索居者,亚里士多德会说:回到人群中去,和他人生活在一起,唯有同舟共济,才有机会战胜生命中的风暴,各位才有机会拯救自己的生活。相比于改变人性,亚里士多德更愿意尝试改变人际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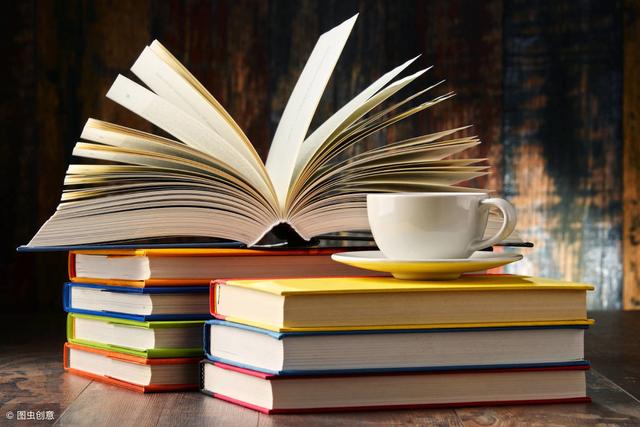
回到开头之问:我们还有必要坚持做好人吗?这取决于如何定义“做好人”。如果做好人指的是为了实现个人幸福、逃避风险而做出的理智选择,那么“做好人”就没显得那么紧迫,尤其是对那些拥有绝对理智的孤傲强者而言。但除此之外,若“做好人”还意味着一系列关乎社会的承诺,即在行为上表现为包括正直、勇敢、忠诚与信任等美德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毕竟人是生于社会、长于社会的,抛开这些美德也就意味着疏远人群。反过来说,一旦我们认可个体有“做好人”的责任,也就意味着,我们愿意接受来自社会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