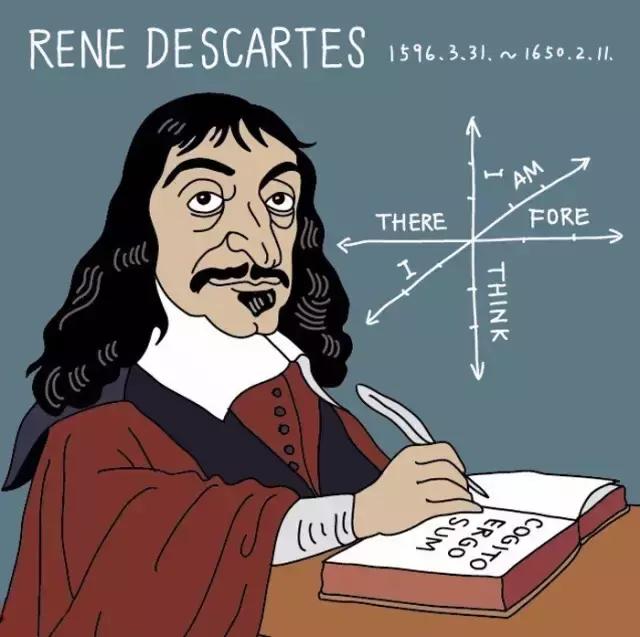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J·B 施尼温德《自律的发明:近代道德哲学史》,上海三联书店,张志平 译。
笛卡尔说,他希望他能避免写伦理学方面的东西。他认为与他的其余哲学思想已经给他带来的麻烦相比,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点甚至会在保守的宗教信仰者那里给他带来更大麻烦。更何况,规范他人生活仅仅属于统治者的职权范围,而与个人无关。在《方法谈》中,他提出他所谓的“临时道德” ——une morale provision;但是他告诉布尔曼,他这样做仅仅是“考虑到像学究那样的人们;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或信仰的人,并且想用自己的方法颠覆他们” 。在笛卡尔或者他的读者怀疑自己的所有信念并探求重建它们的基础时,遵循这种临时道德是应该的。因为,在此期间,他不得不行动,并因此需要指导。
这种临时道德是以一条怀疑论者的普遍原则开始的:服从你自己国家的法律和习俗。接着是李普修斯可能会同意的两条准则:无论让你作出选择的信念有多么不确定,一旦你选择某种行为方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通过让自己仅仅渴求完全在自己权能范围内的事情,而做自己而不是世界的主人。最后一条准则所要求的行为似乎一生只有一次:对所有可获得的职业进行评估,并选择出其中最好的。不过,在此笛卡尔比听上去要更为果断。他认为,是上帝赋予我们独立分辨真假的能力,而他打算一生都去运用这种能力,这种决心是他仅仅暂时接受别人意见的唯一理由。他想用自己的新方法为探求真理而奉献—生;只有那样,他才会知道应如何生活。
知识对正确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笛卡尔对此毫不怀疑。那么,他也意识到,要获得我们所需的这种知识并不容易,他非强调获取知识的顺序。具备临时道德之后,研究者首先逻辑学;其次必须掌握形而上学及其论断;正如笛卡尔在《沉思录》(Meditations)中所表明的那样,他进而要从研究有关自我的知识过渡到有关上帝的知识,再过渡到有关无机界的知识。接着,他还要研究生命物,尤其是人 。认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能指望获得医学和道德原则知识。这两门科学对我们最为有益。可以说,形而上学构成知识之树的根部,而实用科学是其果实,由此可见,“哲学的主要用处取决于它只有在最后才能让我们学到的那此部分”。只有在我们掌握了它们之后,我们才能拥有最完善的道德体系。
笛卡尔补充说他对知识之树枝条末端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这种评论似乎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不够真诚,因为在他作出这种评论时,他已经发展出一门激情心理学,而他与此相应的伦理学也有了雏形。如果他是在很认真地宣称他对道德的无知,因只能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必定是无知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他说,要推出这些原则所能向我们表明的知识,可能还需要花上好几个世纪。笛卡尔对道德的理解使他足以发现,没有人拥有我们过一种理想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无论我们具备怎样的道德,它都总是“临时性的”。
斯多葛主义者当然意识到,甚至最有智慧的人,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也不会拥有完备的知识。不过,就像其17世纪的追随者那样,他们重视描绘完善的圣人可能会过的生活,要远胜于对我们如何克服自己不可避免的无知提出建议。相对来说,笛卡尔对德性圆满的生活却谈得很少。他认为他就应该如何生活所能给我们提出的积极忠告,是合乎人类境况的。我们的无知使他所发现的最值得赞赏的美德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心理学就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美德。
对笛卡尔来说,思维实体(thinking substance),也就是我们的心灵,是简单的。因此,所有不同的心理功能都必须被看成是不同的思维样式。一位批评者曾指出,由此必然会得出结论说,意志(will)这类东西是不存在的。对此,笛卡尔回答说“欲求、理解、想象、感觉等等,都只是思维的不同样式,并且也都属于灵魂”。我们体验为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各种念头就是意愿(volitions),它们是心灵独有的活动;构成知识的各种知觉就是激情。有些意愿指向内心,如那些使我们思考抽象存在物的意愿;其他意愿则指向外部,如让我们决定去散步的意愿。不论如何定向,意愿作为念头都与某个对象有关,其作用就在于把我们与那个对象联结或分离。
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纯粹理论思维中,意志都很重要。当我们有了某种理论想法时,我们能够或者接受它——把它变成我们的——或者拒绝它;而如果我们接受它,我们就要相信或认识它。当我们有了某物是好的想法时,我们对它的认可就是们所谓的欲望,而欲望又会通过把精神重新引向松果腺而有效调动我们的身体。因此,在与行动的关系中,意愿就是好和坏或完善和不完善的活跃想法。我们必然会追求我们认是好的而避免我们认为是坏的东西。接着,笛卡尔说,如果我们清楚而分明地发现“某物对我们有好处”,只要我们一直抱有这种想法,“要消除我们对它的欲望”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们想到这样做可以很好地证明我们拥有意志自由时,我们才会放弃追求被清楚感知到的善。
因此,我们的自由(liberty)基本上不是无所谓(indifferent)的自由,只有当我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选项的好处和坏处缺乏够明晰的知识时,我们才会对它们无所谓。我们的无所谓是一种不完善——缺乏知识——的表现,尽管它在上帝那里是出于他的全能。但是,我们给予赞同或反对的能力,或者说,我们的自由(freedom)是一种积极的权能,它没有任何不完善之处。笛卡尔宣称,我们拥有这种权能是如此地自明,以至于我们有关我们有它的知识可以与我们有关其他那些天赋观念的知识相提并论。我们不能怀疑自己的自由(freedom),甚至当我们发现上帝已预定一切并且无法理解这种预定如何能与我们的自由相兼容时也是如此。当我们自由行动时,我们就是在做我最想做的事情,既然清楚性和分明性是我们表示赞同的最好理由,我们就应该赞同清楚而又分明的命题。另一方面,既然再也找不到欲求某物的更好理由,我们就应该去追求我们发现显然是善的东西。当我们没有理由接受或拒绝时,我们就会无所谓;没有理由的行为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自由行为。“因此,”笛卡尔对一位批判性的质问者说道,“一般意义上,我所谓的自由就是出于自愿,而你却想把这术语界定为只有在无所谓时才作出决定的权能”。在无所谓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也能自由行动,但这样做的能力并不重要。正因为自由意志是接受或拒绝的权能,我们的赞扬和谴责以及功和过才有可能。
于是,对笛卡尔来说,“自愿和自由就是一回事”,而对自由的恰当运用就在于,使我们仅仅根据清楚分明的知觉采取行动。但是,由于我们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体的束缚,要获得清楚分明的知觉并不容易。由于身体的影响,我们对世界上物体的知觉并不完善。这些知觉是混乱而又模糊的思想。通常,它们很容易引起我们对实际上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好的东西的欲望。只有知识能帮助我们;但是,即使懂得知识的妙用并对它孜孜以求,我们也不见得总是能获得它。
笛卡尔针对无知而提出的补救措施,就在于他临时道德的第二条原则:尽可能地果断;一旦作出决定,哪怕是根据可疑的意见行动,也要坚定不移。后来,他把这条准则改述为“在践行理性忠告时,人要真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甚至在我们明知不可能获得终极真理时也要如此。如果我们具有清楚分明的善的知识,它就会向我们发出行动的命令。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知识,就只有意志坚定不移的坚强决心才能向我们发出行动的命令。如果我们很果敢,我们甚至会根据我们还不确定的信念而坚定地采取行动。笛卡尔反复说,我们最像上帝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例如上帝是绝对坚定不移的。因此,当我们拥有美德时,我们就是在尽可能按照上帝形象塑造自己:我们使自已坚定不移。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并按照经过反思对我们是最好的理由行事,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后悔或遗憾。而让我们受到指责的事情也就将与我们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