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王安忆
- 文章来源:《什么是幸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 图片来源于《战争与和平》电影截图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巨作,篇幅特别长,有那么多人物,可我觉得这部小说只写了两个人:
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彼尔,写了这两个人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主要为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是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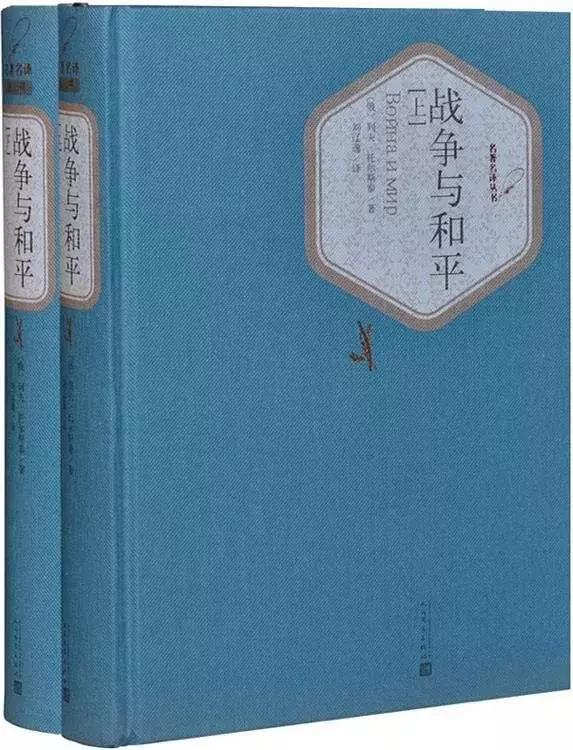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在民间传说中,主人公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最后一句话往往是:
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什么是幸福呢?这是困惑每个人的问题。
安德烈和彼尔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从不同的途径来解答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为什么托尔斯泰选择这两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他们是谁。

两人都是贵族,衣食早已不成问题,全部人生都可用来清谈、冥想、玄思,过精神生活。
但贵族阶级开始没落,走下坡路,糜烂、腐败,丧失活力。
道德伦理岌岌可危,礼崩乐坏,四处可见贵族子弟堕落的细节。

贵族家庭很普遍出现财政赤字。
人口单薄,过着一种沉闷的生活。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幸福,要是有,又是什么?
贵族子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养尊处优会产生纨绔,也会孕育思想精英,托尔斯泰派遣他们去接受精神的危机,继而探索什么是幸福。
小说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但在真实的条件下发生,派生出故事和细节,真实是虚构的源泉。
《战争与和平》启用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战争。
托尔斯泰写了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是为了布置一个大舞台,好让各色人等在上面表演。
这一出大戏最终还是归结到那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

《战争与和平》中,两个人历史上真有其人,一个是库图佐夫,一个就是拿破仑。
真实的人物对于写作人来说存在一个悖论。
一方面觉得心里很踏实,我的虚构有一个靠得住的背景,靠得住的人和事,可能因循合理的逻辑,不会出大错;
另一方面问题也来了,能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
我们离托尔斯泰已经那么远了,离开那一场战争也很远了,却可以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带着这样一个信任度阅读。
我们这些写作者都是小人物,不敢像托尔斯泰将那么宏大的造物作为故事的背景,必须谨慎地对待我们的能力。
托尔斯泰就敢,这就是大手笔,是虚构中的造物。
由于时空隔离,我们无从认识库图佐夫,也无从认识拿破仑,当然关于他们的图片和记载有很多,但那都是概念的,要尊重他们的真实性。
在小说里,我以为相对来说是有自由的。
这两个真实的人物,如何与虚构人物发生关系?
对于安德烈和彼尔,两个历史人物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他们的故事是怎样从这两个人物身上发生和繁衍的?

为什么不是让其中的一个人去完成思想任务,而是要用安德烈和彼尔两个人完成?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经历,走上不同的道路,最后相辅相成完成答案。
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知道的世界,可以感受、求证、传达;
还有一个信的世界,可以相信,却无法证明。
安德烈是知道的世界。
他非常聪明,看得清贵族阶层内部所有弊病,认识到沙皇体制需要改良。
彼尔却对现实生活严重缺乏常识。
但是他信,总觉得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一种力量,驱使或者暗示着什么,但又不很清楚,茫然的信念使他怀着一种莫名的快乐。
胖乎乎,又高又大,对人友善,毫无成见,赤子之心,像美国电影里的金刚。
安德烈的世界一切都是确定的,他的出身、谱系都非常清楚。
他知道贵族的责任是什么,为了维护荣誉,要和拿破仑作战。

彼尔是什么都不确定的人,包括出身。
托尔斯泰对彼尔寄予的希望更大一些。
似乎宗教历史或者民间传说有一个共同之处:
凡是伟大的人,天地要给大使命的人,出身都很暧昧。
比如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耶稣生在马槽里。
彼尔的出生也有问题。他是莫斯科一位大公爵的私生子。
大公爵有无数私生子,但他只认彼尔一个,他把这个孩子送到法国去受教育。
法国是一个有着自由民主思想的国度,当彼尔再回到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怪物。
他的行为举止不合规矩,不通世故人情,更要命的是他崇拜拿破仑。
他的人生充满不确定因素,非婚生,在法国受教育,再回到俄国,突然之间成为富人,在非理性的遭际中改变着命运。

安德烈对事物拥有理性的判断,彼尔是感性的,有着对玄思的爱好。
安德烈很有行动能力,当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做得很成功,彼尔是没有实际能力的人,生活在冥想里。
看看两个虚构人物和两个真实人物的关系。
我将他们组成两对关系,安德烈和库图佐夫、彼尔和拿破仑。
库图佐夫和拿破仑这两个历史真实人物的出现,是为开拓虚构世界的空间。
库图佐夫担负起了安德烈的命运转折的重任。
他有一种什么特质呢?
他懂得有一种东西比人的算计和意志更加强大,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库图佐夫有点像东方的哲人。
安德烈到库图佐夫那里报到时很积极,对这场战争充满热情,觉得是挽回皇权荣誉的伟大事业,在内心深处是期待以战争来激励日常生活中的颓唐。

结果,安德烈发现,战争不关乎荣誉,只关乎各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是一个名利场。
更使他感到很奇怪的,他的外交官朋友几乎把彼得堡的沙龙整个儿地搬到了战争的前方。
同样的喝酒、纵欲、谈女人,糜烂和腐化在这里照样上演,他寄予战争拯救的希望开始崩塌。
他在一场战役中负伤,突然发现世界上有一种感觉是疼痛,比什么样的占领和光荣更强大,更有覆盖性。
在安德烈的世界里,一切都井然有序,逻辑严密,都是可以推论的。
但安德烈体验到了无可控制的力量,思想得到了一个嬗变的机会,开始向着彼尔的“哲学想象”进发,这个嬗变以抑郁症为表现。
他对战争不关心了,对政治不关心了,保皇党、革命党都不干他的事,一心就在养育儿子。
当他在庄园里平凡度日的时候,和彼尔相遇过一次,这正是彼尔经历着思想上的蜕变的时刻。
与安德烈相反,彼尔处在激动兴奋的状态,昂扬情绪感染了安德烈。
这个时期,安德烈遇见娜塔莎。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寄予重托的女性。
她和彼尔出场都是不让安德烈消沉,他还没有走到终点,还要再受历练。
安德烈迅速爱上娜塔莎,对生活产生新的希望。

他觉得知道什么是幸福了,抑郁症不治而愈,重新对战争、政治有了兴趣。
政治也呈现新面貌,因为拿破仑战争影响,俄国开始自省体制和制度,兴起改革。
可彼得堡照旧充满着庸俗的琐事,安德烈所寄热望的改革派发起者其实是在玩弄权术。
娜塔莎也背叛了他。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他的私人生活失败了,对战争的热情早已消退,真不知道拿什么救什么。
他又一次参战,受了重伤。
在伤痛和死亡跟前,他的名誉和受辱变得渺小,爱情和仇恨也不重要。
和娜塔莎的不期而遇自然令他欣喜,但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他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死亡。
死亡是一个需要“哲学想象”才能够处理的问题,对注重实际的安德烈是极大挑战。
让安德烈去经历死亡,这是托尔斯泰给的大任务。
将蹈入死亡的神秘国度时,他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所有的人和事,爱也罢,恨也罢,亲也罢,疏也罢,所有的存在都融为总和。
就像彼尔的世界,一个抽象的世界,所有的具体性,都在这个总和当中模糊了差异。
所谓具体性,只不过是这个总和,随机分配到每一个人的世界里去,最终又汇总来了。
这个境界连作者都不了解,他用思索,也就是“哲学想象”进行描摹,将描摹的图景送给笔下的人物安德烈。
死亡这个最大的虚无终由安德烈走了进去。
拿破仑和彼尔也是一对。

拿破仑最早出场在大家的口传中、上层社会的沙龙里,贵族,尤其是贵夫人,谈到他的时候,心情很奇怪,夸张的厌恶和恐惧,并从中享受着某种刺激的快感。
他的力量和野心,迷惑着人们。
彼尔崇拜拿破仑,安德烈对拿破仑也心存敬意,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暗地里渴望成为拿破仑这样的人。
拿破仑,破落户出身的新皇帝,骄傲,粗野,却活力充沛,充满希望。
彼尔是拿破仑公然的崇拜者,一个异类。
可上层社会接受了这个异类,因为他得到了巨额遗产。
彼尔艰辛的思想历程开始了。
笨拙的彼尔从来没有被海伦放在眼里过,以她的肤浅远不能认识彼尔的价值,她依然过着交际花的生活,让彼尔蒙羞。
彼尔不明白生活怎么变得那么糟糕,莫名其妙地有了妻子,莫名其妙地妻子背叛他,再又莫名其妙地和妻子的情人决斗,一切都很低下,使他讨厌。
他离开莫斯科,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想离开这些远远的。
马车在夜间停在一个驿站——

驿站是特别会发生故事的地方,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换马,歇息,素昧平生的人不期而遇,脱离生活常规的离奇的邂逅就发生了。
在驿站休息的时候,彼尔遇到一位共济会的长老,我觉得很像甘地。
托尔斯泰似乎内心趋向东方哲学,西方哲学的推论方法推不下去了,就会把希望寄托于东方神秘主义,比如库图佐夫的思想方式,安德烈临终前的状态,都有着东方哲学想象。
长老说,你的生活很杂乱,那么多过剩物质,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荒唐的行径,必须清理自己的生活,共济会可以帮你做到这些。
彼尔参加了共济会,好像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方向。
彼尔进入共济会好比安德烈进入战争,精神振奋。
很快,失望就来临了。
他发现共济会组织的阴暗面,最终被驱逐出教会。
他再次消沉下来,回到了和海伦的婚姻生活当中,抑郁症发作。
在思想历练途中,他们总是要患抑郁症,抑郁症其实是嬗变的前兆。
精神跋涉的旅程是相当漫长的,什么是幸福的答案,还很遥远,可正在接近它。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关系到安德烈,却对彼尔的生活起到推动作用:
那就是娜塔莎被海伦的哥哥诱惑,背叛了安德烈。

娜塔莎所以受诱惑,与爱情无关,有负气的成分,也有补偿的成分,更因为娜塔莎是那种反叛的女孩。
这次荒唐的行为及时被发现和制止,可她和安德烈的婚事也完了,严重伤了安德烈的心。
彼尔极其愤怒,和海伦决裂了,把财产留给海伦,脱离了这个家庭。
这时,法军和俄军在莫斯科近郊激战,库图佐夫作出大撤退的战略,拿破仑即将占领莫斯科。

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就要进入虚构人物彼尔的情节了,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开始呈现。
人性的戏剧,即将在历史的时空场景中上演。
这是《战争与和平》中最令我感动的情节。
彼尔走回莫斯科,在长老的书房里度过整整两天足不出户的日子,我将它称为静修的两天。
这静修又有一个现实的名称,就是酝酿刺杀拿破仑。
彼尔变成了一个英雄主义者,就好像安德烈后来变成一个玄思者,这两个思想者就这样交汇着跋涉,走着现实和虚无的之字形路途。
法国军队逮捕了彼尔,成为战俘。
彼尔穿着破衬衫,一条士兵的裤子,农民的外衣和帽子,没有鞋子。
可他却很宁静,长老所说的过剩的物质全弃下了,生活变得极其单纯。
在此,我们又发现一个总量,罪与罚的总量,好比安德烈临终前觉悟到的爱和恨的总量。
这一个总量是天意,又由上天来分配在具体的人身上,这便是命运。
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个别的局部的命运后面的全体性。
托尔斯泰让这两个人分别履行思想的职责,什么是幸福?
安德烈在死亡中找寻,彼尔在活着里寻找。
安德烈安详满足地死去了,彼尔如何活着呢?
妻子海伦死了,彼尔和娜塔莎结婚了,如同民间故事里说的,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的幸福生活其实是非常日常的,经营农庄,养育孩子,和谐的夫妻之道,不受穷,但也绝不过奢。
在这里,我看到了托尔斯泰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在《复活》里面也出现过。
当聂赫留朵夫跟随苦役犯走过西伯利亚的流放路途,最后去拜见西伯利亚要塞司令,在司令家中,他看到了一种和谐的生活。
司令一家都是性情和善的人,他的女儿请他上楼去看看刚生下的一对小儿女,看着婴儿酣甜的睡态,他非常感动。
经过受苦,他发现人道的生活就是这样简朴却不受罪,问心无愧,生活最好的境界就是这样的。
彼尔和娜塔莎结婚,生儿育女,养家活口。
但显然托尔斯泰还不满足,还有更宏大的理想,关乎全人类的,他给了彼尔一个任务。
时常地,彼尔会出远门,去彼得堡,娜塔莎以为是处理一些田庄上契约方面的事务,可彼尔的神情却显得很神秘,似乎和政治有关系,好像是在和十二月党人接触。
娜塔莎确实在安德烈和彼尔的思想变革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托尔斯泰总在女性身上赋予神圣的使命。
托尔斯泰笔下,女性是非常感性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热情的、生机勃勃的形象。
娜塔莎的热情具有建设的力量。她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汲取快乐。
抑郁症时期的安德烈,就是被她的快乐唤起了对生活的兴趣,又在彼尔混乱纷沓的思想中,呈现出单纯朴素的情感,由此引导走向生活的本义。

有一件事情我企图寻找答案。
就是为什么让娜塔莎犯错误。
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是有严肃社会意义的,娜塔莎则是一次真正的错误,好在托尔斯泰把她推到悬崖边上,又及时拉住了。
为什么要让她有这个污点呢?
大概因为托尔斯泰让她也成为一名罪人,再得到救赎,这才有资格拯救两个思想家。

让娜塔莎在我们共同的罪愆里面也承担有一点罪,然后再拯救她,就好像一次冶炼。
当安德烈遇见她的时候,她一派天然,纯真无邪。
而在彼尔的爱情里,她已经是个小罪人了,但这并没有贬抑她的价值,反而使彼尔更加尊敬她。
这不是指彼尔的宽容有更多的爱,而是说,娜塔莎的纯洁里已经有了理性。
她不单纯是个小女孩子,无来由地快乐,而是一个经历过生活的女性,好像在马槽里生下基督的圣母马利亚,是受过孕的处女。
对聂赫留朵夫的救赎,是由玛丝洛娃这个堕落女子来实现的。
这些戴罪的女性,就像折断翅膀的天使误入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