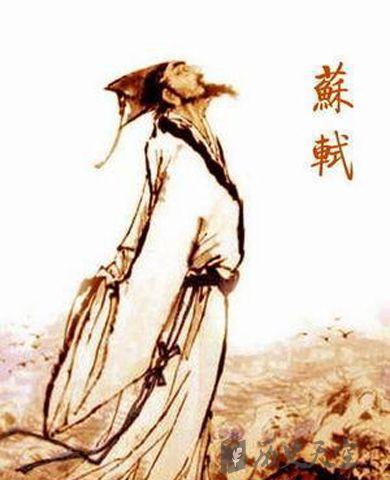
初、高中语文课本告诉我们,苏轼是中国豪放派文人最著名的代表(几乎没有之一)。确实,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至今读来依然大气磅礴,豪气冲云霄,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愉悦感。我也打算从此说起。
且再读这首豪放“绝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读起来朗朗上口,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短短数百字,仿若古今沧桑已俱在其中。

而在细读之中,我似乎嗅到了中国文化里的虚无本质。你看周瑜、曹操、诸葛亮这些影响着其时代命运的人物,当年的美人大乔小乔,如今安在否?纵是“羽扇纶巾”,到头来还不是“灰飞烟灭”……这里,苏轼的皮相虽然豪气冲天,骨子里的基因却是虚无的,至少词人的聚焦点是历史的虚无。而人生如梦的感慨,预示着自己也会走进历史的虚无。
关于历史或现世生活的虚无感,还能从苏轼的诸多佳句中发现:

如果说虚无感是流淌在中国文人血液里的一大基因,那么这一文化基因从何而来呢?——这就不免牵涉到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了。
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历史地看,差不多一直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线的。道家虽然讲“自然无为”,但也并没有真的忘记为庙堂之高的君主出谋划策,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说的也基本是圣人的事。圣人是谁呢?归根结底,圣人要么就是统治者,要么就由统治者代言(天子替天行道)。这一点,儒、道两家并没有根本区别。
至于佛教的哲学,在印度虽有严密的信仰,传到中国则逐渐演化为多个分支,其中又以“中国特色”为主的禅宗学说影响较广。尽管信佛的人中不乏真正的佛教徒,但毕竟是少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很有限,至少远远不能和儒家相提并论。而中国的传统文人,可以说得意时几乎没有不追随儒家入世思想的,但现实坎坷、复杂、多变,导致入世的文人多不能如意,而失意之后,他们又难免从道、佛寻求精神慰藉。

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这看起来是在说儒释道的不同作用,实际上仍是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一句妙言。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这样的儒家情怀,在苏轼、李白、杜甫、陆游等传统文人身上无一不存在,说白了,绝大多数传统文人都有居庙堂之高的政治抱负。而一旦政治抱负不被朝廷待见,仕途受阻,便难免郁郁不得志,人生的虚无感也趁机接踵而至。
因着政治上带来的人生虚无感,一些境界不高的文人便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连浪漫如李白也不能幸免),或者感慨仕途的险恶,再不屑于与“宵小之辈”争名夺利,而另一些境界较高的文人,经由仕途失意,(自诩)看穿了一切入世作为的虚无,所以,有的转而寄情山水,有的以酒自醉,有的参禅悟道,有的退隐逍遥,算是获得了别样的感悟,升华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如陶渊明、白居易)。当然,也有些文人,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入世的情怀,苏轼即是典型。被朝臣诬蔑、被流放蛮荒之地、被党同伐异,苏轼也总会在“有道难行不如醉”的牢骚之后,聊发他的少年狂,指望朝廷许他“西北望,射天狼”。

我从苏轼身上看到了中国文人频频上演的一出崇高悲剧。说崇高,是感于他们心底长盛不衰的对天下苍生的赤子情怀;说悲剧,是哀于他们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不得志。这种悲剧,不仅是说他们仕途失意难以避免,更是指他们没能跳出官本位的思想,始终以为要拯救苍生,就得入朝为官或是行军打仗,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否则,诗歌写得再好、艺技再高超、修养再高岸、科学研究再厉害,也只能是聊寄余生,怅然若失。
或许,更高的悲剧在于中国文人在信仰上的虚无。中医认为人的死就是个元气耗散的过程,用文人陆游的话说,就是“死去元知万事空”,换成用孟郊的诗就是“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所以说到底,不仅升官发财注定虚无,就是艺术创作也是虚无,就是得意失意也是虚无,善恶到头也是虚无。虚无的虚无,终归于无(老子)。我们没法断定“人生是虚无”的观点的对错,只能说,这种思维方式是独断的,没有深思死后的世界,直接斩断了对死亡的多元探索。

说起来,我们伟大的孔夫子也难辞其咎。他的“未知生,焉知死”无形中给中国文人对于死亡的认识奠定了基调。其后的中国文人对死亡的认识总体上是肤浅的,更准确说,连肤浅都谈不上,因为死亡问题在中国的文化里,实际上是被搁浅的,老庄倒是略有论述,但实在是杯水车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