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29日,是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的九十寿诞。对很多大陆读者来说,或许并不诗人痖弦2005年回大陆期间,于11月12日在广西师范大学做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诗歌演讲:
咱们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样样都用诗来表现。你看,夏天,到人家里去,咱从前没电扇,就拿一把扇子,扇子上面有字:“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理不通。”为什么?你热我也热呀;到庙里抽个签,签条上是诗;家里小孩夜惊,贴个小红条在墙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敬茶给客人,茶杯上有诗句:“可以倾心”或者“壶中日月长”;情人谈情,把诗题在红叶上,写在手绢上。
诗不但可以供人欣赏,而且还可以吟唱,中国的戏曲就是诗句嘛。甚至于说,连官方的告示都是用诗句来写的,以便于老百姓来记诵,便于记忆,便于传诵。武松到咸阳道中,看到那官方的告示,如“有大老虎在吃人,不能上山,结伴同行”等等,都是用诗句来做的。所以在中国可以说,从天子到庶人都写诗。比如唐朝,坏诗人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写,当然会有很多坏诗人。但是没有关系,乱是繁荣的另外一个表象,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是乱的。当时附庸风雅的人,也会弄假成真,最后慢慢地,经过时间老人的耙梳整理,坏的作品不见了,好的作品留下来。所以,在我们中国,诗是人人都会两下子的。医生也会,叫儒医;将军也写阵中诗,叫做儒将;商人也写诗,叫做儒商。人人都会。
可是到了新文学运动以后,新诗出现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它很有意思,就写,写着写着,把它慢慢专业化了,就变成只有诗人才写诗,一般人就不能写了。报纸上也有诗,但一般人看报,一看到诗眼睛就迈过去了:哎呀我受不了,每个字都认识,接在一起,不懂。所以慢慢地诗歌就专业化了,这对诗歌是一个很不幸的发展。
很多人认为诗是高中生的玩意。生日啊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庆典哪,总是要送一首古典诗才象样,觉得现代诗不够大气,不够正式,不够尊重,所以新诗就变成了青年人的玩意儿、恋爱中人的臆语,变成不好的。因此我主张恢复我们中华古国过去“人人都是诗人”的境况。专业的诗人是狭义的诗人,广义的诗人是也写两个句子好玩儿的这些人,人多了就一定会产生好的作品。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就定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
昨天晚上肖先华先生,他是广西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生,他现在马上要设计一个大约四千人的诗歌朗诵会,我就跟他谈桂林的历史。我发现桂林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城市。你看我们的老校区,就是靖江王府,明朝朱元璋的侄孙,成为靖江王;还有一个朱元璋的儿子在我家乡,河南南阳,那儿也有一个类似靖江王府的地方,不过保存没有这边完整,只有一个假山留下来。我想象当时南阳的唐王的王府,其各种建筑体制一定跟靖江王府有点像,所以到这儿有点回乡的感觉。南阳破坏得很厉害,基本上没有了,只有个假山在。非常好的校园,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校园,可是从来很少一个校园里有一个王府的,这是有王气的地方。
那么桂林为什么又是一个文学的城市呢?比如说,在我们老校区的校园里颜延之读书的那个石洞现在还在呢。中山先生1922年北伐的时候,大本营就设在靖江王府,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些石刻,“中山先生精神不死”。唐朝的李靖,也是个大文豪,在这里待过;杜甫没有来过桂林,但是非常向往桂林,他还特别有一首诗的两个句子是歌颂桂林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真正适合生活的地方,最宜人的地方只有桂林;韩愈是来过桂林的,他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形容桂林山水的秀丽。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句子是宋朝王正功的,真是甲天下。桂林的山是上帝给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加拿大是大山大水,但是山都没有线条,她的山是物质的山,不是精神的山;我们看的桂林的那些山,都是那些大文人题了字歌颂过的山,是文化的山,是伦理的山,是我们历史的山,情况完全不同。在加拿大看到大山大水就是物质的,那么大,那么高,没有其他意义;我们的山是文化的山,所以韩愈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前天我们去游了漓江,其中有个小村子我特别喜欢,叫做兴坪。我跟我孩子说,我将来呀,百年之后啊,就把我的那个,随风而去的那个(学生笑),撒到兴坪算了。
唐朝的储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柳宗元、李商隐,宋朝的黄庭坚,通通都在桂林待过,你说她不是个文学的城市吗?你说她不是个诗歌的城市吗?在这样的城市里,如果以后没有再出诗人,是不应该的,所以希望在桂林,在这个诗歌的城市里面,人人都能够成为诗人。珍惜这个山水,对花落花谢都有敏感的人,我称他为广义的诗人。不写诗的诗人也是诗人,是广义的诗人;把这化成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是狭义的诗人,每个人都应该是个诗人。我这个题目是这么来的。
现在我想分做几条来谈,如果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诗人?刚才已经说了一点,现在我们把它规律化,演绎成几条:
第一条,诗人是对生命认真的人。诗人就是真人,最热爱生活的人,最认真生活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过着自己日子的人。通常我们说,诗来自生活,不是来自学问。学问越大,诗学得越反,因为学问是逻辑的,是理解的,是分析的,而诗是纯粹感觉的,这个感觉是与生俱来的。

河南有个作家,是南阳作家协会的主席,叫二月河,他的历史小说红得不得了,而且都拍成电视剧了。他看到我时说:我对诗人充满了敬意,我什么文体都可以写,就是这个诗我没办法。你说我写个散文,我凑合着也能写得出来;写个小说呢,更是我的专业;写文学评论,也行;你说写诗,我一句也写不出来。诗人是天生的,我没办法形容,诗就是一种特异功能,呵呵,特异功能。
其实没那么神秘。诗就是认真生活的结果。诗人能够面对生活,忠于生活,善于感觉生活,理解生活,提高生活。我们常常说:诗的生活,生活的诗。先有了诗的生活,才能有生活的诗,生活的深度就是诗的深度。假如一个人不爱在生活上作思考,糊里糊涂地过日子,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诗人。所以诗人都有几分自恋,这没有关系,不要太过分就行,诗人是自恋的。长城很多人都去过了,但是诗人去了长城,那就石破天惊,不得了了,一件大事情了,因为“他”来了。
有了诗的生活才有生活的诗,没有生活就没有诗人,所以诗人是认真于生活思维的人,对于风吹水流花落花谢都有感受。一个花落了,对一般人来讲,那算个什么事呢?对诗人来讲,可严重了,落花有死醉楼人哪,落花声,那跳楼的人,“啪”地惊呼,就听到了,那不是好大的事么?所以诗人,他把所有的生活,把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扩大,诗人有扩大生活的能力。
风、花、雪、月,通常我们拿这些来形容比较浮浅的浪漫主义的东西。通常有这样一种嘲弄:你这个玩意儿,就是风花雪月嘛。其实风花雪月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如何去用新的观点来看风、看花、看雪、看月。我们当年在编《创世纪》的时候,编过四部文集,第一部叫《风之柳》,第二部叫《花之声》,第三部叫《雪之韵》,第四部叫《月之魂》。多好,是不是?风花雪月嘛,新风花雪月。所以有人说,你这个是感伤主义嘛。感伤主义也是一句不好的贬义的词句。其实感伤是很重要的。多愁善感,通常也是嘲弄诗人的句子,其实多愁善感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这个愁你这个感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有创意。
中国有句话叫“江郎才尽”,江郎才尽了,完了,他不能再写东西了。江郎的才会不会尽?不会尽。不是江郎的才尽了,而是江郎的生活尽了。江郎没有生活了,江郎失去了生活就写不出诗来了,生活与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密切。我们看到两岸的情况都有点像。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势大好,所以很多的文人纷纷地下海,更换跑道,本来写诗的去做生意了。这些人都有一个想法:我把钱赚足了再来写诗。这好像是个如意算盘,其实很难回头,生活的步调乱了,很难再加以整理。
一首诗是一个心情,是一个情绪,这个心情,这个情绪是根据你的年龄走的,不是永远可以保持的。超过了这个时段,你再也不能够把这个时间追赶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能说我把钱赚饱了回头再来写诗,不太可能,所以,写诗或者从事文学后再去改行做生意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台湾更是如此,台湾的人们连广播、连广播电视台,连电视台都不上了,认为那个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那就是面对一盏孤灯在写诗、写小说、写你的文章就可以了,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跟作品分离的话,往往伤害了作品的内涵。那谢灵运是多大的诗人,他写山水诗,但他官也做得不小,所以他变成双重人格,他一方面隐逸于山水,另一方面又去做官,所以谢灵运的诗就不能够跟陶渊明比。陶渊明是真正的能人,真正做活的,他的生活跟他的艺术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谢灵运的诗,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修辞,但有时候仔细一分析,里面有作伪的成分,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说,你的诗写成什么样你的人也该是什么样的,诗很宏大你这个人也很宏大。也不是。有时候,是诗人的内在,是他的精神视野很宏大,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小人物也说不定。比如说读传记,很多人读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传记就非常失望,他在诗里面简直是一个民族的歌手,其形象何其宏伟,但在他的实际生活里,他只是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报纸的小记者,根本乏善可陈。严格说来,他只写过一本诗集,但是《草叶集》最初出版,没有人知道惠特曼是什么人,他就弄些假名字,写评论,“我们美国最大的诗人诞生了”等等,自己吹自己。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他的诗的内容和实际的生活好象是不大对头的,这没有关系,是因为他希望变成象他诗中的那样一个人,他的精神视野自然是宏大的,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

图 / 台湾诗友与痖弦(后排右一)
第二条,诗人是感情、感性思维非常强旺的人。什么东西都是通过感性的,不是理性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文学、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好象车的双轮、鸟的双翼一样,必须要平衡才能使人正常。但是我必须说,诗人是非理性的人,诗人是不正常的人,越正常越糟。不正常才能写诗,非理性。
第三条,诗人是非常喜欢文字、语言的人。诗人对语言非常敏感,对文字特别敏感,而且对形象化的文字或者文字的形象化特别有一种思维的惯性,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个画面,什么东西都想用画面来表达出来,这是诗人的本性,诗人都有这个能力。
人有治河的有治矿的,诗人是治语言的人,他治语言,他是个语言的大行家,什么语言在他那里他都喜欢去跟它做游戏,跟它来对话,所以他常常为商店取名。台湾现在诗人为商店起名字的很多,大陆现在渐渐也有了,就是想得很绝的名字。卖面的叫“面面俱到”,卖螃蟹的叫“横行霸道”,服装店叫“一种主张”。台北有一条路上有一个服装店叫“一种主张”,乍一想,这是卖什么玩意儿的,叫什么“一种主张”,可再想想,也对呀,我们穿衣服穿出我的主张来,穿出我的风格来,这不就是一种主张嘛,生意还挺不错的;还有一个美容屋,美容发廊,叫做“远离非洲”,本来黑乎乎的一个人进来以后变成小白脸了,呵呵,他美容了;商业广告也受到诗人的语法的影响,说“我们是种房子的人”,我们不是盖房子的,我们是种房子,我们的房子好像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那样根深叶茂地好啊,“清晨从鸟声中醒来”,你看这句话,会有多少人来买这个房子,清晨是鸟把你叫醒,这房子的地段太好了。孟母到了这里就不要再搬家了,这地方好啊,距离菜市场近哪,距离小学又近,送孩子可以走到学校去。这些都是受到诗语的影响。
诗人是个大行家,我曾经在《联合报副刊》上举行一个特别的专题,叫做“美丽的市声”,市场上传来的声音,桂林市的市,声音的声。但中国传统的市声是很嘈杂的,“王二麻子剪刀”,“真王二麻子剪刀”,“真真王二麻子剪刀”,叫喊在市场上。我小的时候,我爹带我到铺子里去,每一家铺子都挂两个牌子,黑底金字,有的是黑底红字,永远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就这一句话,已经用了几百年没换过。可是现在的商业广告,争鲜斗艳,已经侵入到诗歌领域去了。所以当我们“美丽的市声”这个专辑出现以后,很多厂商都找诗人说,“哎,怎么样,你来帮我设计一个?”内衣广告,这内衣美得不得了,美到什么程度呢?“让午夜苏醒,清晨燃烧”,你说那不是诗吗?午夜可以苏醒,清晨可以燃烧,大家睡不着觉了,因为内衣的关系,呵呵,好听吧?所以大家为想文案绞尽了脑汁,通通都学诗人的标准。
郑愁予的诗,最广为流传的是那首《错误》,其中有一句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也都在学这个语调,把新的内容装进这个句型里去,甚至影响了政变。你这规格学了大陆的海归派对不对?你这海归到底是归人呢还是过客?海归分作两派,一个过客派,一个归人派,都是受到诗歌的影响。所以诗人是热爱语言、提高语言、丰富我们语言内容的人。
我们常常说,歌德是德意志语言的创造者,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的创造者,写诗跟语言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诗人甚至溺爱他的民族语言,爱到溺爱的程度,创作了好多新的语言,丰富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譬如说,我们有很多成语,很多大家用得已经不觉得是诗的语言了,这哪是谁的作品嘛,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一个人失恋了,我们说,哎,你老兄何必那么悲壮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啊。这不是引的古人的诗吗?所以这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了。诗人从实际生活里提炼语言,再把更好的语言还诸给社会。所以我们的语言如果要保持它的活力的话,即如果它不会老化,不会变成语言的化石的话,就要靠诗人多多去创新。
我是河南人,1949年离开河南的。等我再回到河南的时候,我的河南话变了,速度变了,节奏也变了,语汇也变了,整个都变了。所以当我说河南话的时候,我姨就说,“你看你这味儿,多少年了,这个话我都没听说过了,你怎么还会说呢?”为什么?因为我的话是止于1949,是老河南话的活化石,很有研究价值。
社会会变,语言会变,节奏会变,跟着社会整个的大的脉搏在前进,所以诗人一定要知道,语言象河流一样,现在新的语言流向哪里,什么样的语言正在死去,什么样的语言正在诞生。没有表达力的语言慢慢就死掉了,没人再用了,继续有表达力的语言、生活的语言在诞生着,诗人一定要完全地掌握这种变动,才能在语言里做一个领导者,做一个领先者,诗人是领导流行的人,可以这么讲。
第四条,诗人是有一贯人格的人。诗人的人格是一贯的。诗不是一种技术,诗是一种思想,诗是一种人格,诗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最高显现,诗是非常高贵的。你看,所有文类都没有一顶帽子,只有诗人有一顶桂冠。
写散文的人也写诗,你永远不要只夸他散文好。“哎,光中先生,我觉得你的散文写得好啊。”就是不提诗,他心里不舒服。你可以提诗而不提散文,因为散文家没帽子,诗人有一顶桂冠,这个帽子很重要。所以诗学是文学的贵族,诗常常体现一些非常高贵的情操,诗是一贯人格的保持。
诗人有他一贯的人格,有他的道德精神,有他不变的情操,所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常地严谨,也非常地华丽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炼字、炼句、炼意,炼字就是语汇,炼句就是整个的句法,炼意就是意境。我常常说一句话: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人(人的品格的修养)。诗人在开始的时候比的是技术,谁的句子用得漂亮,谁的哪一首诗写得特别好;但最后比的是精神人格,比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完整不完整,他的人格统一不统一。如果他精神世界不完整,他的诗虽然可能会有些好诗,但他只是个小诗人,或者只是个好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一定有他的精神品格。如果让在我们中国选一个诗人,那一定是屈原;选两个可能杜甫在里边,李白就有点危险;选五个,李商隐可能会在里边,选四个李商隐在不在里边很难讲,但是屈原一定在里边,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人格精神的一贯性。屈原是个投江自沉的诗人,我们都是含着眼泪想念他的,实在是伟大,作品的风格和人格产生高度的统一性。这样的人,我们说,他即使不写诗,但他是把诗当作日子过的人,他也是个广义的诗人。这样的人生成立了,就是个诗的人生。
我常常会想到地域对人的影响。比如刚刚说到桂林这个地方,这里出过很多古人,大文豪,大诗人,他们留下了很多题咏、歌颂这山水的诗句;新文学运动以来,很多诗人曾经在这里出版他们的诗集,1942那一年对桂林特别重要。比如说写十四行诗的冯至,当时这边一个出版社叫“明日社”,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就是1942年在明日出版社出版的;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也是1942年在桂林出的;还有李广田(就是和何其芳他们写《汉园集》的,好象做过广西大学校长,《阿诗玛》这个长诗是他整理出来的),他的《诗的艺术》也是在桂林1942年出版的。
所谓人杰地灵,诗人可以称为地灵上的人杰,所以诗人通常也是一个旅行家,喜欢出去跑,喜欢自然,喜欢看瀑布一样的生活,喜欢收集不同的语言。象屠格涅夫不是写散文诗嘛,屠格涅夫的小说其实也是广义的诗,特别是《猎人日记》,都是诗意很浓厚的。他非常喜欢听瞎子的唱歌呀,乞丐的表演呀等等,从那里面收集素材,写随笔,写日记,抄抄写写。所以诗人不但是勤于思想,也是勤于动文字的人。
假如说一个人写日记,每天都写,写了三十年,最善于用他自己相信的文字来整理自己的思想,记录每天所做的事情;假如一个人跟朋友通信都写得很长,我们年轻的时候通信都通得很长,现在电话那个叫短什么?短信?那没出息的,那不行,写那种没有出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鸿来雁往,等待绿衣人,今天有信来。现在那寂寞的邮筒,现在的邮筒非常寂寞,没有信件,那些都是广告,叫“le’se”信(垃圾信),真正的信没有了。我是一个最喜欢写信的人,我准备捐两千封信到台湾的文学馆。我每天大概要写三十封信,写信的对象大作家也有,高中生也有。我太太常常嘲弄我说:这个人喜欢写信,哎呀,那个痖弦哪(对小豆笑,“对不起呀,我骂你妈妈”),真喜欢写信哪,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如果痖弦请你吃饭,你寄了封信给他,说:“痖弦,那天菜真好,谢谢你请我吃饭。”痖弦包准还要回你一封信,信上说:“不谢!”呵呵,到了这个程度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喜欢写信,我写一整天的信都不累,因为我觉得好像看到这个人一样。胡适先生也喜欢写信,当然我不能跟胡先生来比。胡先生写信的时候下面垫一张复写纸,写完之后稿子就留下来。有时候在外边旅行没有买到复写纸,或者复写得不清楚,他会写个简单的信说:我先把这个事告诉你,正式的信过几天再写给你,因为我还要去照相,还得请人抄一遍。所以胡适的信都非常完整。我的信也是,因为有影印出现了,通通都是有复信在后边。现在很多人在收集信了,因为这东西少了,所以我打算捐两千封信,这里边有巴金先生的,有冰心老人的,因为我这个岁数也跟上伺候他们了。(呵呵)北京的那些名角不是经常炫耀“梅兰芳老板我伺候过”,我说“冰心老婆婆我伺候过”。所以假如说一个人,他写了三十年的信,记了三十年的日记,每天不断,他不是作家也得是作家,他非是个作家不行了,因为他对文字太了解了。
我们学中文的人,都受过诗词歌赋的陶冶,大家的样子跟言谈举止几乎都一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就觉得这边中文系老师和同学们喝酒跟台湾完全一样,说话的内容通通都一样,所以我觉得两岸的结合不象犹太人,犹太人的结合是用犹太教,我们没有国教,佛教虽然非常普遍,但也不能算是国教。我们用什么来结合?用文化来结合,用文学来结合对方。两岸不管是哪一个侨居地,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政治结构,只要提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方式。因此作家为了扩大他文字的想象的领域,扩大他生活的领域,他就变成了旅行家。
现在又有旅行文学的出现,旅行文学是“带着故乡去旅行”。有一首诗是我读大陆的年轻诗人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写得非常好。他写一个帽子,就是乡下人的斗笠,他是这么说的:离家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戴着那个破帽子(破斗笠)?对方说:不,那是故乡的屋顶。头上戴着故乡,也真是绝了,每个人的故乡都永远戴在你头上,如影随形,所以诗人是永远用他的故乡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人。但是那个写《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英国作家伍尔芙(后来跳海死了),她说“你永远回不了故乡”,因为你回去的故乡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故乡了,就象你在行船,这一秒种看到的水已经不是刚才的水了,故乡的变化很大,不是说回去就能回去。所以爱乡爱旅行的人,故乡跟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斗争,这些焦躁这些思考就成为文学最重要的题材。
在广西师范学院我曾谈到华人文学,现在的华人文学可不是从前的华人文学,从前的华人文学是“我是广东人,我想念我家乡”,就是这么简单;现在不是,现在每一个侨居地的新生的华侨,他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成长与经验都不一样了,虽然都是用汉语写作,但是每一个地方的文学都主张彰显他们的自主意识,都有他们的地方色彩。“马华”(马来亚华人文学)有马华的特殊风格,“越华”、“日华”、“美华”、“加华”,所有的这些“华”字的文坛,虽然合起来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坛,但是这些文坛是统统都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习惯于这样来衡量华侨,对其他人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写?”因为其中有拥抱和出走等等。有些人主张出走(从中华母体中出走),有些人希望拥抱,有些人是徘徊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可以说非常地复杂,因为复杂所以丰富,因为苦闷所以深刻,这些题材都有,甚至提到中国又爱又恨,等等非常复杂的情形。我们赞成这种真正的想法,因为如此才能把一个出去了好几代的人的想法说出来。文学中没有对错,不是说“你这个人忘本”,那些浮浅的价值判断我们把它抛开,我们说只要你真正写出你真正的感觉来,就是为我们中华的大的文学,为我们汉文的写作,丰富我们写作的内容,一定要这样看,所以说诗人是永远纠缠在故乡和域外的人,这也是诗人永远都在出走和拥抱之间徘徊的原因。
今天的华人文学已经是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各种人出出进进。将来大陆也应该像台湾一样,现在大陆出国一定要外边邀请的,上个报告啊,上级要打好多圈啊,才能让你出去;台湾现在可以出去,但是没有一个留在外边,都回来了,即使办了移民的人过两天他又回来了,两地来回跑。所以中心和边陲的观念也变了,结构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支流和主流的观念也变了,大师在哪里,哪里就是主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经常地旅行,经常拿着故乡作为基础,带着故乡旅行,跟故乡作对比,将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去感受着,一定是具有现代诗的性格的,一定能写出具有现代色彩和现代性格的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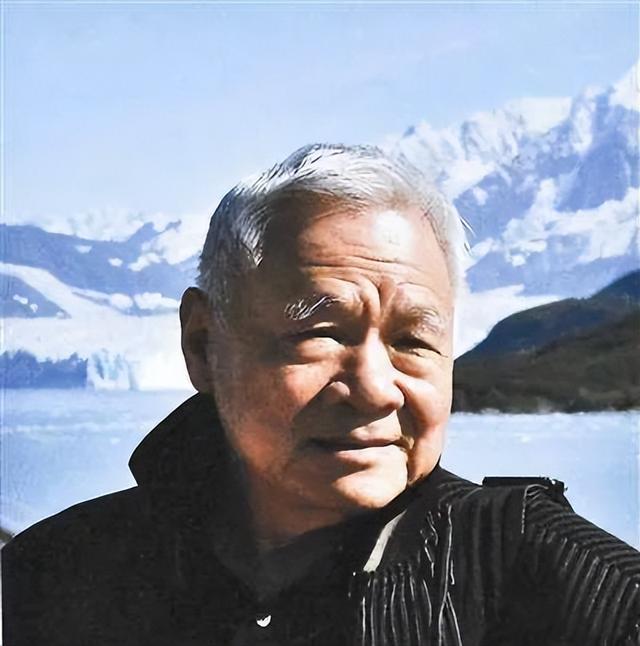
痖弦先生答学生问:
学生:我觉得您的痖弦这个称呼,对于诗歌来说,是一个非常伤感的称呼,我这个观点您是否同意?
痖弦:我高中的时候喜欢拉二胡,喜欢二胡哑哑的声音,因此我在高中的时候壁报副刊上就用“痖弦”这两个字,是少年时代的瞎胡闹(呵呵)。我当时还不知道真的有这个字,我想“瘖哑”的“瘖”字不是有个“病”字边吗?那个“哑”为什么要弄个“口”字边呢?弄个“病”字边好不好呢?就用了。后来我查了查康熙字典,还真有这个“痖”字,就是“哑巴”的“哑”的古写。后来问的人也多了,我就想这样解释好象太浮浅,就找了一句陶渊明的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来搪塞。无弦之琴,此时无声胜有声,不发声的琴可能更好听些也说不定,这岂不是我名字最好的诠释吗?后来还有人解释我这个名字说“大音希声”等,没有那么严重。我也曾经自嘲说“南郭先生”,在乐队里作演奏状,其实并没有奏出什么音乐。
学生:面对诗歌的嘈杂,面对中国的这种现状,作为一个诗人该如何保持他的激情和诗人的状态?
痖弦: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认真。对于生活的珍惜,对于生命的认真,一步一个脚印,一点感觉都不放过,没有其他的功利,那样就能够保持。有了功利的生命就完了。要保持生命的锐气,保持对这个世界继续有意见。我对留胡子的人、长头发的人都很敬畏,因为我知道,留胡子的人一定是对这个世界很有意见,长头发的人好象还有一点反古的样子。你对这个世界要保持你的意见,如果完全没什么意见,太平日子流水过,那你就完了。肥胖是诗人的羞耻,你们看我这样胖乎乎地,就完了,你们看我哪一天变瘦了就是要开始写诗了。(呵呵)
学生:您是否经常读别人的诗歌?您怎么读?
痖弦:我什么诗都读,我是编辑出身,什么样的诗都喜欢,什么样古怪的诗都试着去理解它,我是一个文学的泛爱主义者,不是说合我的这种我就读,不合我的我就不读。写作的时候可以有个性,阅读的时候不能有个性,写作的时候可以骄傲,阅读的时候要谦虚。这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认为新诗现在成绩还没有赶上旧诗,但是,也没有让旧诗来替代新诗的这种存在,新诗也有若干个成就了。
学生:我问的问题可能会让你轻松一点,我不谈诗,也不谈感伤的问题,谈谈乡情吧。我们是老乡,我是河南信阳人,我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老乡的事,就是二月河,他的皇帝系列前些年在海外影响很大,您认为他的作品是否能留传下去,他将来在文学史上是否能有一席之地呢?
痖弦:对二月河我不忍心说话说太重,因为我到南阳去他还在园子里摘石榴给我吃(呵呵),“吃完我家的石榴还说我坏话不像话”。二月河的东西有大众化的品质,所以能够流行,能够得到电视剧的青睐,一步一步地受到欢迎。在台湾,也有一位写历史小说的叫高阳,跟二月河有类似的地方,不过高阳的诗学的底子比二月河要深一点,二月河也不简单,他比较大众化,高阳有时候大众化,有时候也掉书袋,我想这两个人都是很可尊敬的,他们的作品也是会留下去的,至于能不能得到严格的文学尺度评选,那是小说家专业的事情。就比如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好,你说他就是大众吗,这也太过分了,武侠小说就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要想进入文学的殿堂也不容易,因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即使是最好的武侠小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你究竟还是通俗文学。二月河的作品是介于普通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他里面也有普通文学的成分,所以他很不简单。我想二月河还有很多写作的计划,他现在对大家过分地去捧踩他也烦得很,他也想写点大家看不懂的东西,震震那帮批评家,表示一下“你们那玩意儿,我也会”。(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