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有时是一种“所见即所是”的文字——没有宏大的词汇,或浪漫优雅的句法,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细节的排列组合。神奇的是,我们常常可以借此重新看见生活的一点一滴,发现意想不到的奇迹。在单调乏味的日子里,诗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可能性。
本文精选了九首关于日常生活的诗,你最喜欢哪一首?欢迎留言与大家分享。

01
早餐奇迹
清晨六点,我们等待着咖啡,
等待咖啡,还有慷慨施舍的面包
它们会被供应在特定的阳台上,
——仿佛旧时代的国王,仿佛一宗奇迹。
天还没亮。太阳的一只脚
立稳在河面一道悠长的涟漪上。
这天的首班渡轮刚刚过河。
这么冷,我们希望咖啡是
热腾腾的,眼瞧着太阳
已无法使我们暖和;我们希望每个面包心
都是一整块面包,抹上了奇迹。
七点钟,一名男子走出,踏上阳台。
他在阳台上独自站了一会儿
视线越过我们头顶,看向河。
一名侍者将奇迹的材料递给他:
由一杯孤零零的咖啡,和一个
面包卷构成,他走上前,将其捏碎,
就是说,他的脑袋在云中——和太阳一起。
这人疯了吗?他在日光下
阳台上,到底想做什么!
每个人都得到一小块死硬的面包心,
一些人鄙夷地将它掸入河里,
在杯中,每个人都得到一滴咖啡。
我们中有些人四下站立,等待奇迹。
我能说出随后看见了什么;那不是奇迹。
一座美丽的别墅在日光中伫立
门中传来阵阵热咖啡的氤氲。
前面,有一座巴洛克白石膏阳台
再添上沿岸筑巢的鸟儿,
——我用一只眼贴近面包心,看见它——
还有画廊,还有大理石房。我的面包
我的大厦,由一宗历尽沧桑的奇迹
为我制成,由昆虫、飞禽,还有
冲刷卵石的河流。每一天,在日光中,
在早餐时分,我坐在阳台上
搁高脚丫,喝着一加仑一加仑的咖啡。
我们舔掉面包屑,吞下咖啡。
河对岸一扇窗上阳光闪耀
仿佛奇迹正发生在错误的阳台上。
——伊丽莎白·毕肖普
包慧怡 译

02
星期六
我早早起床,光脚走过
门廊;下楼去花园里
亲吻每一株植物;
深深呼吸大地洁净的水汽,
从绊根草里蒸腾;
在绿色美人蕉环绕的泉中
沐浴。然后,湿漉漉地
梳理头发。双手浸没
双瓣茉莉的馥郁汁液。小心
精巧的鹭鸟
从我的裙摆里抢走面包屑。
然后我穿上稀薄的长衣,
比薄纱本身更加轻柔。
轻巧一跳把我的麦秸沙发
搬到门厅放好。
我的眼睛紧盯着栅栏,
紧盯着栅栏。
挂钟对我说:早晨十点钟。
里面有陶土和玻璃混合的声响:
饭厅笼在阴影里;双手揪紧
桌布。
外面,从没见过这样的太阳
照在台阶的白色大理石上。
我的眼睛继续紧盯着栅栏,
紧盯着。我在等你。
—— [阿根廷]阿方斯娜·斯托尔妮
汪天艾 译

03
生活
I
我和农夫打交道,还有舀勺和饲料之类的事物。
每三个月我为自己预定好
那家——酒店——三天一百英镑。
酒店杂役提着我简陋的旧皮箱
送到楼上的单人房,我挂上我的帽子。
一杯啤酒,然后“晚餐”,用餐时
我读——《郡府时报》,从汤到炖梨。
出生,死亡。售卖。警察法庭。汽车备件。
然后,吸烟室里喝威士忌:克拉夫、
玛格特、船长、沃特森医生;
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亏空倒霉的人,
政府关税,工资总额,股票价格。
烟雾在灯光下漂浮。墙上的画
使人发笑——狩猎、沟渠,无人介意
或注意的东西。从酒吧传来
多米诺骨牌的声音。我起身兜了一圈。
后来,广场空了:一大片天空
消失在港湾里,像一条金色河流的
河床,而海关大楼的办公室
仍然亮着灯。我裹在前军队被单里
昏昏欲睡,不知为什么
觉得值得一来。父亲已经去世:
过去是他的,但现在家业是我的。
是时候改变了,在1929年。
II
七十英尺以下
海水向上爆炸,
反复地,垂涎着
离开码头台阶——
奔跑的泡沫,充满喜悦!
礁石盘绕着重回视野。
珠蚌、帽贝,
信奉着它们的顽强,
在冰冷的滑行中——
小家伙,我爱你们!
白天,天空渐渐变成
葡萄黑,在灌进海水的
未播种的骚动的田野上方。
无线广播摩拳擦掌,
告诉我别的地方:
气压计下降,
港口因风暴而关闭,
船队像猎狗群一样被禁锢,
愁闷小旅馆里的火
炙烤着大海的景色——
不提这一切!
到夜里,雪突然转向
(噢散漫的飞蛾的世界)
穿过凝视,飞越
皮革般漆黑的水面。
光芒照拂下,
我摆好盘碟和勺子,
随后,占卜的扑克牌。
亮灯的搁置的航船
像疯狂的世界摸索着向西航行。
——菲利普·拉金
舒丹丹 译

04
走廊
一扇门开着,可以看到厨房——
总有令人垂涎的味道传出来,
但令他酥软的,是那地方的温暖感,
那屋子中央散发热流的炉子——
有些生活就是这样。
热流在中心,恒稳得没人会多想一下。
但他攥着的钥匙能打开另一扇门,
而门的另一边,温暖并不在等他。
他得自己制造——以自己与酒。
第一杯是自己人已到家。
能闻到烤肉,是红酒与橘皮混入小牛肉的味道。
妻子在卧室哼唱,哄孩子入睡。
他喝得很慢,妻子自己开门进来,手指在嘴唇上,
然后他让她热切地扑过来,拥抱自己。
在那之后,烤肉就会上来。
但之后的几杯令她离开现场。
她把孩子带走;整套屋子回到之前的状态。
他另外找到一个人——也不算是另一个人,
而是一个鄙视亲密的自己,似乎婚姻的隐私
就是一扇两人一道关起的门,
谁也不能单独出去,妻子不能,丈夫也不能;
于是那热流郁积在那儿,直到他们窒息,
仿佛他们是住在电话亭里一样——
然后,酒喝完了。他洗脸,在屋子里各处转悠。
正是夏季——生命在热流中腐烂。
有些夜晚,他仍会听到一个女人对着孩子哼唱;
有的夜晚,卧室门后,她那赤裸的身体并不存在。
——[美]露易丝·格丽克
柳向阳 范静哗 译

05
公鸡
水劳作一通宵,顾不上喘息,
雨像点燃亚麻油一直到天明。
从淡紫色屋顶下冒出了水汽,
大地宛如一罐栗汤热气腾腾。
待到小草抖掉水珠后跃起,
正赶上第一只公鸡引吭高歌,
接二连三地直到百鸡齐啼,
有谁能向朝露描绘我的惊愕?
它们逐一反思那逝去的岁月,
它们能轮番地对黑夜呼停,
它们开始预言面临的变化,
为一切一切:雨水、大地、爱情。
——[俄]帕斯捷尔纳克
顾蕴璞译

06
饮水
她每天来打水,每一个早晨,
摇摇晃晃走来,像一只老蝙蝠。
水泵的百日咳,水桶的声音,
捅快满时响声逐渐减弱,
宣告她在那儿。她那灰罩裙,
有麻点的白搪瓷吊桶,她那嗓门
吱吱嘎嘎地响就像水泵的柄。
想起那些夜晚,满月飘过山墙,
月光倒穿过窗户映落于
摆在桌上的水杯。又一次
我低下头伸嘴去喝水,
忠实于杯上镌刻的忠告,
嘴唇上掠过;“毋忘赐予者”。
——[爱尔兰] 谢默斯·希尼
袁可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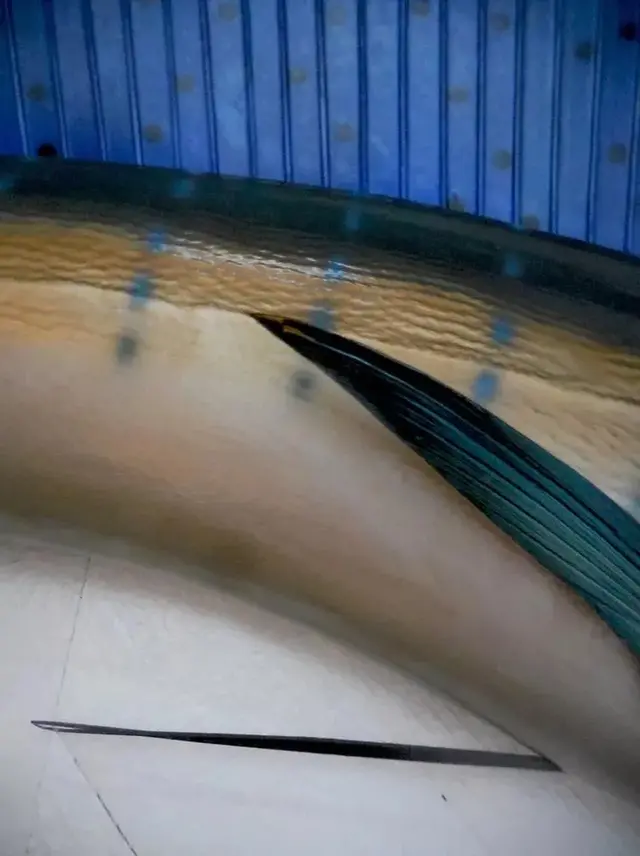
07
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
这里的一切都呈现黄和绿。
听它的歌喉,它土地皮肤的声音,
听青蛙清脆的嗓音
当它们像小广告牌那样颤动。
林间成群的小兽儿
正把死亡面具
搬进狭小的冬天洞穴。
稻草人,摘出了
他宝石般的眼睛,
走进村子。
将军和邮递员
也卸下了行囊。
这一切都发生过
但这里没有过时的事情。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可能。
也许正因如此
一个女孩儿放下了
她冬天的衣服,悠闲地
依着树的肢体,
那肢体伸过河边的池塘。
她被泼撒到那肢体上,
下面便是各种鱼类的屋顶,
而鱼群正出没她的倒影,
沿着她双腿的楼梯上下游弋。
她的身体把云朵一路背回家。
她在俯视她水汪汪的脸,
正午,有几位盲人
到这河中洗浴。
正因如此
土地,那冬天的恶梦,
已经治愈自身的伤痛,怒放出
绿色的鸟群和维他命。
正因如此
树木在沟堑中转动身姿,
并用修长的手指
举起一只只精小的盛满雨水的杯。
正因如此,
一个女人,站在炉火前歌唱,
烹调着花朵。
这里的一切都呈现黄和绿。
春天也一定会允许
一个女孩子一丝不挂
轻柔地转动在她自己的阳光里,
并允许她不再害怕自己的床。
她早已数出七朵鲜花
开在嫩绿又嫩绿的镜子里。
两条河水,在她脚下汇合到一起。
那张孩子的脸在水里
化成波纹,便永远消逝。
眼中的这位女人
全身都是野兽般的美丽。
她珍存的,顽固的皮肤
深深躺在这水汪汪的树下。
这一切完全充满可能,
那几位盲人也能看到。
——[美]安妮·塞克斯顿
金重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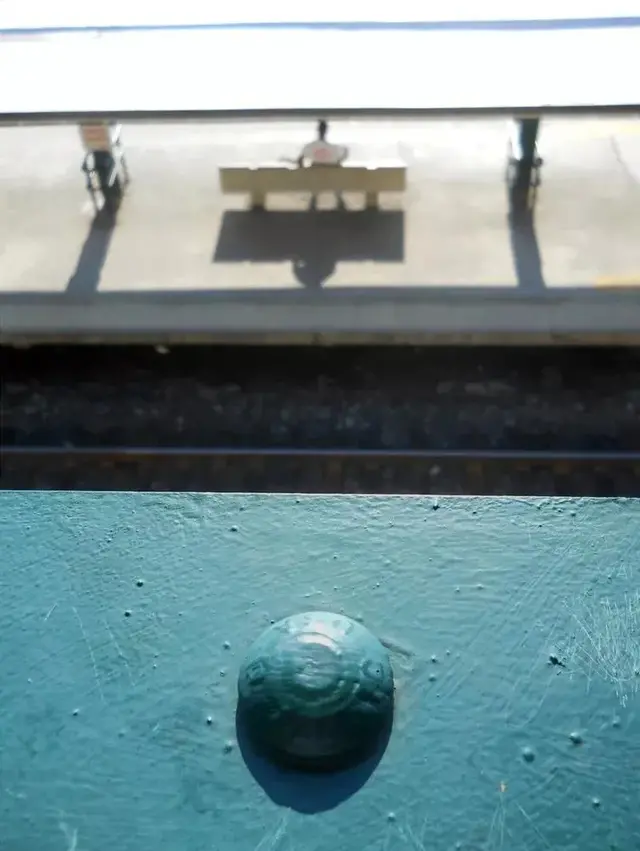
08
金纽约地下铁
这天黄昏 刘易士·霍华德先生
住址不详 疲倦又沮丧
穿一件灰大衣载一顶竭色小帽
决定要搭「布城」甘纳西线
在第八街最后一站 遇到
一位老兄 一袭灰衣一顶竭帽
满脸 沮丧又疲倦,尤如
刘易士·霍华德先生的尊容
就在月台出入 十字转栏旁
站着位仁兄 穿一件灰外套,沮丧
的面色 亦如刘易士
霍华德 并且木然呆视
从骯脏的阶梯上 走下来
一位竭帽老兄 疲倦又沮丧
带着一付其实就是刘易士·霍华德的面容
接着 穿过磨损的木十字转栏入口
来了位妇人 疲倦又沮丧
住址不明 一个手提包一顶
竭小帽 面貌正如同
所有的人,亦正如刘易士·霍华德,而且
彼此的脚步 充满紧张的脚步声
与乎昏暗的灯光 乃是来自
刘易士·霍华德,来自 此一住址不详
与乎 彼一住址不详 接着
木十字栏又转动 拍搭好象一个脑袋
丢进菜蓝子,又或 在旋转栏后面
还可以看见 一个性别不明以及
住址不详 需不甚而完全如同
刘易士·霍华德 脚步 清晰可闻
脑袋 旋转门 昏灯以及走道
统统吸进 第八街 第八街 那块站牌
锵零空隆越来越间
而当列车离站的时候 一阵旋风
把一张报纸 翻到那篇
报导一位住址
不详 浮肿 身份不明的
仁兄 穿一件灰大衣戴一顶竭小帽
既疲倦又沮丧
——[捷克] 米罗斯拉夫·赫鲁伯
商禽 译

09
选自《你有手绢吗——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
比娅说逗点在这里跳舞
你正进入一高脚杯牛奶
洗浴于白灰绿色锌澡缸
几乎所有林林总总材料
领取邮包时你都会碰到
瞧瞧这里
我是坐火车匆匆旅行者
也是汤盘里面樱桃雪利
从来不和生人交头接耳
绕过电话总机直接交谈
——赫塔·米勒
庆虞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