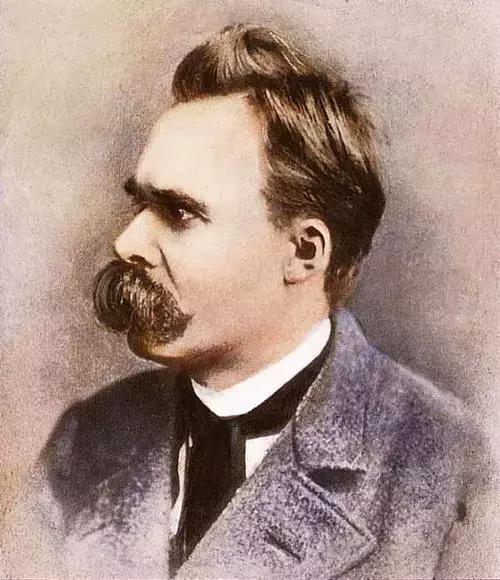
1
最大的危险
若不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头脑,亦即对自己的理性进行训育,并把这种训育视为自尊心、责任和美德(这些东西备受思考时的幻想和荒谬的羞辱),视为“人的健康理性”之友,则人类早就毁灭了!在人类的上空,过去高悬、现在仍然一直高悬着一种最大的危险,这就是突然闪现错误意识,也就是出现感觉与视听的随意性,反而对头脑的无训育、对人的非理性竟然洋洋得意。与错误意识相对立的并不是真理和确定性,而应是对信念的普遍责任,亦即评估和判断的非随意性。
迄今,人类完成的最大一项工作就是使许多事情相互协调并制定了协调的规则,也不管这些事情是对还是错。这就是对头脑的训育,它使人类赖以保存。然而,相反的本能欲望一直十分强烈,以至于人们在议论人类的未来时总是缺乏信心。事物总是在发展运动,从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变动得更加剧繁;可恰恰是那些特殊的能人一直在抗拒对未来之信念的责任,尤以真理的探索者们一马当先!对未来世界的普遍信仰总是给人“高人雅士”增添烦恼和渴望。这信仰要求思想的发展进程需模仿乌龟爬行的慢速度,这已被人们当成一种规则加以接受了;然而,这种慢速度却使艺术家和诗人沦为逃兵。这些缺乏耐心的精英人士极易突发错误意识,因为它具有欢快的速度。
我要使用毫不暧昧的字眼说,我们现在需要符合美德的愚笨,需要舒缓的、不可动摇的思想节拍,以便使那些坚信伟大信仰的人们继续舞蹈,此乃当今第一要务。我们余者都是特殊的人、危险的人,我们需要永远自卫!现在该为“特殊”美言几句,倘若特殊不变为常规的话。
2
通俗性从何而来?
通俗性从何而来呢?是缺乏羞耻心吗?是通俗之物十分自信才堂而皇之登场吗?正如同类通俗的音乐和小说中某些高雅、妩媚、激情的东西一样吗?“动物和人一样,也有它的权利,它可以自由地四处奔窜;而你,我亲爱的同代人,不管怎样也是这种动物啊!”在我我看来,这话就是通俗性的注脚。
同精良的审美情趣一样,粗鄙的审美情趣也有其权利,当它成为一种大的需求,一种自信的满足、一种通俗的语言、一种叫人一看就懂的面具和姿态之时,它甚至比精良的审美情趣还有优先权,而经过遴选的精良的审美情趣总是包含探索性的、尝试性的东西。对它并无确定性的理解,但它永远不是、现在和过去从来不是通俗化的!通俗化始终是面具!
倘若人们不理解别人为何对面具感兴趣,不理解别人对面具的良苦用心,那还能对面具做什么别的理解呢?
3
我们感谢什么?
我们感谢什么?只有艺术家,尤其是戏剧艺术家才给人们安上眼睛和耳朵,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看和听:每个人自己是什么,经历了什么,自己想干什么;他教会我们如何评价英雄,本来,我们芸芸众生里并无人知晓这英雄。他们教会我们一种艺术:怎样把自己当成英雄,从远处简略而清晰地观察自己,此乃将自己“置于场景中”的艺术。于是乎,我们得以摆脱了身边的鄙琐之事!
倘若没有这种艺术,那我们作为“前景”就一文不值了,而只能生活在透镜的魔力中。透镜可以把最近、最鄙俗之物变得硕大无比,变成真实之物。
也许,宗教也有类似的功劳。它用放大镜看每个人的罪过,并用罪过制造一个个伟大而不朽的罪人,其手段就是描述每个人永恒的、未来的前景,教导人们从远处看自己,并把自己当做已经过往的整体来看待。
4
做自由的自己
生活在对我们每个人呼喊:“做个血性男儿!不要跟随我,而要跟随你自己,你自己!”
我们的生活也应对我们保持无误!我们应当自驾游、坦荡,从清白无辜的自我本位发展自己、强盛自己!当我在观察这类人的时候,耳畔一如既往地响起如下的话语:“情欲比斯多亚主义好,比伪善好;诚实,即便是恶意的诚实,也比因为恪守传统道德而失去自我要好;自由的人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然而,不自由的人则是对本性的玷辱,因此不能分享天上和人间的安慰。总之,谁要做自由人,必先完全成为他自己。自由不会像神赐之物落在人的怀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洛伊特》)
5
学会尊敬
人必须学会尊敬,就像必须学会轻蔑一样。凡是走上新的生活轨道并把许多人也带上新的生活轨道的人,无不惊异地发现,这些被带上新的生活轨道的人在表达感激之情的时候是多么的笨拙和贫乏,更有甚者,连单单把谢意表达出来的能力也不常有。每当他们说话,便似骨鲠在喉,嗯嗯啊啊一番就复归平静了。
思想家在感受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时,在感受他的思想改变和震撼人心的威力时,这感受方式几乎是滑稽的,其中还有所顾虑;怕受其影响的人内心受到伤害,怕他们会用各种不当的手段来表达其独立自主的精神受到威胁。要形成一种有礼貌的感激习俗,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嗣后,思想和天才一类东西进入感激情愫中的那个时刻才会到来。届时,会出现一个接受感恩的为人,他不仅因为自己做了好事而受感戴,更主要因为他的先辈们日久天长积累下那个至高之善的“宝物”而受到感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