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完美的作品应当一挥而就
我们欣赏一切完美的作品时,往往忽略它的生成问题,只是怡悦于眼前的作品,仿佛它是魔棍一挥便从地下跳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仿佛还处在一种古老神话感觉所遗留的影响之下。我们几乎还有这样的心情(例如在象裴期顿神庙那样的希腊神庙中),好象某个早晨有一位神灵游戏似地用这些巨材盖了他的住宅,或者好象有一个灵物突然被魔法镇入一块巨石,现在想借之诉说。(裴斯顿,希腊移民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筑有著名的长方形大会堂“巴齐立卡”。)
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唯有使人相信是即兴而作、是奇迹般的一挥而就之时,才生出圆满效果;所以,他巧妙地助长这种幻觉,把创作开始时那热烈的不安、盲目抓取的纷乱、留神倾听的梦幻等因素引入艺术,当作欺骗手段,使观者或听者陷入某种心境,相信这完美的作品是一下子蹦出来的。
不言而喻,艺术科学断然反对这种幻觉,指出悟性的误解和积习,正是由于这些误解和积习,悟性中了艺术家的圈套。
2. 艺术家的真理意识
在对真理的认识上,艺术家的道德较思想家薄弱;他决不肯失去生命的光辉的、深意的诠释,抵制平淡质朴的方法和结论。他仿佛在争取人的更高尊严和意义;实际上他是不愿割爱他的艺术的最有效的前提,诸如幻想、神话、含糊、极端、象征意义,高估个人,对于天才身上某种奇迹的信仰:所以,他认为他的创造行为的延续比科学上种种对真理的献身更重要,觉得这种献身也是太单调了。
3. 作为招魂女巫的艺术
艺术除执行保藏的任务外,还执行给黯淡褪色的印象稍稍重新着色的任务;当它解决了这个任务,它就为各个时代织成了一条纽带,唤回了它们的幽魂。虽然借此出现的仅是墓地的虚假生命,或如逝去的爱人梦中重返;但至少在顷刻之际,从前的感觉又一次唤醒,心脏又按业已忘却的节拍搏动。为了艺术的这种普遍效用,即使艺术家并不站在启蒙人类、使人类继续男性化之前列,人们也应宽宥他:他一辈子是个孩子,或始终是个少年,停留在被他的艺术冲动袭击的地位上;而人生早期的感觉公认与古代的感觉相近,与现代的感觉距离较远。他不自觉地以使人类儿童化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他的光荣和他的限度。
4. 诗使人生变得轻松
诗人若想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他们就把目光从苦难的现在引开,或者使过去发出一束光,以之使现在呈现新的色彩。
为了能够这样做,他们本身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所以人们可以用他们作通往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通往正在或已经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遗民。至于他们用来减轻人生苦难的药物,诚然可以说:它们仅仅抚慰和治疗于一时,只有片刻的作用;它们甚至阻碍人们去为实际改善其处境而工作,因为它们解除了不满者渴望行动的激情,使之平息消散了。
5. 美的慢箭
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作暴烈的醉人的进攻(这种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
在观照美时我们渴望什么?渴望自己也成为美的:我们以为必定有许多幸福与此相联。——但这是一种误会。

6. 艺术的有灵化
宗教消退之处,艺术就抬头。它吸收了宗教所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绪,置于自己心头,使自己变得更深邃,更有灵气,从而能够传达升华和感悟,否则它是不能为此的。宗教情感的滔滔江河一再决堤,要征服新的地域。但生长着的启蒙动摇了宗教信条,引起了根本的怀疑。于是,这种情感被启蒙逐出宗教领域,投身于艺术之中;在个别场合也进入政治生活中,甚至直接进入科学中。无论何处,只要在人类的奋斗中觉察一种高级的阴郁色彩,便可推知,这里滞留着灵魂的不安、焚香的烟雾和教堂的阴影。
7. 韵律缘何美化
韵律给现实罩上一层薄纱;它造成了一些话语的做作和思想的不纯;它把阴影投在思想上,使之忽隐忽现。正如阴影对于美化是必要的一样,“模糊”对于明朗化也是必要的。
艺术使生活的景象可以忍受,因为它把非纯粹思想的薄纱罩在生活上了。
8. 丑恶灵魂的艺术
如果要求唯有循规蹈矩的、道德上四平八稳的灵魂才能在艺术中表现自己,就未免给艺术加上了过于狭窄的限制。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
9. 艺术使思想家心情沉重
形而上的需要多么强烈,人的天性多么难于同这种需要诀别,由以下情况可见一斑:一位自由思想家即使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艺术的最高效果仍然很容易在他心灵中拨响那根久已失调、甚至已经断裂的形而上学之弦,便如,在倾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某一段时,他会感到自己心中怀着不朽之梦想,远离大地,飘摇于星星的大教堂中:众星在他周围闪烁,大地渐渐沉入深渊。
如果他意识到这个境界,内心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刺痛,向着替他引回失去的爱人——所谓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人喟叹。他的智性在这瞬时受到了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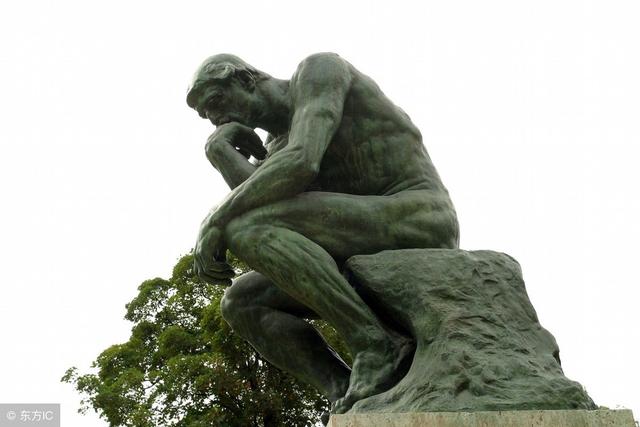
10. 与人生嬉戏
荷马式幻想的轻松和粗率是必需的,以求抚慰和暂时解脱过于激动的情绪和过于敏锐的悟性。他们的悟性说:人生看来是多么严酷!他们并不自欺,但他们故意用谎言戏弄人生。西蒙尼德斯劝他的邦人把人生视同游戏;严肃之为痛苦于他们是太熟悉了(人间的苦难实在是诸神听得最多的歌唱题材),他们知道,唯有艺术能化苦难为欢乐。但是,作为对这种认识的惩罚,他们如此受虚构欲望的折磨,以致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摆脱谎言和欺骗了,正象一切诗化民族都爱撒谎,并且毫无罪恶感一样。邻近的民族有时真对他们感到绝望了。(西蒙尼德斯公元前五百年的古希腊诗人。)
11. 对灵感的信仰
艺术家们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即所谓灵感;仿佛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上照下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象力是在不绝地生产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若不太严格地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与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
12. 再论灵感
如果创造力长期被堵塞,其流动被一种障碍阻挡,那么,终于有如此突然的奔泻,宛如一种直接的灵感,并无此前的内心工作,好象发生了一种奇迹。这造成了常见的错觉,而这种错觉的延续,如上所述,与所有艺术家对此的兴趣有相当关系。资本只是积累起来的,它并非一朝从天而降。此外,这种貌似的灵感在别处也有,例如在善、道德、罪恶的领域里。
13. 天才的痛苦及其价值
艺术天才愿给人快乐,但如果他站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他就很容易曲高和寡;他端出了佳肴,可是人家不想品尝。有时会使他产生可笑的伤感和激励;因为他根本无权去强迫人家快乐。他的笛子吹起来了,可是没有人愿跳舞:这会是悲剧吗?也许是吧。但作为这种缺憾的补偿,比起别人在所有其他各类的活动中所具有的快乐,他毕竟正在创造中具有更多的快乐。人家觉得他的痛苦言过其实,因为他的喊声太响,他的嘴太会说;有时他的痛苦真的很大,但也只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和嫉妒心过重。像开普勒、斯宾诺莎这样的科学天才一般并不急于求成,对于自己真正巨大的痛苦也并不大事张扬。他可以有相当把握指望后世,而舍弃现在;但一位艺术家这样做,却始终是在演一场绝望的戏,演出时不能不伤心之至。但在极稀少的场合,当一个人集技能、知识天才与道德天才于一身时——除上述痛苦外,还要增添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可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人以及一切受苦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远大的认识相连而有价值(同情本身价值甚小)。然而,用什么尺度、什么天平来衡量它的真实性呢?一切谈论自己这种感觉的人,不是都令人生疑吗?
14. 伟大的厄运
每种伟大的现象都会发生质变,在艺术领域里尤其如此。伟大的榜样激起天性虚荣的人们进行表面的模仿或竞赛。此外,一切伟大的天才还有一种厄运,便是窒息了许多较弱的力量和萌芽的机会,似乎把自己周围的自然弄得荒凉了不少。一种艺术发展中最幸运的情况是,有较多的天才互相制约,在这种竞争中,较柔弱的天性往往也能得到一些空气和阳光。
15. 艺术有害于艺术家
如果艺术强烈地吸引住一个人,就会引他去反顾艺术最繁荣的时代,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具有倒退性的。艺术家越来越重视突然的亢奋,且相信鬼神,神化自然,厌恶科学,其情绪变化如同古人,渴望颠覆一切不利于艺术的环境,而且在这一点上,如同孩子那样地偏激不公。艺术家本来就已经是一种停滞的生灵,因为他停留在少年及儿童时代的游戏之中;现在他又受着倒退性的教育而渐渐回到了另一个时代。因此,在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终于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留下一个悲惨的结局;就像古代传说——荷马和埃斯库罗斯那样,终于在忧愁中活着和死去。
16. 被创造出的人物
所谓的戏剧家(以及一般艺术家)当真创造了性格,这种说法只是哗众取宠和夸大其辞,由于这种说法的存在和流传,艺术得以庆祝其意外的、似乎是额外的一个胜利。事实上,当我们举出一个真正的、活人的各种性格时,我们对其所知不多,又概括得十分肤浅。我们这种对人极不完善的态度与诗人相一致,他给人描画(所谓“创造”)的肤浅草图,正和我们对人的认识一样肤浅。在艺术家创造出的这些性格中有许多的虚假;这根本不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产品,反而和画家一样有点儿过于单薄,它们经不起近看的。所谓一般活人的性格往往自相矛盾,戏剧家所创造的性格是浮现在自然面前的原型,这种说法也是完全错的。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整体,一种完全必然的东西(哪怕在所谓矛盾时),不过我们并非始终能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虚构的人物、幻象也欲表示某种必然的东西,但只是在那些人面前,这些人在一种粗略的、不自然的简单化中理解真实的人,以致一些常常重复的粗线条,配上许多光,周围涂上许多阴影和半影,也就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了。他们很容易把幻象当作真实必然的人,因为他们惯于把一个幻象、一个投影、一种任意的缩写当作整个真实的人。画家和雕塑家要表现人的“观念”,这更是空洞的幻想和感官的欺骗。谁这样说,他就是被眼睛施了暴政,因为眼睛只能看到人体的外表和肌肤,而内脏同样也属于观念。造型想使性格见之于皮肤;语言艺术借言词达到同一目的,用声音模拟性格。艺术从人的自然和无知出发,越过了人内在的东西(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性格上的):因为艺术不是属于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
17. 对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信仰中的自我评价过高
我们都以为,倘若一件艺术品、一位艺术家吸引我们,并震撼我们,其优秀就算得到了证明。可是,在这里必须首先证明我们自己在判断和感觉方面的优秀才行,而事实却并不尽然。在造型艺术的领域里,有谁比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贝尔尼尼更令人心醉和神迷呢?在狄摩西尼之后,有谁比那个引进亚细亚风格,并使它占统治地位达二百年之久的演说家更具影响力呢?支配整个世纪丝毫不能证明一种风格的优秀和持久的效用;所以不应当执著于某一位艺术家的衷心信仰。这样一种信仰不但相信我们的感觉真实无欺,而且相信我们的判断正确无误,其实,判断和感觉可能分别或同时发展得太粗糙或太精细,太紧张或太松弛。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给人以幸福感和慰藉,却同样丝毫不能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就像疯子因他的固定观念感到幸福,但丝毫不能证明这观念的合理性一样。
18. 出自虚荣心的天才迷信
我们自视甚高,但我们根本不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画出一张拉斐尔式的草图,或写出一部莎士比亚式的戏剧,于是我们自我解嘲说,这种才能只是异乎寻常的奇迹,极为罕见的偶然,或者,倘若我们有宗教感情,还会说此乃天赐的恩惠。所以,我们的虚荣心和自爱心促进了天才的迷信;因为只有当天才被设想得离我们十分遥远,如同一种神迹时,他才不会伤人。人们显然只是在这种场合才谈论天才:巨大智力的效果对于他们是极为令人愉快的,使他们无意再嫉妒了。称某人为“神圣”则意味着:“在这里我们不必竞争。”再者,一切完成的、完满的东西都令人惊奇,一切制作中的东西都遭小人观看。没有人能在艺术的作品上看出它是如何制成的,这便是它的优越之处,因为只要能看到制作过程,人们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完美的表演艺术拒绝对其排演过程的任何考察,而作为当下直接的完美作品产生强烈效果。所以,首先被视为有天才的,是表演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实际上,扬彼抑此也不过是理性的一种孩子气。
19. 天才与无价值之作
在艺术家中,恰是那种独创的、自为源泉的人有时会写出极其空洞乏味的东西出来。相反,有所依赖的天性,即所谓的才子,倒是充满着对一切可能的美好事物的记忆,即使在才力不足时,也能写出一些还算过得去的东西。而独创者却是与自己隔绝的,所以记忆无助于他们,于是他们就变得空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