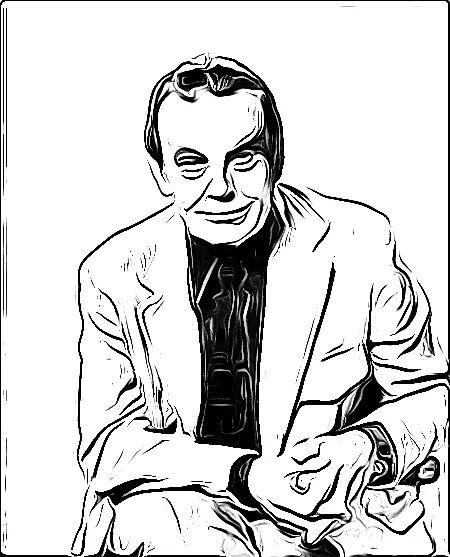
使命
在恐惧和颤栗中,我想到要完成我的生命,
唯有让自己公开地承认,
以此公开我和我的时代的羞耻:
我们可以以侏儒和魔鬼之舌尖叫,
纯洁大度的言辞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厉的惩罚下,无论谁敢于发出一个声音,
他就得将自己认作一个失踪的人。
献词
你,我不能拯救的你呵
请听我言。
请理解我这些简短的语言,换了别的我会感觉羞愧。
我发誓,我没有使用巫术的言辞。
我以云或树的沉默与你讲话。
使我强化者,于你却是致命。
你把旧时代的告别错当成了新时代的开始,
将仇恨当作了抒情之美的灵感,
把盲目的力量当成了完成的形态。
这里是波兰河水流经的河谷。一座巨大的桥梁
超越白雾。这里是破碎的城市,
当我与你交谈
风吹你的坟茔,阵阵鸥鸟的叫声。
诗是什么?——它救不了
民族和人民。
对官方的谎言装出的视而不见,
即将被割破喉咙的酒鬼所唱的一首歌,
写给无知少女阅读的无聊读物。
我要的好诗仅仅一望而知,
它的益处,我发现了,太晚太晚,
在此,仅仅在此,我找到拯救的意义。
他们总是习惯往逝者的坟头倾洒粟米或罂粟的子实,
以祭奠化装成飞鸟的亡魂。
为了你不再寻访我们
我向你献上这本书,曾经生活的你。
与简妮交谈
简妮,我们且不谈哲学,将它放下。
道理那么多,卷佚那么浩繁,谁能忍受它们。
我曾告诉你,我远去的自我的真相。
我已不再忧虑,对于我不幸的生活。
较之人类通常的悲剧,它不会更好,也不更糟。
三十多年了我们不曾停止过争执
就像现在,在这热带天空下的小岛。
我们逃过大雨倾盆,转瞬又是艳阳高照,
我感觉木然,眩目于树叶的翠绿。
我们浸没于细浪涌起的泡沫,
我们游出很远,直到看见水天一线处,香蕉丛
和棕榈风车似的叶子纠结成一团。
而我承受指责:比如我并不堪当我所有的劳作,
比如我对自我的要求还不够,
也许我应该向卡尔·雅斯贝尔斯学点什么,
比如我对这时代种种的说辞轻视得还不够。
我随海浪翻转,看着白云朵朵。
你是对的,简妮,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关心灵魂的救赎。
一些人被召唤,另一些人则各显神通。
我已接受,一切降临于我的,都很公正。
我不会为了尊严装出拥有老年的智慧。
言不及义,我仅于眼前所是的一切中安顿,
在这世界现存的、而又能够取悦于我们的一切事物之中:
沙滩上赤裸的女人,她们胸脯前古铜色的锥体,
木芙蓉,菟丝花,一朵红百合,--吞噬
以我的眼,唇,舌,--那番石榴汁,西塞尔的李子汁
加冰和蜜的朗姆酒,那雨林中的兰花,
--那儿,树木高耸于它们的根部。
你说,死亡,你的和我的,已越来越近,
我们为此承受痛苦,这有限的尘土并不足够。
菜圃里黑紫的尘土
仍将在那儿,无论你我在意与否。
大海,就像今天,仍将从它的深度中呼吸。
越来越小,我消失在这在无边无垠,越来越、越来越自由。
一小时
阳光下闪亮的叶子,黄蜂热切的嗡嗡,
从远处,从河流外的某处,延绵回声
和并不急迫的锤击声不仅给我带来愉悦。
五官打开之前,远在一切开始之前
它们就等着,准备好了,迎接那些自我命名的人类,
为了他们会像我一样赞美,生活,它就是,幸福。
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早散了,我在花园劳作。
蜂鸟歇息在忍冬花。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遭受过的一切邪恶,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难堪。
在我体内,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蔚蓝的大海和叶叶船帆。
忘却
忘记不幸
你带给别人的。
忘记不幸
别人带给你的。
河水流呵流呵,
泉水闪着光,逝去,
你走在就要遗忘的土地上。
偶尔听到远处声声叠唱。
那是什么意思?你问,谁在歌唱?
孩子似的太阳变得温暖。
孙子和重孙诞生。
你又一次被牵着手。
河流的名字没变。
它们仿佛永无止境!
田野在身后伸展,
城市的塔已不是曾经的塔。
你站在门槛,没有言语。
在加勒比海一座岛上翻译安娜·斯维尔
最后一次见到你时
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你的诗。一头那样长而密的白发
你可以骑上扫帚,将一位魔鬼引为情人了。
而你自负地宣称着
你的脚趾、脉搏、大肠的哲学。
“诗的定义:无论我们做什么,
欲求,爱,占有,受苦,
总是只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一定存在别的什么,真实而稳固。
尽管无人知道永恒是什么。”
“而身体是最神秘的东西,
尽管,它是那么易朽,却意欲纯粹,
从那大叫着‘我’的灵魂获得解放。”
安娜·斯维尔,一个玄学诗人,
倒立于头顶时,她感觉最好。
孤独研究
荒漠里一个长距离水渠的守卫者?
沙地里驻守要塞的一个人的小分队?
不管他是谁。黎明他看到皱起的山峦
融化的夜色之上,灰烬之色,
似浸染了紫罗兰,化作一片流动的胭脂,
直到它们呈现为满天,桔红的光芒。
一天又一天。在他意识到以前,已是一年又一年。
为谁?他问,这壮观之景,仅仅为我一人?
在我消失之后,它依然会得长存。
在一只蜥蜴眼中,或在一只候鸟看来,它是什么?
如果我即是全部的人类,没有我,它们是否还是它们?
他知道哭也没有用,因为它们中谁也救不了他。
蟒蛇
我想说出真相,
但感觉徒然。
我试图坦白,
却没有什么能够坦白。
我不相信精神疗法。
我知道我会说出不少谎言。
如此,我带给自己一条缠绕着的愧疚——
它于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站在雅斯朱尼的拉乌杜尼卡湿地,
一条蟒蛇拖着尾巴正消失在
矮松林下的苔藓。
我扣动扳机,铅弹射出了霰弹枪。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粒子弹
击中那可怕的白腹
或它背上的条形纹。
较之心灵的种种冒险,无论如何
这容易叙述得多。
非我所属
我整个一生都在谎称这属于他们的世界是我的
并深知如此佯装并不光彩。
但我能怎样?假如我突然放声喊叫
并作出预言。无人会听。
银屏和麦克风不为这个存在。
类似我的另外一些人徘徊在街上
他们自言自语。在公园的长椅
或小巷的走道睡觉。将所有不幸者关起来
牢房就不够用。我笑了保持安静。
他们现在还不会带走我。
和那些被挑选者共赴盛宴——这我擅长。
距离
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跟随着你,羞于离你更近。
虽然你选我在你的葡萄园做工压你愤怒的葡萄。
根据其本性,对每一个人而言:那残损的不一定都会治愈。
我甚至不知道一个人是否会自由,因我一直在违背我的意志劳作。
被按着脖子,像一个男孩踢着咬着,
直到他们使他在桌前坐下命令他写作业,
我愿和别的人一样却被赋予了孤绝的苦涩,
相信我乃是众生平等的一员,醒来却发现一个陌生人。
反视自己的举止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
愧疚于对俗仪的反叛。
世上有那么多人善良而公正,被正确地挑选
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追随着你。
那也许是真的:我秘密地爱着你
却没有像他们那样有着靠近你的强烈希望。
悲叹
真的,我们的族群和蜜蜂类似,
收集智慧的蜜,运送,储藏于蜂巢。
我能几小时地漫步
在图书馆的迷宫,一层一层。
可是昨天,为寻找大师和先知的话,
我走到一个实际上
无人涉足过的高处。
我想打开一本书却什么也不能破解。
因为文字漫漶已从纸页消失。
啊!我惊叹——怎么会这样?
你们在哪里,可敬的先贤,你们的长髯和假发,
你们秉烛熬过的长夜,你们妻子的不幸?
拯救这世界的启示就此永归沉默?
这是你居家制作腌物的日子。
你的狗,躺在炉火旁,醒来,
打着哈欠,望着你,仿佛知道答案。
造物主
来吧,圣灵,
让或不让青草弯曲,
出现或不出现在我们头顶,以火焰之舌讲话,
在干草丰收时或在我们耕作果园时,
或是,当白雪覆盖内华达山脉被毁坏的冷杉时。
我不过是一个凡人:我需要可见的圣迹。
我易于疲劳,建造空想的阶梯。
你知道,一次次我请求,
教堂的塑像,为我抬起手,一次,只要一次。
而我想,圣迹一定要显现于凡人,
不是我——虽然我不缺正派——
那样,便可召唤世人,无论在什么地方,
也能让我,在看着那人的时候,
为你感到惊奇。
咒语
人类的理性美丽而不可战胜。
任何栅栏,铁丝网,将书籍化纸浆的行为,
任何流放的判决都不能战胜它。
它在语言中确立普世的理念,
指导我们的手以大写字母写下
真理和正义;谎言和压迫,以小写。
它将理应置于事物之上者如其所是地安置,
它是绝望的敌人和希望的朋友。
它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主人和奴隶,
将世界的产业赋予我们来经营。
它从被歪曲的词语相互之不洁的龃齬中
拯救出朴素而明晰的只言片语。
它说太阳下一切都是新鲜,
松开过去凝固的拳头。
美丽年轻的是哲学
和诗歌,她们一同致力于美好的一切。
直到昨天自然才庆祝她们的诞生,
这消息由独角兽和回声带到山中。
她们的友谊将充满荣耀,她们的时间没有极限。
她们的敌人会把自己交付毁灭。
翻译/李以亮

1911年6月30日,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维尔诺(现维尔纽斯)附近的一个农庄。
1934年在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之前,米沃什曾在维尔诺的泰凡·巴托雷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文学刊物,和一个同名的文学团体“火炬社”,号称波兰文坛的“灾难主义诗派”。并在1933年,以《冰封的日子》一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1936年从巴黎回国后,25岁的米沃什开始在波兰电台文学部任职,并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被公认为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作家。
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米沃什曾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红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的那些先锋派的诗歌小圈子,已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他只好匆匆逃离,穿越四道封锁线,回到华沙,并加入左派抵抗组织,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
1943年,米沃什目击华沙犹太区惨案,并写下了他作为见证者的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描写了华沙犹太人起义的情景。
1944年,波兰地下军发动华沙起义被德国占领军镇压,苏联红军隔河袖手旁观。华沙劫掠之后,米沃什和一帮作家、艺术家躲到古老的克拉科夫城避难。
1945年,苏军攻占了柏林,德国投降,米沃什目睹波兰新政府追捕听命于流亡政府的“国家军”战士。在克拉科夫市政当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离开。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后在老友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的内容似乎都在有意背离着官方的教条。
1950年,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外交官,再次来到巴黎。
1951年初,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从任上出走,并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
1960年,米沃什移居美国,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并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会员。
1970年,米沃什加入美国国籍。
米沃什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动荡、凶险、屠杀与在时间中的遗忘,当然,还有贯穿于他的诗歌写作中的拯救。米沃什的全部诗作可以看成是一首挽歌,一首关于时间的挽歌。当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曾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试图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同时也在他的诗中包含了对人性、历史和真理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对往事的追忆和对时间的思索构成了米沃什诗歌的特色。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展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和拯救。这就使他的诗中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失去家园的感觉对于米沃什来说是双重的:地理上和时间上的。他目睹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变化,并为之深深触动。早年的信念破灭了,许多熟悉的人和城市消失了,德国法西斯的覆亡并没有使和平真正到来,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集权和冷战。但幸好这种时间的变化并没有把他引入一种虚无主义,而是使他具有了见证人的身份。
米沃什的反思源于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但他不是十足的悲观主义者,至少他的部分诗歌并非那么沉重。他也写过一些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可以把这视为他全部作品中的华彩乐段,也可以看作他对生活的热爱。诗人主张并鼓励人们去感知、享受尘世的快乐,即使这快乐是短暂的。正是经历了一连串的不幸,正是对时间的本质有着深切的感知,诗人才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毋宁说,他是在遮掩或说服自己忘掉内心的痛苦。因为过去的一切不断地袭扰他,包括那些死者尽管他可能真的认为生活即是幸福,但人活着所要学会的不光是死亡,还有活着本身。
在米沃什最初开始写作时,现代主义诗风正在欧洲盛行,年轻的米沃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米沃什留在华沙,亲眼目睹了纳粹的种种暴行。这些噩梦般的日子日后经常出现在他的诗中,直接或戴着面具。在1956年完成的长诗《诗论》中,米沃什对1900至1945年波兰的历史文化和诗歌创作进行了回顾,这可以看作他在流亡西方后对自己思想的一次清理。米沃什深知自由对一个人的重要,但他并未忽视自己对历史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在他看来,最可怕的莫过于遗忘。如果过去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那它们就不是真正的消逝。但消逝的过去一旦被遗忘,那就意味着它真的消逝了,人们也就断绝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晚年的米沃什,诗歌的创作中开始带有神学思想,一方面尊重宗教,另一方面又手握着虚无。在诗集《第二空间》中,诗人在完成一生孜孜不倦的诗歌写作和社会活动之后,重新梳理自己的宗教体验和生死观念,以一种最基本的私人经验作为终曲。
尽管米沃什熟悉几种语言,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并没有放弃用波兰语写作。这一方面是他意识到诗歌必须要使用母语才能写好。另一方面,坚持用母语写作,也是他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1945年前后的米沃什,在诗歌风格上大大不同。他的前期作品具象征主义特色,也因为二战的缘故,既有悲观的一面,又有反战情结。1945年后,尤其是流亡后,他开始关注人类本体的终极意义,在极权禁锢下,他挣脱牢笼,希望在哲学、历史和文化中寻求武器。
米沃什的风格朴素而强烈。他并不过分追求形式和外在的诗意,但他的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也许是理性和道义的力量在诗歌中得以体现的缘故。他常常使用散文化的句子,没有更多的修饰,显得自然流畅,有时甚至显得直率。米沃什的思想明晰,沉郁,甚至忧伤。就精神气质讲,米沃什属于古典主义,代表着欧洲文化的传统。晚年的米沃什,他的观念形态是一种无可避免的世界性杂糅,并在诗歌中重拾古希腊和拉丁诗歌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