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三年之病
文|茅盾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帖,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消之故。母亲争辩说:“我没学过医,可是常听爸爸说,疟疾宜表不宜遏。”父亲却相信奎宁治疟并不是什么遏止。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圯塘)来给父亲会诊。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父亲还是天天气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焦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大砚台在楼下书房(即祖父教几个儿子侄儿读书那间房),母亲去找,果然方子还在,还有当年和尚留下的他在杭州的住处。母亲高兴极了,就同父亲商量,如何派人到杭州找和尚。父亲说,和尚云游,时隔十多年,知他还在杭州否,不如先照和尚方子服几帖再说。可是母亲瞒着父亲写个字条送给宝珠,叫她想法。随即阿秀来了,说外祖母正在设法,好端要弄个明白:那和尚是否还在。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母亲决心请她的六叔(渭卿)来治。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母亲坐了船去,希望原船接回渭老。父亲的那些师兄师弟,此时天天都来会诊,看见“师妹”亲自去请渭老,他们都坐着等待。他们一边等,一边同父亲谈弟弟的病,一边传观和尚那张方子,都说,怎么方子上只开病情不作判断,又说看他一手字,便知是“斲轮老手”。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茶点早已摆起,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其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父亲等看了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这里,我是完全根据母亲对我所说记下来的。母亲在事隔七八年后对我讲这件事时,也说不清弟弟患的是什么病,也只记得渭老开的方子中间有这两味药)。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实际他们心里是怀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稳。半夜醒来,居然说肚子饿了。连服三帖,病已痊愈。母亲连忙写信,与父亲连名,感谢渭老。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进来了,随后是宝珠扶着外祖母。原来外祖母结伴到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和尚。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庙都访过了,都不知有此和尚。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果然那和尚云游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捞月了。外祖母抱着病后初愈的弟弟却对父亲说:“老头子(指外祖父)在世时常说,树皮草根,只治得病,不能治命,看来姑爷——”外祖母声音哽咽,说不下去。父亲苦笑道:“讲到命,也许突然又来个神医。君子安命,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母亲接着说:“也只好这样,自安自慰吧,死生有命。”

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最初,父亲每天还是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房中窗前读书一、二小时,然后又卧。他那时还是对数学最有兴趣,他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那时新出的谢洪赉编的),其次是喜欢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又其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也看那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关了。这个时候,在乌镇通常是一个最冷的时候,常常下雪。乌镇一带地区的房屋构造是不保温的,也没有取暖设备,因此显得特别冷。父亲此时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的丝棉被;他常常支起双腿,躺着看书。不料腊月既过,天气渐转暖和时,父亲的两条腿不能放弃,好像因为长久支起,筋已缩短。如果别人帮着用力拉,是可以拉起的,但因父亲脸上有痛苦表情,妈妈不忍,就让这样支起(直到死,还是这样。殓时有人拉了一下,才放弃了,但那时妈妈倘看见,也会伤心的)。
然而除了渐渐转动不便(在床上翻身,也要妈妈帮他),别无痛苦。饭量照样好,每天外祖母送来各种滋补的食品,父亲都能吃,然而人却一天一天消瘦下去。
在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了个愿,让我在阴历七月十五出城隍会时扮一次“犯人”。这是乌镇当时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药物不灵时,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许愿,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神就会让病人的病好起来。
祖母是迷信神道的,在父亲卧床不起后,她多次提出要去城隍庙许愿,都被父亲和母亲拦阻了。现在她看到儿子日益消瘦,也就不管我父母亲的反对,自己到城隍庙里去许了愿。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围挂着琉璃彩珠,打上灯彩。“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因为各街坊要互相竞赛,所以“抬阁”和“地戏”年年出新斗奇,除非那年逢上了大灾荒。
出城隍会,照例由一队人马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就是各街坊的“抬阁”和“地戏”在喧天锣鼓声中慢慢地依次走过。队伍的中间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轿,里面坐着城隍的木像,面施彩皮,身穿神袍,轿前有“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前呼后拥,十分威风。但是大轿在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却突然锣鼓息声,抬轿的人要一起跑步,飞速穿过观前的那一段街道。这是有名目的,叫做“抢轿”,因为修真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模大样地经过修真观,只能跑步通过。城隍大轿的后面,又是“抬阁”和“地戏”,最后就是“犯人”的队伍。“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围一条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是一副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一根带子系牢,挂在“犯人”的脖子上。整个出会的队伍要在乌镇的四栅(东南西北栅)周游一圈,“犯人”也要跟着兜一周。有的年龄小的“犯人”,这样远的路走不动,也可以由大人抱着参加游行。即使走得动的“犯人”,一般也有家里人在旁边跟着,因为怕孩子把“手铐”丢了。
祖母让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岁,正是最爱玩耍的年龄,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不过事后想想,又觉得不上算,因为“犯人”只能跟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见只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围观的人群,实在没有扒在我家老屋临街的窗台上看下面经过的队伍来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连“抢轿”的场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另外,我虽然当了一次“犯人”,父亲的病却未见有一丝的好转。
母亲现在不得不日夜守着父亲。白天,她经常替父亲拿着翻开的书籍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在看完一页以后翻过新的一页。父亲此时连举手捧书也觉得困难了。他自己叹气说:“怎么,筋骨一点一点僵硬了。”当真,他颤颤巍巍地举起手来时,五个指头拿东西显得不平稳,而且举了一下就觉得“重”,不得不放下了。
那时,弟弟住在外祖母家,宝珠管他。我每天到隔壁的立志小学读书。我每天下午三时便放学了,回家来,母亲便教我坐在床沿,执着书,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乘此时候,母亲下楼去洗衣服,因为父亲大小便都在床上,衣服得一天换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执书让父亲看,父亲忽然说:“不看了。”停一会儿,又说:“拿刀来。”这是指我们房中的一把切瓜果之类的钢刀,长方形,长有半尺,宽有寸半,带一个木柄。我拿了刀来,问道:“做什么?”父亲说:“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那时我原也觉得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还是把刀给了父亲。父亲手拿刀,朝刀看了一会儿,终于把刀放下,叫我拿走。父亲也不看书了,叫我去看看母亲洗衣完了没有。我下楼,看见母亲已洗完衣服,就对她说:“爸爸欲剪指甲。”
母亲就上楼去了。后来我再进房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眼眶有点红,像是哭过。到晚上,等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叫我拿刀给他,他想自杀。原来母亲听我说父亲要剪指甲,进房后就要给父亲剪指甲。父亲自己却把刚才想要自杀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他说:“病是一定没有好的希望了。这样拖下去,何年何月可了,可不把你拖累了么?”而且他自己也一天一天不耐烦了,一举一动都得人帮助,这也不好受呀。父亲又对母亲说,虽然暂时不缺钱,但明知病不能好,每天花不少钱弄吃的,这不是白花了吗?还不如省下来,留给母亲和我们罢。父亲又说:教养两个孩子成人,没有他,母亲也会办得很好,只要有钱,母亲什么都能办好。这都是父亲想自杀的原因。母亲自然认为这些都不成其为理由。母亲认为父亲的病还有希望可以治好。即使不能治好,只要不死,瘫痪怕什么?大家都在想法,如何使父亲不感到寂寞,不感到任何不便。而且父亲除了不能动,原也没有什么痛苦,为什么就“活得不耐烦”了?
据母亲说,父亲终于答应,不再起自杀的念头了。但是母亲仍不放心,切实叮嘱我:以后把刀子藏好,剪子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父亲了。
这半年里,每逢星期,外祖母早上派阿秀送食品来,顺便带我到外祖母家吃过午饭,又由阿秀带了我和弟弟一同回来玩一会,然后同弟弟回去。又逢到星期了,阿秀又来了,母亲却不让我去。父亲知道母亲的用意,便笑道:“让他去,我答应过了,一定守信用。”
午后,阿秀和我及弟弟回来了,阿秀把一个衣包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原来是给我和母亲做的新衣,有夹的,也有单的。阿秀说,这都是宝珠做的。料想母亲一定忙不过来,以后,我们的衣服都由她做,还向母亲要了父亲衣服的尺寸去。母亲却将事先写好的一个字条偷偷交给阿秀带回去。
隔了一天,外祖母带了宝珠和阿秀来了。外祖母对母亲说:“你说暂时瞒着姑爷,我却要推开天窗说亮话。”父亲摸不着头脑。外祖母又说:“请郎中瞒着病人,不好。”父亲听这样一说,便猜着几分了,说:“又有什么和尚道士会医的罢。”外祖母说:“不是和尚道士,是东洋鬼子。”于是就一五一十都说明白。原来是母亲听说南浔镇(离乌镇约二三十里,太平天国后许多暴发户都出在这个镇上)有个西医院,医生是日本人,请外祖母设法打听。外祖母派陆大叔去了一天,打听明白,这个医院的日本医生可以出诊,诊费每日十元,外加伙食费每日五元,药费另算,到乌镇来回作三天算,如请来诊,合计大概要五十余元。
父亲听了摇头,说:“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日本人未必有本事治这怪病。”
外祖母说:“姑爷,管他能治不能治,请来识识也好。五十多块钱,我还不算一回事。”
母亲和宝珠也帮着说。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于是母亲写了封信给那个医院,请于五天后派医生来镇,并付定洋四十元。
到期,外祖母和宝珠带阿秀一早就到我家等候。祖父不愿见外国人,出外找朋友去了。祖母、大姑母也都躲开,三个叔叔好奇,赖在客堂,却被外祖母赶走。
大约十点钟,医生来了,却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带个翻译,四十左右,还有个女看护(中国人),二十来岁。外祖母问那翻译:“医生呢?还在船上?”翻译指那日本女人,说她就是医生。外祖母很不高兴,正想发作,幸而母亲下来了,对外祖母说:“女的也一样,请他们上楼罢。”于是都上楼去,挤满了一房。女医生倒很大方,脱了木屐,爬到床上,开始诊病。此时正当初夏,气温较高。翻译说,病人该脱上衣。母亲和宝珠,那个女护士,三人一起动手,才把父亲的上衣脱下。照例听、敲以后,医生按着父亲的胸脯,问“痛不痛”?又使劲捏住父亲的手臂关节,问“痛不痛”?父亲都摇头。医生向翻译叽哩咕噜说了几句。翻译说:该脱裤子看看。外祖母听着笑了。宝珠有点害羞,站远了点儿。母亲便同那女护士替父亲脱裤子。医生按着父亲的支起的两腿,又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问:病人的腿能不能伸直?老是这样支起的吗?母亲叹气回答:一年多了。医生又把听诊器按在病人肚上,这边,那边,听了好一会,又要父亲侧卧,把听诊器在背脊从上到下都听过了。蹲在床上一会儿,看着病人全身无肉,摇了摇头,这才下床来,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说:诊断完了,下楼去罢。母亲拿一条夹被给父亲盖好,留阿秀在房,便一同下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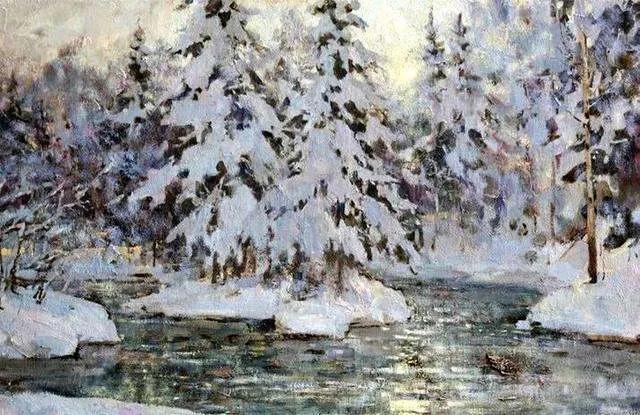
到了客堂,外祖母请医生等吃茶点,一边问:这病有办法治么?翻译同医生商量了好多时候,然后回答:老太太明白,病人全身肉都落尽了,又听说饮食照常,这个,你们小心照管,不会马上出事。外祖母又问:这是什么病?翻译又同医生讲了几句,拿起桌子上的纸、笔,写了两个大字:骨痨。
母亲看是“痨”,就有点吃惊,问翻译道:“骨痨是什么?”翻译回答:这是痨病的虫子钻到骨头里去了。
母亲便不再问。外祖母和宝珠也不出声,神色都变了。
女护士打开一个大片包,医生从中拣出两三个玻璃瓶,瓶内有药丸,也有药粉。医生各取若干,分别包成二十多包,向翻译说了一通。翻译便说:这药丸和药粉每天各吃一包。这时,医生对外祖母鞠躬,便带着护士往外走。宝珠拉住那个翻译问:是什么药,管什么?翻译回答:都是开胃药,兼带润肠。又说,诊断完了,我们下午便回南浔。此时护士又回来说:药价四元。
外祖母又同母亲、宝珠上楼去,祖母也出面了,同到父亲房里,母亲把医生的诊断简短说了一说,便问父亲:“你知道什么叫骨痨?”父亲想了半天回答道:“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父亲说话时心平气静。外祖母和宝珠都哭了。父亲笑道:“原来说是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书了。却和母亲低声商量什么事。一、二天后,父亲口说,母亲笔录。我在旁虽然听得,却不解其意义。母亲一面笔录,一面下泪,笔录完,母亲重念一遍,父亲点头说:就是这样罢。但是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应当请公公来写。”父亲听了,苦笑道:“你想得周到。”于是叫我去请祖父来。祖父来后,父亲不把母亲写好的底稿给他看,而自己再念一遍,请祖父写。最后二句,我却听懂了:“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还有年、月、日。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的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立遗嘱后的一天,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小说留着,却指着一本谭嗣同的《仁学》对我说:“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却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还常常勉励我:“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母亲要我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语说“长兄为父”,弟弟将来如何,全在我做个什么榜样。
第二年夏季,气候酷热。母亲见从前预备给曾祖父住的两间楼房(家中称为新屋)此时空着,便找人背着父亲住到新屋的靠西一间楼下。安排我和弟弟住在靠东一间楼下。这年夏末秋初,父亲去世了。父亲死时并无痛苦之状,像睡着似的永远不醒来了。当母亲唤父亲不应时,还以为父亲睡酣,但脸上血色全没有了,摸摸脉搏,才知道父亲真个离开爱妻和娇儿,到他常常想念的第二次变法维新国富兵强的中国去了。
我和弟弟正在写字,听得母亲一声裂帛似的号,急忙奔去,却见母亲正在给父亲换衣服,我和弟弟都哭了。一会儿,家里人都来了。七手八脚想帮助母亲。但是母亲摇手,泪如雨下。母亲亲手用热毛巾把父亲全身擦干净,换上殓衣,很小心地仍让父亲的两腿支起。
父亲的遗体移到楼下靠东,平常作为会客室的一间。母亲始终只是吞声呜咽。直到外祖母和宝珠哭着进来时,这才放声大哭。
因为天热,第二天就殓了。丧事既毕,母亲在父亲逝世的屋内设一个小灵堂,只供一对花瓶,时常换插鲜花。父亲的照片朝外挂着。照片镜框的两侧,母亲恭楷写的对子是: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父亲终年三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