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邓安庆,节选自布鲁斯.N.沃勒著《思考哲学基本问题》陈晓曦 杨晞帆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2016 一书中译本前言部分
近年来,我身边真心喜欢哲学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他们有的是事业有成的领导者,有的是生意亨通的企业家,有的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当然也有一些“民哲”,再加上那些“被教育”而爱上哲学的“天之骄子”—复旦大学的学生,给我的一个真切感觉就是,对哲学的真实需要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感觉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哲学之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的人而言,无疑是非常的惬意。这种惬意并非是说,在寂寞人生中会增加几个“同路人”(因为对于真正喜欢哲学的人而言,从来就不会感受到“寂寞”,反倒是“寂寞”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清净”和格调的“纯粹”,没有这些,何以抵抗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嘈杂”和“诱惑”?),而是如同审美愉悦那样,当一艺术品的审美趣味被同侪的鉴赏力品鉴出来产生的品味相通的精神快感。
哲学常常被人误认为“无用”之学,说它既不带来“面包”,也不赐人“长技”,既不令人“富贵”,也不助人“升官”。而一般哲学老师最怕人问的问题,据说就是学哲学究竟有何用?这实际上是长期被灌输的“假哲学”留给人们的“偏见”。
世上只有“乞丐”才需要别人“带给”他面包,正常的人依靠自身的“雕虫小技”就能取得,何劳“哲学”之“大驾”?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标只定位为获取“面包”,他确实不需要来糟蹋哲学。但凡一个人有更高一点点的追求,什么“长技”、“升官”和“富贵”,虽不用哲学也可成之,而若有哲学襄助,定将让其取之有道,得之无愧,这也是无需申论的常识了。哲学尽管不是“技术”,却能助人以“长技”;哲学虽藐视一切“升官之道”,但能教导真正的“为官之道”;哲学耻谈“富贵”,却能教人何以“既富且贵”。
人之“贵”全然不在于他的面包,官位和财富,而在于他的知识,才华和教养。而真正的知识、才华和教养的获得,非有哲学不能成。哲学既不教人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算术之知”,亦不求解“太阳晒石头热”这样的“物理之知”,它只引导你探索真知何以为真知,即一个能称之为“真知”的“知”何以为“真”的标准或“道理”,因而,哲学的知识乃是对“真理”之判准的探索,它实际上已经内在地转“知”为“智”了。于是,哲学的“知”基于“科学”的“知”,但又超越甚至“高于”科学的“知”。所谓“超越”就是“跨越了”具体科学知识的狭隘“界限”,具有了“世界性”和系统性,正如“物之理”是物理学的知识对象一样,哲学的知识对象是“知识”本身,因而是知识它自身的那个“世界”或“体系”;所谓“高于”,不是说哲学的“知识”在“天上”,而是说它是一切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的具体知识的“根基”或“基础”,体现为对科学本身所“不知”和“不思”的所谓“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之“理”的探究与阐明,这种探究与阐明或许不能成为人人同意的“知识”形态,但却构成我们一般去求取真知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所以,就此而言,只有哲学才有可能使我们具有“真知”,即对“世界”(万有)之“第一原理”之理的知,这样的普遍的知才有可能使我们具有超越狭隘、跳出自我而从“世界”与“人类”视野来思想的“才华”和“教养”。只有具备这种普遍化的视野和心胸,人才具有“人类”的高贵性。一个人“才华横溢”,本事大得不得了,不是说他“力大无边”,“无所不能”;一个人知识广博,见识高远,不在于他“无所不知”,“无见不识”。人的知识、才华和教养主要在于他的思想力与判断力。如果一个人有“知识”,却判断不了“是非善恶”,那他的“能力”与“才华”不但不能助其以贵,相反地却要助其以恶。所以,真正有才华的人会启动其“判断力”,对人类面临的一般问题能做出正当的判断,对人类一般行为法则能够承认,知道如何正确区分何者“能为”何者“不能为”,何种“该为”何者“不该为”,随之能够“自我立法”,杜绝做“不能为”“不该为”之事,而对“能为者”尽其力做好,对该为者尽其才达于至善,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才华。因此,真正的才华不仅是个“转知为智”的工作,同时还要进一步“转智为德”,以德去恶扬善,这样才有真正卓越的“教养”与高贵。

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教人以高贵的学问。人的卓越与高贵,不是天生,不靠出身,而仰赖于我们自身精神品质或灵魂品质的高贵。而精神或灵魂的高贵,非哲学不能成之。因为精神或灵魂的品质以思想和判断为支撑,而高贵的思想与判断无不需要得到卓越的哲学之涵养。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哲学的基因,儿童天生就像哲学家,但是,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认识到哲学的需要并将哲学需要自觉地予以呵护和涵养。生活的艰难与困苦,往往把人拖累在为面包而奋斗的旅程中,使人压抑并泯灭其天性中的哲学需要。有了美味的面包但教养粗俗的人,从来体味不到一点精神层面的愉悦,只会在贪图世俗的享受、权力和金钱上耗费其全部的心血与体力,从而只能将上天赋予他的宝贵生命止于低俗而无法超升。只有少数幸运者能体会到哲学生活的至趣至乐,自觉到人的更高使命是将自然生命自我造就为卓越,因自我造化的卓越而显高贵,以此回报和延续着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从而对哲学产生不可或缺的强烈需要。一般而言,我们生活中有三类人容易发现并尊重内心深处的哲学需要:一是心有惧怕者,二是天性好思者,三是追求高雅者。
心有惧怕者既包括成功人士也包括大量失意者,当成功者在某一晚突然被自己的成功而深深地震惊:我何德何能这辈子能发这么大的财,能当这么大的官,能赢得如此大的成功?这时,如果他是一个真有教养的人,就会产生哲学的冲动,不仅仅是探究成功的深层原因,而是探索生命的意义,我的一生真的是为这些而活的吗?我的生命能承受得了如此的成功吗?内心的惊讶与恐惧就成为他走向哲学的引线。当然,大量无教养的人,当被自己巨大的成功所惊讶时,内心的惧怕不是将其引向哲学的沉思,引向生死意义的探究,而是引向寺庙去烧香拜佛,祈求神佛的保佑;失意者同样如此,会在某一天被自己的挫败深深地震惊,内心的惧怕既有可能把他引向探究生与死的奥秘,人生的真谛,从而走向哲学,也有可能让其彻底拜倒在神佛殿下,以为上帝会拯救一个不动脑筋的人或精神的侏儒。
天生好思者离哲学最近,因为哲学就是思想的学问。每一个人长大成人,无论家庭富贵还是贫穷,都必须独自地面对正在他自己面前展开的生活,这就必须自己学会思考,而不可能事事求得父母的指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们动脑筋想清楚,才有可能做好。不思考,不动脑筋的人,生活如果不是一塌糊涂的话,也几乎就会一无所成。人生的短暂使得我们难以承受不断地犯错,人生的不可重来又使得我们无力支付挫败之不可挽回的代价,这一切都赋予了思想之于人生的至关重要。但是,“好思”不等于“会思”。人类的可悲往往就在于,当我们急需思想时,却徒然发觉自己并不会思,于是急忙地从权威,从成见,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取一现成答案来救急,殊不知,别人的思想成果对于自己当下的真实处境并不必定有效。就像一个“救急国家”不会国泰民安一样,不断陷入救急的人生必然也是危机四伏。所以,美好生活需要好思者,而好思者需要变成会思者,就必须经过哲学的专业训练。因为哲学就是教人思想并以思想为生。只有学会哲学思考,才能说会思想。会思想的特征是通过思维的逻辑抓得住问题的实质与根本。好思的人也会胡想乱想,但他的思想可能并无逻辑,而哲学思维的逻辑训练,最主要的是培养思想之“务本”的能力。“本立而道生”,原因就在于,“务本”能防止我们胡思乱想以假乱真,以表象代实质,从而错过根本问题。只有抓住根本问题入思以得问题的根本解决,才会具有“高屋建瓴”的才华,这种才华唯有哲学能成之。

追求“高雅者”之所以能发觉并尊重内心的哲学需要,是因为这种追求本身就足以表明追求者已经无法容忍粗鄙生活的价值颠倒了。人的粗鄙并非与生俱来,但世俗生活的柴米油盐和风光攀比,极容易让人活在生活之外,生活不是自身高贵生命的造化过程,反倒成了给别人看的“面子工程”,于是物欲、权欲、名欲这些能给生活增添亮色的表相就会无限膨胀,以至于无力从中脱身以进入自身高贵生活的塑造之中。相反,内心追求高雅者总会把高贵的生命理想与目标放置前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这一理想与目标常如灯塔,照亮其前行的路,不会让其落入俗鄙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追求高雅者之所以能走向哲学,在于他必须思考清楚,究竟何为生活的高雅与高贵的生活这一作为其终生理想和目标的东西,以及如何这种生活值得自己过一辈子而不管别人如何看,否则他很难拒斥粗鄙生活的诱惑与攀比。
而当一个人能够为何种生活是高雅的,何种高贵的生活目标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进行定位或辩护时,他就已经是一个不俗的哲人,而且可算是真正的哲学家了,因为他已经能够解答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哲学的最高问题了。追求高雅者不管是否受到了哲学的专业训练,他一定能够为了心中认定并相信的“高雅”确立起一套价值高低的等级秩序,从而使得其心灵有序而不会随意被世俗生活的滚滚红尘所扰乱(本文由慧田哲学推送)。这样,他/她就能真正进入本身的生活之中,这种生活因其是本己的,从而是自由的,它追求的是哲学的真实:“是其所是”,因而是独立的;因其自由而独立并担负者完成自然生命之向高贵生命自我塑造的使命,因而它不一定能享受到世俗认同的幸福,但一定是配享幸福的,从而是有尊严的,因而是真正体面的。无论他人生活如何风光与艳丽都无法与这种本然的高贵相攀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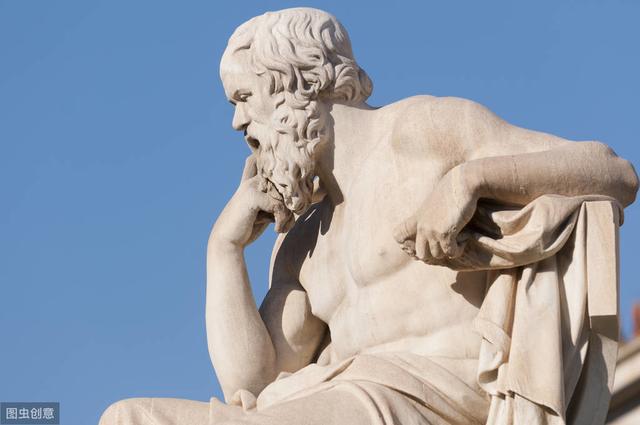
人们需要哲学,实际上就是希望哲学能将其引向这种通往高贵生命的自我造化的道路。因为并非每一种天然的哲学爱好能最终成就一种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从来不能作为一种名词(Philosophy),作为一种现成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灌输给谁,哲学之能受用,根本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个动词,即德语的philosophieren,作为一种“务本”的思想活动而融化到人的血液中,变成其精神或灵魂的品质,从而对生活形式乃至生命进行“自我塑造”。哲学作为这样一种精神或灵魂的自我塑造的活动,需要得到专门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