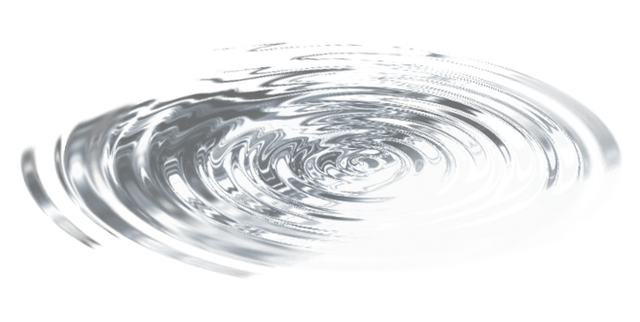1911年1月19日
在我看来彻底地完了——去年我每天醒着的时间连五分钟都不到。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很多。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句话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句话在我的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大不相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觉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少多少。
有一次我构思一部小说。在小说中,两个兄弟斗来斗去,他们中的一个去了美国,而另一个则待在欧洲一处的监狱里。我只是有时候开始写上几行,可是这使我马上感到疲乏。有一次,在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去看过祖父母并总在那里吃过用奶油涂过的一般的、可是特别软的面包之后,我又这样写上一些关于我设想的监狱。我现在可以这么做了,我绝大多数是出于自负这么做的,我在桌布上将纸移来移去,敲着铅笔,在灯下向四周环顾,想吸引谁来将我写的东西拿走看一下,并对我表示赞赏。在这几行里主要是写监狱的走廊,首先是那里的安静和寒冷;对于留下来的兄弟还说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好兄弟。我大概曾对我所描写的东西失去价值有过瞬间的感觉,可是我在那个下午之前对这种感觉从没有过多地注意,如果我处在我已习惯的亲戚中(我害怕得如此厉害,使得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情况中让我感到一半的幸福),坐在熟悉的房间里圆桌的周围,而且我不能忘了,我是个年轻人,有责任从这个目前不受干扰的环境里成长为大人。一位喜欢笑出声来的叔叔终于从我这里取走了那页纸,因为我只是微微地捏着它。他仓促地看了一下,又交给了我,甚至连笑声都没有,只是对着另一些用目光追着他的人说,"一般的胡说八道",对我却什么也没说。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仍像早先那样匍匐在就是说我那页没用的纸上,可是我却真实地感觉到挨一棒子被赶出了这个集体。叔叔的判决带着已经几乎是现实的意义一再地在我心中回荡,在这个家庭感情里,我本人就已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冰冷的空间,我一定要用一把火来温暖这个空间,这火正是我要去寻找的。
1911年11月5日
我要写作,额头却在不停地颤抖着。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房间就处在整个寓所的噪声大本营中。我听见所有的门在碰撞,这种声音只不过为在其间歇中跑动的脚步声所淹没,我还听见厨房里炉门如何关闭。父亲乒乒乓乓地推门关门,披着垂地的睡衣穿过我的房间,隔壁房间里在把炉灰刨出来。瓦莉(卡夫卡的二妹)不知在问谁,父亲的帽子是否已刷过。她的叫喊声穿过前厅,仿佛穿过一条巴黎的街道,那头叫喊着回答,发出几近亲切的嘶嘶声。寓所的门把被拧动,声音像发自黏膜炎患者的脖子中,然后像女人唱着简短的歌句似的启开,复以一种沉闷的男性的冲撞关上,听上去真是肆无忌弹到了极点。父亲走了,现在开始了较柔和的、较分散的、更无指望的嘈杂声,由两只金丝雀的声音领唱。在此之前便已想过,金丝雀的声音再一次使我想起,我是否可以启开一条门缝,像蛇一般爬到隔壁房间里去,爬在地板上请求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小姐安静下来。
当昨天晚上马克斯(卡夫卡挚友)在鲍姆家朗读我小小的汽车故事时,我感到一种苦涩。我同所有的人都隔绝了,将下巴埋在胸脯上抵御这个故事。故事中杂乱无章的句子有着宽阔的裂缝,足以容双手同时插入;一句响得高,一句响得低;一句磨着另一句,像舌头磨着一只蛀空的牙齿或一只假牙;一个句子以粗糙不堪的开端迈步走来,导致整个故事陷入令人厌烦的莫名其妙之中;一个是对马克斯的模仿(指责是压低了调子的一一而我却得到鼓励),它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跑了进来,有时候看上去像是在一个舞蹈学习班的最初一刻钟内。我的解释是,我时间太少,安静的时刻太少,未能将我的才能的潜力构成整体发挥出来。因此不断出现断裂的开端,这些断裂的开端比如说贯穿于这篇汽车故事始终。倘若有朝一日我能够写下较大的整体,从开头到结尾一气呵成,那么这个故事将永远不能脱离我,我将能够平静地、睁大眼睛,作为一篇故事的直系血亲来倾听人们朗诵它。可是像现在这样,故事的每一小段在无家可归地流浪,并将我朝相反的方向推去——假如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还将感到高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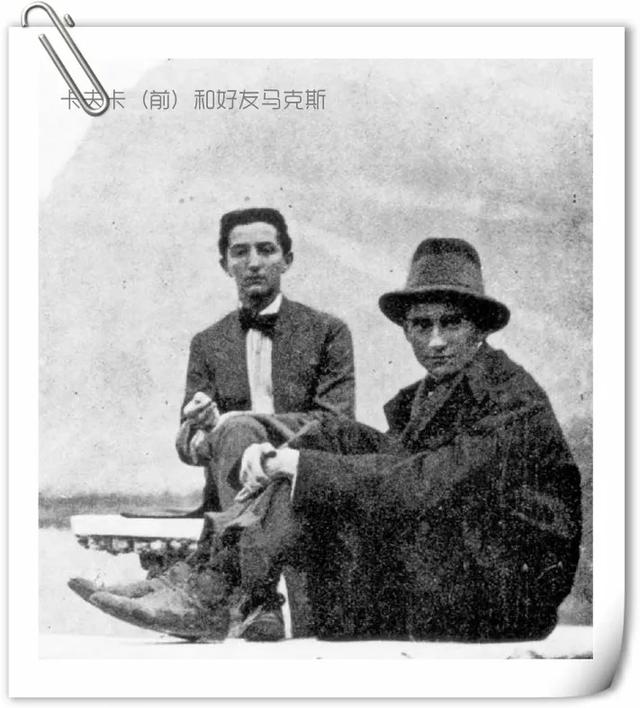
1911年11月15日
……
我在感觉良好时能够逐字逐句地构思,甚至在一瞬间确实找到了具体的表达语言。可是当我坐在写字台边试图把这一切写下来时,它们便表现得枯燥、颠倒、笨拙,与整个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畏畏缩缩,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原先的构思并没有丝毫忘却……由于没有能力将那丰富的世界诉诸笔端,所以这丰富的世界既恶劣又烦人。人们既为它所吸引,又无法接近它。
1911年12月29日
……
结尾(甚至一篇小文章)的难处不在于,明明前面的内容不能导致一团火产生,我们的感情却硬要在文章的结尾处燃起一团火来。结尾的难处是这么产生的:哪怕最短小的文章也要求作者进入一种自我满足和忘我潜心的状态。从这种状态走出来步于日常生活的空气中,没有强有力的决心和外界的鞭策是难以办到的。所以,与其将文章圆满结束、平静地滑出去,还不如在此之前,借不安的推动力挣脱出来,然后反过来用双手从外部来完成结尾。这双手不仅要干,还必须锲而不舍。
1913年6月21日
……
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致粉身碎骨呢。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葬在我心中。我就是为这个而生存在世上的。我对此完全明白。
1914年8月6日
……
从文学方面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写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使其他一切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能使我满足。可是现在我进行那种描写的力量变得不可捉摸了,也许它已经永远消逝,也许它有朝一日还会降临,我的生活状况无论如何对它是不利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向山顶飞去,但在上面一刻也待不住。其他人也摇摇晃晃,但那是在下方,而且力量比我大。当他们有坠落的危险时,亲戚们就会抓住他们,亲戚们就是为此目的走在他们身边的。而我晃动在上方,可惜这不是死亡,却是死的永恒的折磨。
爱国主义的游行。市长的讲话。然后他消失了,然后其他人出场,德语口号:“我们热爱的君主万岁,万万岁!”我站在一边看着,射出恶狠狠的目光。这类游行是战争之最令人讨厌的伴随现象之一。这是由犹太商人们发起的,他们一会儿是德国人,一会儿是捷克人,虽然自己这么认为,但从来不能像现在这样扯着嗓门喊出来。当然他们也吸引了一些人加入进来。组织得不错。这将每天晚上来一次,明天星期日将举行两次。
1914年12月13日
……
回家途中对马克斯说,躺在床上死去我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只要不痛得特别厉害。我当时忘了补充,后来又故意不再提起,因为我写的最佳作品的成功原因便在这种能够心满意足地死去的能力之中。所有这些杰出的、有强大说服力的段落总是写到某人的死亡,这个人死得十分痛苦,承受着某种不公正待遇或至少是某种冷酷的遭遇,这对于读者,至少在我看来是有感染力的。但我却相信,诸如在待死的床上能够感到满足这类描写暗中具有游戏的性质,我希望能作为这么一个弥留者死去,所以有意识地利用读者集中在死亡上的注意力,头脑比他清醒得多,我估计他会在待死的床上叫苦的,而我的倾诉是尽可能完美的,也不像真的倾诉那样会突然中断,而是既美且纯地发展着。就像我总是向母亲倾吐苦经那样,实际上的痛苦远甚于所倾诉的。在母亲面前我当然不会像面对读者一样要用那么多艺术手法。
1914年12月19日
昨天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写了《乡村小学教师》。担心会写得太晚,超过了一点四十五分。这担心是正确的,我几乎没有睡,只做了三个短梦就到办公室去了。在那儿精神仍是恍恍惚惚的。昨天父亲为工厂的事责备我:“你就这么捉弄我,叫我出洋相。”接着我就回家了,安静地写了三个小时,同时始终意识到:我的罪过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不像父亲说的那么严重。今天,星期六,没有去吃晚饭,一则出于对父亲的害怕,二则是为了充分利用夜晚时间来写作。我只写了不很成功的一页。
初看上去,每篇小说的开头都是可笑的。要使这个新的、尚不完备的、处处有懈可击的肌体在世界那已经完备了的结构中站住脚,似乎是没有希望的。世界的结构同任何已经完备了的结构一样力求闭关自守。但人们显然忘了,小说(如果它有成功的权利)也有着自己的完备的结构,虽然这种结构可能还没有充分展开。因此在小说开始时对此产生绝望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像父母对婴儿的绝望,觉得不应该让这特别可笑的生命来到世间一样。当然人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感觉到的绝望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不过上述考虑可以使人获得一定的依据。这个方面,经验缺乏已经给我带来损害了。
1916年7月5日
共同生活的艰难。为陌生、同情、快感、胆怯、虚荣所迫,只有在底下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能够对爱情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它是无法寻到的,仅在某个瞬间的瞬间向上面闪一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