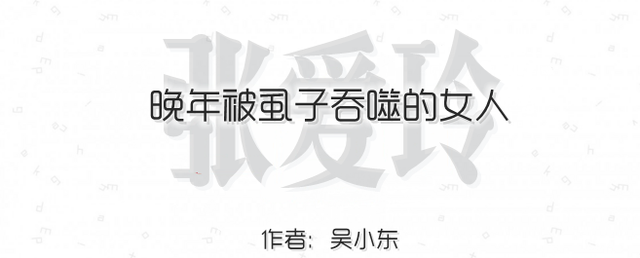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 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二十九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