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与真诚也属于自我意识结构的应有之义。由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我们提出自我意识包含一种忏悔的精神,而与忏悔相连的就是“诚”的问题。自我意识无非是要达到对自我真实的把握,那么对自我的这种把握就是真诚。

什么叫真诚?真正能够达到自我意识的真诚,不是孟子所讲的“反身而诚”。我们前面讲,“反身而诚”可以说是想一想就达到真诚了,往自己心里面看一看就达到真诚了,或者扪心自问就达到真诚了,这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人心不是单一层次的东西,它是一个立体结构,而且是一个无限延伸又不断深入的结构。
真正的真诚,也不像老子讲的“复归于婴儿”。人都是从婴儿长大的,所以老子主张只要每个人想想自己的儿童时代,像小孩子那样回到纯真,就可以做到真诚。我们通常也说,小孩子不会说谎,童言无忌,皇帝的新装的谎言就是一个小孩子拆穿的。但这是不一定的,小孩子只是还没有学会说谎的技巧,但从本心来说,他也是想要撒谎的,只要他觉得有必要。只不过他的谎言大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罢了。人是能够撒谎的动物,连小孩子也不例外。更不用说一个成人完全回到童年是否有可能,除非他得了失忆症。
庄子讲的倒是更适合于成人,他主张要“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什么叫环中?门枢转来转去,中间那个环是不动的。你们捉对厮杀,争来争去都在转圈,你咬着我的尾巴,我咬着你的尾巴,而智者就站在环中,跳开是非,你们去争,我不介入,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老谋深算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们互相打倒,我反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一个狡猾的态度。那么这能否解决自我意识的自欺的矛盾,达到真正的真诚呢?显然不行,这解决不了矛盾,只是逃避了矛盾,而且暗藏机心。
再就是禅宗所讲的“难得糊涂”,就是装糊涂、装傻。“难得糊涂”是为了逃入虚无,就是什么东西讲起来都好像知道,但是又好像不知道。做事也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对错,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行。这与庄子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而且是一种极无诚意的虚无主义。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自欺的矛盾?应该是在行动中。“反身而诚”也好,走进“环中”也好,“难得糊涂”也好,都只是一种态度,但不是一种行动,都是对生命力的一种压抑和放弃。行动才暴露你的本质,你是个什么人,行动起来就知道了,做一做就知道了。人是很容易自欺的,尽管很容易自欺,你还得行动,能够破除自欺这个“环”的,就只有行动。你要做一做试试,不要老是怕这怕那,防止这防止那,在观念里面打转。你一行动起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才会暴露出你的真相。当然这只有在行动中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才能做到,行动是为了认识自我。由此就生发出一种忏悔意识。在行动过后,回过头来再看,你会鲜明生动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及自己在自欺中埋藏着的根本恶。在不行动的时候,待在屋里、躺在床上,那就没有什么好反思的,只会觉得内心一片纯洁。而有了行动之后,你就可以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反思了,于是从这个反思里面就产生出了一种忏悔精神。
鲁迅著名的小说《伤逝》,是一篇非常深刻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的哲学含义揭示出来。尤其是涓生和子君谈恋爱同居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生活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每天陷入赚钱谋生的琐事中,过得极其艰难,爱情最后也逐渐消失了。有一天涓生就对子君说,既然你不顾重重障碍、冲破了传统观念来跟随我,说明你是一个独立的女性,那么你现在也可以离开我,独立地去过自己的生活,总比两个人缠在一起去死要好。子君受了这致命的一击,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她只好回到她父亲那里去了,不久就死了。涓生非常后悔,不光是后悔,而且非常痛心地忏悔,他认为是他用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把子君杀死了。当时这种五四青年,人人都用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样一套空洞的话语来自欺,还自以为真诚。但正是这种真诚,这种把真相直接摆出来的直率的态度,把子君害死了。最后涓生满怀忏悔地说:“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为什么跨进新的生路就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呢?真诚难道就做不到吗?真诚还真是做不到。人们意想中那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真诚,不光是做不到,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有,那就是伪善,或者是自欺。涓生自认为很真诚,他要求自己彻底的真诚,他跟子君的关系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是按照新的女性、新的观念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幸福的。但是最后搞成这样一个败局,他认为最后的责任在他,他把说谎的责任摆脱了,把真话让对方承担起来,真话是不堪承担的。什么是真话?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爱了,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还有待于探讨。但是,为什么要用遗忘和谎言做前导?涓生实际上是对自己当时的那种真诚加以忏悔:我不该那么真诚。太真诚了害死人啊!连害死人都在所不惜的真诚,是虚假的真诚,是走向死路的真诚。所以要走出一条生路,就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在这种遗忘和说谎的前导的背后,才有真正的真诚。因为我知道这是说谎,知道这是生命中无法摆脱的自欺。
中国人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真诚,鲁迅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他不盲目相信真诚,但是仍然要试探、要探讨真诚。真正的真诚不是当下即得的,而是有待于在生命的道路上寻求的。而走上生命道路的第一步,则是遗忘和说谎:要把以前的那种真诚忘掉,以前的那种真诚不值得耿耿于怀,那其实是一种虚伪;说谎不是要骗人,而是指所有自己说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那只不过是一种试探。说真话是不容易做到的,所有你当作真话说出来的东西,都只代表你有说真话的意图,而不代表你说出来的就是真话。所以你宁可承认这些话实际上是说谎,承认人摆脱不了自欺这一事实,以便保持对自己的一种忏悔意识。然而,明知自己说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真诚,但是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姑妄行之,把它当作真的那样去做,这就是向新的生路迈进的第一步。反之,你自以为你说的话是真的,你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叫自我欺骗而不自知,你就会被自己的实践行动所驳斥,所以你最好预先就要留下忏悔的余地。
忏悔和后悔不同,中国人经常分不清这两者。你说忏悔就是你后悔了吧,当初你就不该那么做嘛!忏悔当然是事后的,但它不是着重于当时那么做的后果,而是着重于动机,着重于对自己人性的恶劣本性的自我批判。忏悔与后悔都是于事无补的,已经做过的事情无可挽回,但后悔导致人有一种想做某些事情来将他所造成的后果加以弥补的意向,而忏悔则不是要把自己的过失补救回来,而是要对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挞。后悔追究的是所犯的错误,而不追究为什么会犯错误;忏悔则对罪恶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后悔深刻得多。忏悔不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恶从善——比如你以前做了不少坏事,从今以后要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相反,忏悔就是不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做个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变的,但你愿意为自己的有限性承担责任。这种有限性肯定是会导致罪恶的,要承认这一点,要看清这是人性的本质结构。人性本恶,康德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恶,一切恶都是从人的有限性生出来的。根本恶是不可能通过忏悔摆脱掉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忏悔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把握自己的自欺结构,从而成为一个有深刻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他也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自封为圣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会更加宽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对待他人。
忏悔的目的其实就在这里,即为自己的根本恶承担起责任,促成一种人性的宽容性和人情味。同时,正因为忏悔在事后才发生,所以它并不束缚人的手脚、妨碍人的行动,当然也不能消除人的自欺。人在行动中总是有一种自欺,忏悔不能消除这种自欺。但是它能在人的行动中、创作过程中、行为过程中揭示一个永恒的真相,就是人总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性,但它又总还保留继续接近真理的可能性。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人总是可以再努力的,所以总是可以接近真理的。犯错误当然是远离真理了,但是我们犯错误也要有进步,不要老是犯低级错误,应该从低级的错误到越来越高级的错误、越来越复杂的错误。这就是人性的进化,这本身就是向真理不断接近。低级的错误离真理最远,高级的错误应该说离真理就比较近了!它把人的层次、水平提高了。
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当然并不能避免犯错误,但它不会老是重复犯过的低级错误。像纳粹所犯的,就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种族主义。德意志民族、日耳曼民族的确很优秀,但说它是至高无上的优等民族,其他民族都该被奴役,那就是很低级的错误了,稍微有点知识文化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个民族由于有忏悔精神,就不会老是重复犯这个错误,如果能够避免犯低级的错误,这个民族就把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日本这个民族由于缺乏忏悔精神,只有后悔意识,只是从灾难性的后果来反思“二战”,没有对人性的劣根性保持警惕,就很难保证不重蹈覆辙。人性本身的自我本质——人类自我意识的这种自欺的矛盾,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忏悔过程中,一次次地退回到自己的根本来拷问自己,才会被扬弃,才会从不自觉的自欺走向自觉、走向真诚。哪怕开始显得非常虚伪甚至伪善,但是只要能够反省,就会变得越来越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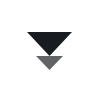
这样一种自欺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是一个矛盾,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在逻辑上是不能并存的,但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这种矛盾会得到扬弃和调解,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在时间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调解。每一次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都不在同一个层次,被欺骗者总是比较靠前台,而欺骗者总是躲藏在后台,被欺骗者总是努力去挖掘出后面隐藏着的欺骗者,从而使人性的层次逐一暴露出来、深化起来。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人性结构,就是在人们有意识的行动中,往往会有潜意识在后面起作用。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但是为什么引起了哲学家这么大的兴趣呢?就是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含义,它揭示出人的自我意识是分层次的,在时间的进程中,它会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开始是被欺骗者,你当然可以为自己辩解:我被人家欺骗了啊,我上当了啊!但是精神分析学会指出:你潜意识之中是知道的,你并不是完全被欺骗,你在作恶的时候,潜意识之中知道这是恶的,但是你还去做,你骗自己说这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一个更崇高伟大的目标。所以,你是被欺骗者,同时你也是欺骗者。而忏悔呢?忏悔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中向后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探索自己:我当时的潜意识是什么样的?你铁面无私,像一个法官一样对待自己,那你就会拷问出自己背后的这些东西。而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承认这些,我们的精神层次就大大提升了一级,就再也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有凭借对自己的忏悔,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层次有所提升,看出我们内心的后台后面还有后台,我们要不断地深入它。像奥古斯丁讲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深渊”,你在这样一个深入自身心灵的过程中是触不到底、没有尽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对“我是谁?”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反思性的回答。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就是那个“谁”。“我是谁?”本来是一个疑问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我就是谁。”我就是那个对“谁”的追问。我不是任何“东西”,我是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独立的人、任何一个有人格的人都不是一个“东西”,但他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自我反身的问题,要反过身来问自己:我是谁?如果没有达到反身自问,那么我就还不是我,或者说我就还没有自我。而假如有一天,我把这个“谁”追问到了,我们对这个“谁”加以定义、加以规定,使它是一个“东西”了,那我也就失去自我了,我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就只是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对自我到底是谁的追问过程,也就是忏悔的过程,自我追问就是自我忏悔。我就是要看看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内心中、潜意识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在潜意识后面还有潜意识,要将它一步步揭示出来。这种忏悔意识,揭示的是人的虚伪,体现的却正是人的真诚,只有真诚的人才会忏悔,才会面对自己的虚伪。真诚的自我既不是欺骗者,也不是被欺骗者,而是忏悔者,是这个对“谁”的追问。
但对“谁”的追问在人这里是不能完成的,因为人永远是有待完成的,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你就有待完成。有些老人,或者自己还没有老,或者还没有太老,就说这一辈子完了,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自暴自弃了。但实际上呢,每个人在临死之前,只要他还没有咽下这口气,他都是有希望的,他可以在临死之前重建自己的一生。比如,有的人也许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但是他在临死之前吐露了一个真相(大笑),他这一辈子就了不起!他就发挥了他这一辈子的价值。所以人在死之前都不要给自己下结论。我们讲“盖棺论定”,就是盖上棺材板子,才能给一个人下定论。在没有盖上棺材板子之前,人是不可预料的,是不可预先判定的。
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追问就是一种忏悔精神,它永远不能够完成。通过这样一种忏悔,人的自欺的过程就变成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寻找真我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结果,但它可以使人变得日益深刻,使人变得日益真诚。这个真诚的话题,应该这样来解决:如果你想做一个真诚的人,你就要忏悔自己的虚伪,忏悔就是一个必修的功课,忏悔是一个真诚的人的必要素质。每个人都有虚伪,不要回避这个词,只要你有理性,你就会虚伪,而忏悔自己的虚伪就是真诚。“反身而诚”是不能做到真诚的,因为“反身而诚”的预设就是人性本善,人性本善的预设就是认为人的本心不会说假话,比如小孩子不会说假话,小孩子生下来是真诚的,所以,大人要回到小孩子去,要返回到“赤子之心”。人性本善,凡是恶,都是受到外来的影响或污染,这是中国文化设定的一个前提。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是未经反思的。小孩子怎么不会说假话?小孩子当然会说假话,大人如果纵容这种假话,他长大了就更不知道什么是假话了,他的不诚实就会恶性膨胀起来,这就叫作把小孩子“惯坏了”。当然小孩子不一定是有意说谎,他是在试探大人的尺度,大人通常也不会过于在意,往往还会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可爱。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度,让小孩子误以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标准,那就麻烦了,他将来有可能把做任何坏事都当作撒娇或儿戏,笑嘻嘻地去做。所以人是有可能真诚地去做坏事的,甚至可以真诚地去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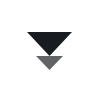
忏悔精神主要是由西方人特别是基督教建立起来的。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都写过《忏悔录》,以奥古斯丁的最早,也最著名。奥古斯丁原来不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包括他的儿童时代,都进行了忏悔。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有震撼力的恐怕还是他在《忏悔录》里所举的一个例子:他年轻的时候和朋友们在街上玩,看到附近的梨树上挂满了梨,就趁深夜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了下来。当时只觉得好玩,现在想来觉得很奇怪,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偷梨呢?我并不是想吃梨,最后还拿去喂了猪,我到底是为什么?他反复想这个问题。最后想到了,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人生来有一种作恶的愉快!人干坏事就有一种愉快,这是从小就有的,没有人教他。你要是说他有什么私心,他的确没有什么私心啊!他又不是想吃那个梨子,他又不是想占什么便宜。但是呢,他有一种作恶的愉快,在作恶中显示出他的能耐。小孩子嘛,他的生命力需要寻找发泄的渠道,如果能让他发挥最大的效果,哪怕是最大的破坏力,他也会感到很愉快,并且感到自己很伟大。有没有私心并不能决定他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是有一些人,把一个卖淫的妓女带到耶稣面前,要对她采用“石刑”——就是用石头把她砸死。这个石刑至今在某些国家里还被保留着。耶稣就说,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去砸她。结果那些人面面相觑,纷纷扔下石头走掉了。于是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判你的罪,你回去,今后好好做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读到这个故事,我经常有一种感动,就是说,这些人的道德水平很不一般!他们肯定都是耶稣的信仰者,他们抓到一个人送到耶稣这里来让他来判,肯定他们是经过耶稣的教诲的,他们都具有忏悔精神。当耶稣说,你们若是谁觉得自己没有罪,觉得自己心地是干净的,就可以用石头砸她。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干净。我想,要是换做某些中国人的话,那就非把她砸死不可,因为不砸死不足以证明自己心地纯洁。看到坏人,你不去砸死他,那你也是一个坏人了。我们今天讲“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就是看到坏人坏事就一定要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势不两立,否则就是同流合污了,就会被别人斗争。这说明我们缺乏这种忏悔精神。西方人的这种忏悔精神主要是在基督教里面。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忏悔”,不是向上帝忏悔,也不是自己内心的自我忏悔,而是向别人,特别是向在自己之上的有权有势的人表白和认错。其实这只是一种生存技巧,当然不是出自内心的。阿Q在遇到王胡的时候说:“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阿Q内心想的也许恰好相反。但这种被逼之下的生存技巧,有时候竟然会成为一种自轻自贱的竞赛,甚至是一种标榜,好像说:你看我多么会忏悔。很长时间以来,每一次搞运动的时候,都有一些人写了检讨书在大会上念,而且痛哭流涕。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提到这种作态,并且对此非常反感。他说忏悔不是要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那都是假的。今天我们流行的说法是:要求某人向某某人道歉。动不动就要求某人向自己道歉,实际上就是要求某人在你面前服软,这样你就特有面子了。忏悔当然也包含歉疚的意思,但并不是向别人道歉,道歉是很表面的,也不光是对被你伤害的人进行补偿和安慰。你伤害了某一个人,你当然应该给他道歉,你赔偿他医药费,你到病房、到他家里去看望他,这都是应该做的。但这是不是就说明你忏悔了呢?未必。这离忏悔还远得很,如果你把这理解为“服软”,那就更是和忏悔南辕北辙了。这些外在的行为可以是内心忏悔的一种表现,但是它们本身只表明了一种民事或刑事纠纷的正常调整,与内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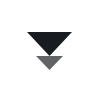
可见忏悔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它不一定要说出来、写出来,它是一个人内心的事情。懂得了这一点,一个人就不能要求另外一个人忏悔。作为一个凡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要求另外一个人忏悔。《圣经》上说:“你忏悔吧!”那是耶稣基督说的,上帝才有权利说这句话,世俗的凡人,没人有这个资格。你要忏悔,你就自己先忏悔,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忏悔。忏悔应该是在内心进行的,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有限性,为自己做过的事羞愧,这样才有可能排除自己的骄傲。但是我们中国人通常会觉得自己本性纯洁啊,觉得自己当时天真烂漫啊、一片真心啊、美好的青春啊……现在很多知青回忆当年,打出的口号是“青春无悔”,觉得自己当年很光明正大。我提过好多次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论调不值得宣扬。你要唱那个时候的歌可以,你在屋子里唱唱,或者和几个当年的朋友一起唱,作为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但是不足为外人道,不应该去向别人标榜炫耀,更不应该把它搬到舞台上去做“红歌”唱,都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老爷爷了,舞台上蹦蹦跳跳的像什么话!(大笑)他们不听我的,他们都觉得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青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走出知青情结》,你不要总时时想着自己是个知青,你要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人,要用人的标准来看待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不要以为你的青春就那么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怀念,但是回过头来,都是需要忏悔的,不要毫无悔过、毫无忏悔地去标榜自己的青春如何辉煌。只有这样才可以消除一些骄傲。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忏悔精神可以使我们在今天摆脱一种戾气。戾气就是一种凶暴乖张的气质,这已经是我们现在国民的共同气质了。现在打开网站,看看微博的跟帖,我们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戾气。每个人都显得那么义正词严,哪怕是满嘴脏话,也都是出于正义感,动不动就说人家“脑残”之类,好像“世人皆醉我独醒”,别人都是那么愚蠢,只有我聪明绝顶,只有我深明大义。实际上,微博上的跟帖表现的才是中国人心底的东西。你在日常生活中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好像还是彬彬有礼、很通人情的,但是到了网上,反正他们又不留名,你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才表现出了他们真正的心智。中国人心中都有一种戾气,都想赢在别人之上,都想发泄一下残暴,想要骂娘,骂这个骂那个……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忏悔精神,那他就可以使自己心态平和,富有慈悲和爱心,能够通情达理、谅解别人。
真正的忏悔是承担自己的责任,原谅他人的过错和伤害,使自己更加具有宽容精神,更加具有对人性的缺点的包容性。忏悔是对人性真相的一种揭示。人都是有限的,都需要宽容,这才是真相。这也是对圣人情结的一种摆脱,不要去迷信圣人,也不要想去当圣人,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人,任何你所崇拜的圣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消除圣人情结,回到人性的真相,就是要回到人的有限性。马克思最欣赏的一句名言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所具有的,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我无不具有。承认这一点并不低人一等,而正是一种平等思想的体现。我忏悔不等于说只有我是坏人,别人都比我好,承认自己有罪并不就是低人一等。谁没有罪呢?只有意识到和还没有意识到之别。
卢梭也写了一本《忏悔录》,忏悔自己一生做过的种种坏事,他诱奸了谁啊,偷了谁的东西啊,说了什么谎话啊,骗了什么人啊,自己多么虚荣、多么下流龌龊啊……他全部都坦白出来,写了很厚的一本。可是写到最后,他来了这么一句: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原原本本摆在你们面前了,没有任何隐瞒,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我想有一天大家都会站在上帝面前,我会说,请大家看一看,有谁比我更好![这段话是卢梭在《忏悔录》的一开始就说了的,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前后呼应。]他实际上是通过忏悔来说明自己其实比那些人还好一些,或者说至少不比那些人差。尽管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但他忏悔过了,而很多人还没有忏悔。
只要没有对人性这种自欺本质加以忏悔,我们越是标榜自己的赤诚、标榜自己的真心、标榜自己的纯洁,就越会落入伪善。真正的真诚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无愧怍于天地之间,而是反思或者忏悔自己本质上的不真诚。反思不真诚才是真诚。但这个反思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条道路。这条忏悔之路通往某种理想或者更高的东西,我们叫绝对真理也好,叫绝对精神也好,叫绝对自由也好,叫绝对理想也好,或者干脆叫上帝,都说明它虽然是无穷无尽的,但它是有方向的,它是不断深入的。而且不是深入了以后就不再上来了,看了自己的内心一眼,又马上跳出来,不敢看了;而是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自己的内心。这种忏悔实际上是给人提供信心的。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深化了一个层次,既然我能够做到这种自我深化,我就可以指望自己不断继续下去。人在陷入无可奈何的自欺状态之中时,就可以通过这样一条忏悔之路走向真诚,使自己得到拯救。所以说人做到真诚并不是毫无希望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虽然天真幼稚的希望破灭了,人生还不至于绝望。而忏悔所体现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后退、不断审视自身和深入自身的结构,最终导致了一种对彼岸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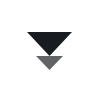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信仰,由于没有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做支撑,常常沦为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服从,甚至一种功利性、实用性的机会主义的考虑。而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就体现在对自我的反思以及自我忏悔精神中,这是中国人从来所不习惯的。中国人只要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权威供他崇拜就够了,他不需要有一个彼岸的信仰,他的心灵不需要有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对话者。而西方人需要一个上帝是有来由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人逐渐意识到自我的独立性、人格的独立性以及每个人灵魂的平等这样一些问题,他只能通过自己后退一步来认识自己,而不能通过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地位来把握自己。在这样一种不断后退、不断从旁审视自己的过程中,他需要有一个终点,因为不断后退对于想要给自我一个确定性的人来说是一种煎熬,通常的人是很难忍受的。于是西方人就设立了一个上帝作为最终的知人心者,作为对自己失去归宿的心灵的一种安慰。所以西方人的上帝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归宿,而不是物质上的祈求对象。

西方人需要一种这样的归宿,但是中国人不需要,中国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世俗生活中得到解决,哪怕暂时不能解决,顶多就是推到未来的世俗生活、推到历史中去解决。未来的世俗生活就是历史,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信仰就到这里为止,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日常的信念,就像相信死后太阳还会升起一样。“汗青”也是世俗的,“天道”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没有超越、没有彼岸的东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都是此岸的。所以,从超越性的角度来看,这不能算是真正的信仰,它只是一种信念(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有一种信念,但它还不是信仰,信仰应该是超日常生活的。这也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超越性。我们前面讲到自我意识的两大特点:一个是反思性,一个是超越性。前面讲的超越性就是人与人之间凭借自我意识超越各自的肉体,彼此能够在精神上相通,那是横向的。而这里的超越性是纵向的,就是我可以超越当下,把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打通,用我的将来刷新我的今天和我的过去,用今天的我来审视过去的我,又用未来的我指导今天的我,而这未来的我就通向了永恒的上帝。这是一种纵向的超越性,这种纵向的超越性是让我们产生真正彼岸信仰的一个必要前提。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信上帝,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真正的信仰,相信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呢?只要我们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立体性的自我意识结构,这应当不是什么难事。上帝就是纯粹精神性的东西,西方人用上帝这样一个权威来代表纯粹精神性的东西;我们不用这个权威,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对人类纯粹精神生活的信仰,以便为自己的自我意识建立起精神的殿堂。
我前面讲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起源,“知、意、情”,或者“真、善、美”,都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它们构成有限人类的无限的精神追求目标,成为人类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之上的理想。我们即使不信上帝,也可以信仰“真、善、美”,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当然这是人所达不到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人才可以借此安身立命,可以不断追求而永无终结。无神论者也可以有一种宗教情怀,所谓religiousness,也译作“宗教性”,我更倾向于把它翻译为“宗教情怀”,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提出来的。他其实也不相信上帝,但是他认为,我们可以不相信上帝,但可以有一种宗教情怀,也就是像对上帝一样的一种情怀、一种追求,即对纯粹精神的一种追求,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物欲所限制,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人都是要有理想、有追求的,这种追求是超越一切、高高在上的一种精神的目标,虽然你永远达不到,但是它时刻鼓舞着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自由的人,不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所束缚。
最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自我具有一种摆脱不了的自欺结构,这是必须承认的,这也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即使你以各种办法去抹杀它、遮蔽它、无视它,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摆脱它,相反你恰好坐实了它。你抹杀它,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你努力想摆脱这种自欺,但要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你只有走出一条路来,离它越来越远。这就只有一种办法——正视它,直面这种自欺的结构,并且反思它,使你的忏悔成为你生活的常态。当然,我们中国人很难忍受像基督徒那样每天晚上都要对上帝祈祷,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双手合十感谢上帝给我们带来面包,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堂里面默想祷告。一般中国人是做不到的,中国人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不愿意受精神上的束缚。但是,你心里面要有这个维度:你不会那样做,但有些人会那样做,而且对他们来说那是一门功课,完全放任自己了,那就容易堕落了。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结构才能够建立起人格独立的模式,才能具有担当精神和进取精神。担当精神也就是敢做敢当,有忏悔精神你才敢做敢当,习惯于忏悔、习惯于拷问自己的灵魂,你才有担当精神。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是建立独立人格的基本要素,也是伪善的克星。
这里讲的是关于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比较难的,自我意识是涉及每一个人生存的东西,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做过深层次的反思,那就会感到很难很复杂。但实际上这是必需的,今天的大学生应该有这样一种反思能力,应该经过这样一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