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读《阿Q正传》(节选)
毕飞宇
小脚和小腿
我首先来谈谈《阿Q正传》的序。这个序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在它的隐喻性。要给一个人作传,三大件必须要满足,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鲁迅想给阿Q写传,阿Q同样必须满足这三大件。然而,经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考证,情况很不妙,阿Q这个人物出现了三个反向的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
大家想过没有,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写成一个三无产品呢?
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落实到小说上,那就是贪大,鲁迅是一个贪大的作家。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鲁迅的眼里,小说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在鲁迅的时代,小说和小说家都没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鲁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他写小说其实就是“下海”。是什么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启蒙。大先生是一个渴望着面对整个民族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呆在象牙塔里,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一,他“白话”了;二,他“做起小说”来了。启蒙才是鲁迅的真使命。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我们都知道,1921年的中国充满了焦虑。从1840年算起,这焦虑已经持续了80年了。在80年的时段里,关于中国,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侮辱。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御侮呢?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附带说一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进去,还是关于侮辱的,———昨天我还是大爷的,一觉醒来我怎么就成了孙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时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反差里头。关于“爷”和“孙子”,我先放在这里,我在后面说。

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换言之,中国该做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不同的侧重:师夷,体用,洋务,实业,科学,废科举,共和,解放生产力,头绪很多。在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了不起的,他们睿智的双眼盯住了一样东西———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他们发现,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一旦变成“解放脚”,女性立马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换言之,中国的生产力就可以提升一倍,中国的GDP也许就可以提升一倍。———对中国的命运来说,如何御侮,女性的双脚才是真正的“内需”。
可是,1924年,鲁迅却拉出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她叫祥林嫂。关于祥林嫂,鲁迅在《祝福》里是这么说的:她“整天的做”,“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在这两句话的前面鲁迅还有一句话,叫“手脚都壮大”。祥林嫂“手脚都壮大”这句话很醒目,很有意味。请注意,祥林嫂不是小脚,是大脚。可是,大脚的祥林嫂只有一个结局,冻死骨。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你确认了自己是一个“贱货”,每天都忙着捐门槛,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就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所以,“小脚”的问题固然重要,“小腿”的问题却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比康梁前行了一大步。

在私底下,我一直把鲁迅的哲学命名为“小腿的哲学”,———你到底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鲁迅的一生其实就是为“小腿”的站立而努力的一生。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看待御侮的呢?这就有点得罪人了,鲁迅认为,只要“小腿”是跪着的,“洋奴”和“家奴”也没有区别。这句话狠哪,狠到骨子里去了,他道出了御侮的本质,———先做“人”,先不做奴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谈御侮。
所以,关于御侮,鲁迅的态度十分明确,他着眼的不是方法论,———不是师夷、体用和洋务,而是世界观:我们要不要做奴才。鲁迅为什么如此在意世界观呢?因为鲁迅有“故乡”,因为鲁迅太熟悉“故乡”的闰土和闰土们了。闰土和闰土们在精神上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望做“奴才”,在奴性文化的驱动下,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奴性的自觉”,这个发现让鲁迅产生了无限的大苍凉。请注意,鲁迅发表《故乡》是1921年的1月,发表《阿Q正传》是1921年的12月,是同一年的一头一尾。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我很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惯性,这个惯性也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逻辑性。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之间有逻辑。这个特有的逻辑就是作家的价值体系,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

总体上说,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对“奴性的自觉”还保留那么一点情面,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含蓄,太优雅,他意犹未尽,他想撕破脸皮、酣畅淋漓地来个“大的”。我估计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卯足了劲,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的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众多,最关键的是,气足,手稳,那是一个小说家的巅峰状态。面对“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鲁迅鼓足了决绝的勇气,迸发了全部的才华,他骁勇无比。不做奴才的鲁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对大,以“彪悍”对麻木,内心无比地恢宏。对奴才,他“一个也不宽恕”。作为读者,我想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
我敢武断地说,鲁迅压根就没想给“阿Q”好好地取一个“像样的”中文姓名,为此,这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为了“三大件”,不惜写了那么长的一段序。就小说的结构而言,这个序的长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很必要。只有有了这个序,阿Q的“三无”身份才能够合理。———鲁迅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姓”、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名”、根本不想让阿Q有“籍贯”,由是,鲁迅保证了阿Q的抽象性。阿Q是“大多数”,甚至是“全部”,他是无所不在的。鲁迅需要这个。
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让阿Q叫做“赵国富”或者“赵国强”,这有趣么?很无趣,很无聊。虽说“赵国强”更具象。
抽象不只是哲学的事情,也是小说的事情。抽象即涵盖,抽象性即整体性。
伦理和肿瘤
鲁迅一共动用了两个章节来描述阿Q的“行状”,也就是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
阿Q的“行状”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受尽了侮辱。可是,无论遭到怎样的侮辱,最后的胜利者却永远都是阿Q。所以,阿Q也是御侮的,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所以,阿Q的“行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等式:行状=侮辱+御侮。
我现在就想对具体的“行状”做一点分析,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鲁迅总共描绘了阿Q的六次受辱,也就是六次胜利。现在我有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把它们分成两章呢?仅仅是为了篇幅上的平衡么?写成一章可以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这不是一个篇幅上的平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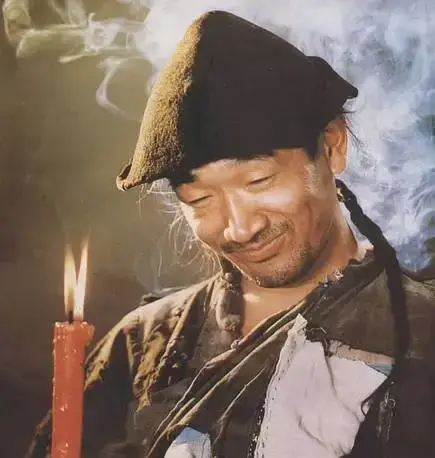
我们回过头来,先来看“优胜记略”,鲁迅写了一个人,也就是“闲人”,这些“闲人”在欺负阿Q。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闲人”看作黑恶势力。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人物具体起来了,分别是王胡、假洋鬼子和小尼姑。我们分别看一看阿Q和他们的关系。
阿Q和王胡———
王胡的头上也有癞疮疤,这就和阿Q平起平坐了。但是,很不幸,他的脸上还有一圈络腮胡子。在阿Q看来,王胡比自己还不如。正因为王胡不如自己,阿Q开口便骂,这一骂,阿Q和王胡打了起来,最终却没能打赢。———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先欺负了比自己弱的人。
阿Q和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什么人呢?鲁迅说了,“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这句话很刁钻,它一下子就道明了假洋鬼子的两重身份:一,富二代;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假洋鬼子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作为穷人,阿Q仇视富二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时还仇视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这就匪夷所思了。阿Q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没有交代,反过来,鲁迅却交代了这种仇视的强度,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可以把这种“不交代”或“强度”看作知识分子的原罪,阿Q必须仇视他们。阿Q的确被假洋鬼子打了,但是,注意,他侮辱假洋鬼子在先。———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天然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对立面。
阿Q和小尼姑———
小尼姑当然也有双重身份:1,女性;2,异己。对待女性,对待异己分子,阿Q就更没有什么可客气的了。请大家留意一下,只有在欺负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时候阿Q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为什么?他有合伙人,那些曾经欺负过阿Q的“闲人”。那些“闲人”统统站在了阿Q这一边。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阿Q对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欺压和亵渎。

现在,问题清晰了。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的六大“行状”分开来写呢?是因为阿Q的六大“行状”、六次受辱、六次胜利所呈现出来的性质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1,他被侮辱;2,他侮辱别人。这两件事不在同一个叙事平面上,绝对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头。相对于“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是小说内部的一个反转,它更是小说的递进,也是小说的深入。能深入的小说才可以抵达深刻。深刻不是你读了几本康德和海德格尔,更不是你学会了写几句诘屈聱牙的长句子。深刻是深入的状态,是深入的结果。这里头全是小说家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当然也还有勇气。
附带说一句,好小说从来不“溜冰”,也就是说,好小说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平面上作“花样表演”。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篇小说,它内部的时空非常有限,它极为宝贵,是小说的命脉。绝不能把小说的叙事时空浪费在信息的重复上。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续优胜记略”的那次反转,“优胜记略”充其量也就是一组油腔滑调的“小故事”。相反,由于有了这次反转,阿Q这个人一下子就立体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迎光”的那一面,我们还能看到他“背光”的那一面。最主要的是,我们从阿Q的两面看到了鲁迅的深刻。
话又要说回来,小说家的深刻毕竟不是哲学家的深刻,小说家的深刻更多地体现在小说的技术上,就《阿Q正传》而言,人物的出场就是技术,这是很讲究的,写作的人一点都不能乱。你把“续优胜记略”里的人物安排到“优胜记略”里去,小说马上就出问题,连接不上的。即使在“续优胜记略”这样一个小空间里,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三个人物出场的次序也不能颠倒,一颠倒小说立即就会缺氧,小说即刻就会死。
那么,鲁迅深刻在哪里呢?第一,鲁迅所描绘的阿Q在底层,如何去表现底层?一般的作家是这样做的———声情并茂地、“深刻”地揭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到此为止。大部分小说都是这样。
鲁迅却直面人性,他面对了一个比底层更为重要的伦理问题,或者说,精神的走向问题: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了,他有可能在痛苦中涅槃,走向善良、互助和公正;也有可能正相反,变得更自私、更恶毒、更邪恶,阿Q就是这样。这个伦理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牵扯到受辱之后精神上的终点,而这个精神上的终点正是御侮的逻辑新起点。
第二,鲁迅告诉我们,阿Q有他与生俱来的天敌:1,比自己弱的人;2,比自己有知识的人;3,妇女或异己分子。请注意这三种人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的精心选择,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认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让读者恐惧。这三种人何以成为阿Q的天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的问题。

我想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整体上是幼稚的,这个幼稚体现在一个文学逻辑上:只要你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拥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真理性。这是隐藏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巨大肿瘤,非常遗憾,这个巨大的肿瘤到了中国的当代文学依然都没有被切除。
很幸运,我们有鲁迅。鲁迅的存在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