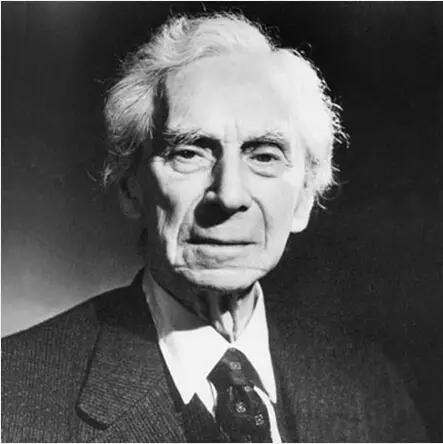
今天,同历史上许多其他时代一样,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贤士,他们看穿了以前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场面,认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确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福引以为荣,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惟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不幸的自豪、夸耀,使得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他们以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些。无疑,这些受难者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某些补偿,但是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活的丧失。
我个人认为,人不快活是没有什么理性、优越可言的。贤士只要情势允许,是会感到快乐的,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过了某一极限而变得痛苦时,他就会转而考虑别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节中试图证明的。我想奉劝读者诸君,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智决不会禁止人们去获得幸福。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那些颇为真诚地把自己的悲哀归于对宇宙的观点的人是本末倒置了。
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出于某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原因,而这种不幸福便导致他们去思考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不甚令人愉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我准备讨论的观点是20世纪中期美国作家、编辑、教师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提出来的,对我们的祖父一辈而言,则是拜伦的观点,对所有时代的人说来则是《传道书》作者提出的观点。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在宇宙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因为成为人而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那样活着”。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著名诗人拜伦这样写道:
当早日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腐朽中渐渐衰落,这世界给予的快乐没有一个能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 。
《传道书》的作者这样说道:
我羡慕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 。但是,那未出生,未曾看见过这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事的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快活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在纽约城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古称达达尼尔海峡,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传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凡此等等”,他建造水池,他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依然没有丧失。然而他把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做一片空虚。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但是,我发现这也是捕风 ,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博,忧虑越重,连他的智慧似乎都使他恼怒,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语:“来吧!试一试享乐!来享享福!” 可是,这也是空虚 。但智慧仍与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的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 因此,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使我烦恼 ,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捕风 。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读很久以前写下的那些东西了,因为要是他们读了,便会得出结论,不管关于水池有人曾发过什么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是空虚。如果我们能表明,《传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贤士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以后出现的表达同样情绪的词句而自扰了。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时,我们必须分清楚情绪及其理智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差别。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是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我自己曾经历过这样的情绪,即感到一切都是空虚,我对这种情绪的摆脱并不是通过任何哲学的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促成的。
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高兴,但是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会觉得孩子的身体复原是件当然要去关心的事,根本不必去考虑人生有否最终价值这种问题。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他便会觉得下一顿饭就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是由于自然需要的过分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斗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不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可满足他的一切奇想怪念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乏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他便会这样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辨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既然具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那么人生必是可怜不幸的。他忘记了缺乏我们所需要的某些东西,正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情绪,我们就谈这些。不过,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
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
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
前人、往事无人追念
太阳底下,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
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些见解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就很可能是这样——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永远在运动之中,然而没有什么会永远驻留不去,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死去,他的后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呆在海洋里。如此周而复始,在无尽期、无目的的循环中,人类和世间万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远的成就。如果河流有智慧就会呆在原地止步。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其实此书并非所罗门所写,这样做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种下果树,让他的儿子来坐享其成了。
但是,如果在另一种情绪下,这一切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天底下没有新事物出现?那怎么解释摩天大厦、航天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讲话,那对处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不啻是一个安慰?要是他有一个新闻剪报机构向他报告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争论的圣哲们的困窘狼狈相的,他还会说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吗?
当然这些事物可能不会完全治愈他的悲观主义,但是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天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没有新事物是同样令人讨厌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成了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但是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处的。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就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欣赏这有冒险性的循环旅行。
至于说到把财物遗给后嗣的痛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灾难。认为一切事物都带有悲观的原因也不尽然。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那么,如所罗门认为的,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的。
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又在于其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无所谓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同这样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像的痛苦的不幸后,最终以圆满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要是我长生不死,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必定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保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烤着双手
火焰低落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同对死亡的义愤态度一样是很符合理性的。因此,情绪如要由理智决定的话,那么快乐和绝望都是有相当理由的。
《传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先生之所以悲伤,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的、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道:“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冥冥世界鬼魂困扰作祟,尚未认识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犹如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他们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何方。”
这一情况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适用的,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摆脱婴儿期的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即科学未实现它的诺言。
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不过他似乎这么认为,六十年前如达尔文、赫胥黎一辈人所期望于科学的,却至今未贡献出来。
我认为这完全是偏见,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人认为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现在的世界上确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而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第一次大战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定感,知识阶级遭受很大苦难。这样一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比较其理论对世界本质的影响来,远远要大得多。很少有几个时代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了,尽管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惜的信仰在那时几乎为所有的人所坚信,除了皇帝和少数几个意大利大贵族外。
因此13世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培根说:“我们这一时代比起任何一个时代来,更多的罪恶统治着世界,而罪恶是与智慧绝不相容的。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考虑一下吧:我们到处发现腐败堕落,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怎样追求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我们来想想宗教的戒规:我所说的一切,决无反顾。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修道士的)新戒规从其最初的尊严里已大大受到腐蚀。整个牧师阶层追求的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首,比方说在巴黎和牛津,他们之间的争斗、吵闹和其他罪恶等等的丑闻便会传遍世俗社会……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
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异教圣贤时,他写道:“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欢欣明畅,富庶荣耀。这一切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塞内加,古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图里,20世纪初穆斯林哲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1世纪末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乌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读到。正因如此,他们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知识”。
培根说出了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看法,他们当中无一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的。我丝毫不认为这种悲观论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奇先生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谈爱的问题。事情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我们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看穿了它。
“对怀疑心理更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来说,爱情起着某些他们已经丧失了的、惟上帝具有的功能。面对爱情,许多人,甚至那些最为顽固的人,一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虔诚意识,这种意识不为其他一切所有,而且他们感到,甚至在他们生命本质的深处,应奉献上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做出一切牺牲;另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样,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还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已经更习惯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但是,我们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而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此时,我们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是这么大。
我记得两位我在年轻时就很熟悉的老妇人,她们都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门徒。前者哀叹道,关于爱情的诗歌实在太多了,她认为爱情是个没有意义的主题。后者则这么说:“没人可以说什么来反对我的,我一直说,破第七诫‘不可奸淫’总不如破第六诫‘不可杀人’那么坏,因为不管怎样,这总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行。”这两种观点同克鲁奇先生声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观点是大不一样的。他的意见显然来自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作家同他们所处的环境绝不是很合拍的。
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布郎宁了。当然,我不能不承认,在他的爱情观里有些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的卑微的芸芸众生
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这即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惟一态度便是奋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郎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按你对自己的评价来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一个如布郎宁夫妻那样的互相爱慕的社会,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无论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她总是给予夸奖,这总是令人高兴的。在布郎宁张口痛责暮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对布郎宁的夫人所作的长诗《奥罗拉·利》表示称赞时,无疑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认为双方的批评官能的完全丧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心理,以及希望在面对批评时寻找庇护的欲望是紧密相关的。许多老单身汉学会从自家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满足。
我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太久,难以成为符合克鲁奇先生提出的标准的现代人。我决没有失去对爱情的信仰,但是我所信仰的那种爱并不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羡慕。这种爱是有冒险性的,睁亮双眼的,在它给予善的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把邪恶遗忘,也不去故作神圣贞洁。把这些特征归属于那种为人称羡的爱,这是性禁忌的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不得不把那些夸张形容词贴在他所认可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饿比现在厉害得多,这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样,无疑更使人们去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混乱的时期,许多人抛弃旧的道德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各种苦恼,由于在无意识中,他们一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麻烦、苦恼冒出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我想发生以上情况的人是不会很多的,但是他们属于我们时代最无顾忌的那群人。我想,我们要是把今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在爱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
使某些人走上愤世嫉俗道路的原因是,旧的理想对无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缺乏,而今天的人正是据此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的。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而在于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现代的世界观,有决心从各个阴暗角落里铲除早为人所摒弃的迷信思想。
要简略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爱情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啊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痛苦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
这几句诗的佚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什么答案,或是在寻求解开宇宙的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欣赏。爱情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而且爱情的丧失是痛苦的源泉。其次,爱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促进了一切最大的快乐,诸如对音乐、高山日出以及皓月当空的大海的欣赏。一个从未和自己所爱的女子一起欣赏过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再者,爱能够打破自我的坚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上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的情绪参与。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处哲学,有的极为崇高,有的则较卑下。禁欲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换言之,不需要人的帮助,便可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还有人把权力当做生活的目标;另有一些人把个人享乐看做生活的目的。所有这些独处哲学都认为,每个人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社会的努力。
我认为,这些观点不仅在道德理论上,而且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错误的。人是有赖于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那种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人的合作情绪的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任何经历过种种爱情体验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认为不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便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更要强烈些,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
我不认为最高形式的爱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确信,在爱的最高形式中所体现的价值一定还未被人知晓,而其自身的价值还未被怀疑论触及,尽管那些怀疑论者并无此能力,但他们却把这种无能归于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是永恒的火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怠,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感觉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看法。他认为,挪威戏剧家、诗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要逊色得多,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写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他对人类热情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生的广阔丰富的想像力——这一切易卜生是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神祗、人类和自然都不知怎么的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条引导我们去寻求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生的平庸被某种程序运转加到了我们身上,正是这同一程序运转导致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的想像力得以被证实”。
毫无疑问,描写王公贵族及其哀愁的旧式悲剧和我们的时代是不相适应的,在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无名之辈的悲哀时,其效果是不一样的。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看做地球上的伟人,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而所有其他人则不得不辛苦劳动,以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
莎士比亚在《朱利阿斯·凯撒》第二章中写道: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在莎士比亚时代,这种观点即便不完全为人所信,至少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深为莎士比亚本人所接受的看法。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辛纳的死是喜剧的,而罗马的将军、皇帝凯撒、刺死独裁者凯撒密谋领袖布鲁图和另一个刺死凯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的。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更深入我们的信念之中。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主要是与社会,而不是与人密切相关的。
我试以20世纪初德国戏剧家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同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一样好,但是我坚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又是实际的。它关注的是英雄行为,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心灵”。像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见,因为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抛弃,而又不能用平庸的事物去替代。要写悲剧,人必须有悲剧的情感。要具有悲剧的情感,一个人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去体验。
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几次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荒凉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荒凉世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面对新的刺激来感知旧的情绪。这种刺激是存在的,但并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重要的接触联系,而人的感情要有这样一种严肃性和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的话,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对所有那些有才能的年轻人,对那些迷惘惶惑、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我的劝告是:“放弃写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别去写什么。走到大千世界中去吧,去做一个海盗,当婆罗洲的国王,到苏维埃俄罗斯去做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让基本的身体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不是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诊断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方法。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些人就会发现,尽管他怎样遏制自己,却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