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清逸,来自长沟流月去无声
鲁迅研究在中国学术体制内早已是一门显学,和“红学”(《红楼梦》研究)、“龙学”(《文心雕龙》研究)一样,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三四代人持续不断的开垦挖掘之后,已经形成丰厚的学术累积和较稳固的理解范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者若想再从文本中读出一点新意来,其实并不容易,更不要说在理解范式上有所突破了。虽然论文数量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但真有深刻洞见、真能带来思想启发、真能触动现实关切的,又有多少呢?
在我心目中,许寿裳(1883-1948)、瞿秋白(1899-1935)等先生是第一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研究中的杰出者。自留学日本起,许寿裳就与鲁迅成为一生的挚友,曾利用自己与蔡元培的关系给予鲁迅诸多的帮助,鲁迅去世后也是鲁迅著作搜集、整理、出版最积极的推动者。在所有的鲁迅回忆文字中,他与萧红的记录最让人感到真切、生动。瞿秋白则被鲁迅视为知己。他与鲁迅都出身于没落士族家族,都是“从旧营垒而来却能反戈一击”的斗士,身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身上又有脱不开去的孤愤与悲情,彼此相知,心心相印。
在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中,我认为最杰出者是李长之(1910-1978)、王瑶(1914-1989)等先生。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大家之一,他的研究是怀着现实关切和浓厚深情的,笔锋长带着浓烈的感情,不像现在那些貌似客观实则贫血的研究文字。他是真正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中去,带着所谓“同情的理解”去批评的。
王瑶先生说鲁迅的思想和文字给青年时代的他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启迪(尤其是那篇名为《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的演讲),他将先生的批评文字视为一种思考方法与学术取径上的启迪,甚至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以“药、酒、女、佛”为切入点,进入士人的深层精神世界,《中古文学史论》就是他早期尝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后人在此基础上更演变成为结合物质文化史对士人“心态史”的研究。他对鲁迅的借鉴是思想方法、研究取经上的移置和扩展,而不是简单地“炒冷饭”:无论就文字论文字,还是就生平论生平。
在第三代(“改开初期”)鲁迅研究者中,我最欣赏的是钱理群(1939- )先生,他曾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与教益。钱理群先生让我第一次深切理解到鲁迅思想中的“阴暗面”的意义——他的绝望感与虚无感,以及他一生毫无妥协地对虚无的反抗,或许都概括在《野草》中的这一句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他的抗争不是为了希望,而是出于绝望。我甚至认为,不理解鲁迅的“阴暗面”,只知道一个以“伟光正”形象出现的鲁迅,那是会极大地误解先生的,也无法真正感受到先生思想的深刻与伟大。
在第四代(千禧年之后)鲁迅研究者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孙郁(1957- )、郜元宝(1966- )和陈丹青(1953- )三位先生。
孙郁(1957- )先生让我看见鲁迅文章背后的“暗功夫”。鲁迅当然是文章大家,而且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文章,涉笔成趣的境界:虽然无意于“被抬进文苑”,但一出手就是《呐喊》《彷徨》,成就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巅峰;从记忆中随便抄出几篇文字,汇成一集《朝花夕拾》,就成为回忆散文的经典;将深晦隐微的心曲寄托于种种象征,就刻画出一个游荡在冰火两重天的孤魂,成就一阕极富哲理意味的散文诗《野草》。这种才华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字功夫,还有更深的底蕴在。
其实,鲁迅的文艺活动远远超出文学写作,他还研究过中国小说史,编过唐宋传奇,校勘过古籍(嵇康集),收集过汉画像、墓志铭,编印过木刻版画,此外还从日文和德文本翻译过数以百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甚至在民国早期作为教育部的官员,还制定过中国美术教育的大纲,设计过北大的校徽。他的学养是真正横跨中西的,故能有超出时代的眼光。这些都是孙郁说的“暗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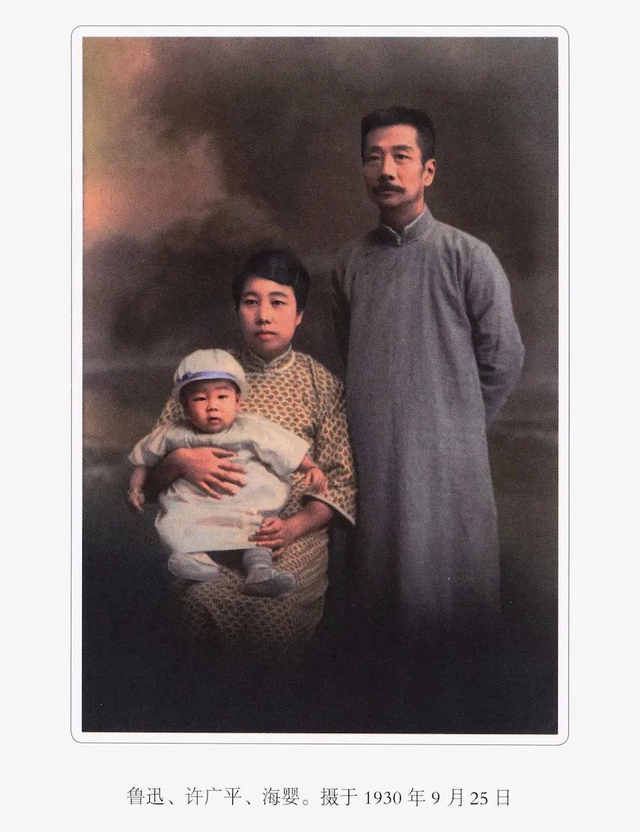
最早知道郜元宝(1966- )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鲁迅六讲》,当时读完就有一种兴奋感。泛泛而谈的一些观念都略过不谈,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对收录在《坟》中的鲁迅早期几篇论文的文本细读,尤其是《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这些早期论文在鲁迅思想的萌芽中十分重要,许多核心思想可谓贯穿鲁迅的一生,反映出其性格的底色,虽然后来也有发展,在表现形式上甚至显得不同,但在思想内核上仍可以看见前后贯通的一致性,如鲁迅对于文艺审美本质的恪守,从不会让文艺沦为政治弄潮儿摇旗呐喊、党同伐异的工具,也不会变成哈巴狗摇尾乞怜、粉饰太平的手段。
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涵养吾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由此审美的感动转为对抽象概念的超越,“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在我理解中,这或许就是“诗与道合”,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无邪”——即成为一个自由意义上的道德的人,换言之,也就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自由的人,这是一体的两面。
另有一位陈丹青(1953- )先生,文学批评虽不是他的本行,却写了不少关于鲁迅(他尊称为“大先生”)的文字,且在青年学子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常能以其直言不讳、大胆直截和去除粉饰的爽利,给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很大的快慰。他的文字语感相当不错,在画家中可谓奇才。当然,若论笔锋的雄健深厚,尚远逊于先生,不过从文风的泼辣生猛、睿智幽默来看,倒颇有几分神似先生,不妨看作是出于由衷的崇敬心理对鲁迅精神一种遗貌取神的模仿与继承。
文章开头说到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体制内的一门“显学”,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但说实话,真正好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这成堆的文献中,我觉得绝大部分都不值得去读,不是路子错了,就是太过琐碎。首先研究者的心态就不对,往往先以崇拜者的心态选好了仰视的姿势,于是这个好,那个好,眼中无所不好,空泛地发一番赞叹,其实都很肤浅,无法与先生平视对话并大胆直面现实。
我认为,鲁迅研究其实还大有可为。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而这些问题又是绕不开去的,因为它们与时俱进地变换着面貌,不断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为我们时代的问题。因此,鲁迅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不是鲁迅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鲁迅,离不开鲁迅。为了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迫切渴望与先生对话,从他留下的文字和思想中去寻求启示。
以上例举的几位研究者在我看来都有一个共性,即能从鲁迅文本的表层进入到文本作者的精神深层,汲取鲁迅的思想方法、鲁迅的社会批判视角,以回应各自时代最为紧迫的关切。可以说,只有当我们这样去读鲁迅时,才最接近鲁迅。千万不要忘记先生临终时的遗言: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