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六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男孩,开始猛烈地阅读时,托马斯•曼的《魔山》广受欢迎,被认为是一部几乎足以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匹敌的现代小说。现在,我刚十五年来第一次重读了《魔山》(1924),又一次高兴地发现它的乐趣和力量未减。它绝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一种一如既往地新鲜而尖锐的阅读经验,尽管这经验被时间微妙地改变。
很不幸地,曼在过去的三分之一世纪里有点黯然失色了,原因是他绝不是什么反文化的小说家。《魔山》不可以夹在《在路上》与某部大块头网络叛客小说之间来读。它代表着现已有点岌岌可危的高级文化,因为这本书要求读者有相当水平的教育和反省能力。小说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工程师,他来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肺痨疗养院看望表哥,原只打算作短暂探视。卡斯托尔普在本人也被诊断患上肺痨之后,便在魔山逗留了七年,既为了治病,也为了继续接受文化教育和发展。
曼最初把汉斯•卡斯托尔普形容为一个“十分普通”的年轻人,但这是一种反讽。卡斯托尔普绝非“人人”,在本质上也不是一个精神求索者,至少首先不是。但他一点也不普通。他无穷地可教,无比地容易受到深刻的谈话的影响,又非常好学。他在魔山接受一次非凡的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跟两个立场相反的老师谈话和聆听他们谈话。一个是意大利人塞塔姆布里尼,他是开明派人文主义者,也是诗人和自由思想家卡尔杜齐的信徒,他先登场,并显示他的权威;接着,到了小说下半部时,纳夫塔登场。纳夫塔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激进的反革命,一个反对民主、信奉虚无主义一马克思主义的耶稣会会士,总是回望中世纪宗教综合体,哀叹欧洲背弃信仰。塞塔姆布里尼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纳夫塔则是反宗教改革的辩护士。两人之间的辩论总是残酷无情,并在纳夫塔大声喊出一个预言时抵达最初的一个重点,这个预言,果真在《魔山》出版十年后在德国应验:
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只有塞塔姆布里尼使我们愈来愈喜欢他,尽管托马斯•曼的笔触蕴含无穷的反讽。反讽既是托马斯•曼最令人望而生畏的资源,但可能也是他终极的弱点(一如他自己知道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对他的批评者提出的抗议,至今依然有用:
在文学中,反讽有很多意义,一个时代的反讽绝少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反讽。我对想象性写作的经验是,它永远包含一定程度的反讽,这也正是奥斯卡•王尔德一个警告所指的。王尔德警告说,所有坏诗歌都是真诚的。但反讽不是文学语言本身的条件,意义也并非永远是一个到处游荡的流放者。宽泛地讲,反讽的意思是说此指彼,有时甚至是正话反说。托马斯•曼的反讽常常是一种微妙的戏仿,但是对《魔山》敞开怀抱的读者,将发现它是一部有着温柔而高度严肃性的长篇小说,以及最终是一部有着伟大激情的作品,既才智卓绝,又感人肺腑。
如今,托马斯•曼这个奇妙的故事提供的主要不是反讽也不是戏仿,而是一个可爱的视域,这是一个现已消失的现实的视域,一个现已永远逝去的欧洲高级文化也即歌德和弗洛伊德的文化的视域。一位二〇〇〇年的读者,必须把《魔山》当做一部历史小说来体验,当做一种已失去的人文主义的纪念碑来体验。这部出版于一九二四年的小说,描绘那个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分崩离析的欧洲,这场大战也正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从魔山下来所奔赴的大灾难。大多数人文主义文化在这场大战中幸存下来,但是托马斯•曼对他这部小说出版短短十年后掌权的纳粹的恐怖有一种先知先觉的预见。虽然托马斯•曼原意是要对欧洲文化进行一次怀着爱意的戏仿,但是变易、时间和毁灭造成的反反讽,却使《魔山》在二〇〇〇年成了一部无比感伤地研究怀旧的小说。
在我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现在似乎是一个比我五十多年前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时更微妙也更讨人喜欢的人物。虽然托马斯•曼希望把卡斯托尔普视为一个求索者,但我觉得求索并不是这位小说主人公的任何重点。卡斯托尔普并不热切追求某个神圣目标或理想。他是一个最令人击赏地超然的人物,他会带着同等的满足聆听开明的塞塔姆布里尼、恐怖主义的纳夫塔,或怪诞地充满生机论色彩的明希尔•皮佩尔科恩。皮佩尔科恩很晚才与充满情欲的斯拉夫美人克拉芙吉亚•肖夏一同抵达魔山,卡斯托尔普对这位美人意乱情迷,但仅与她享受一夜的满足。汉斯•卡斯托尔普情欲上的超然,似乎很不寻常;他爱上克拉芙吉亚七个月,却只有一刻的高昂激情,接着便在逗留魔山的七年的剩余时间里消退。他也没有因为皮佩尔科恩而心生太多的嫉妒,后者是陪伴克拉芙吉亚重返魔山的。卡斯托尔普七岁起就成了孤儿,他爱上克拉芙吉亚之前,曾与其斯拉夫同学普里比斯拉夫•希佩有过一段极度依恋的青春期同性爱关系。他对克拉芙吉亚的爱恢复了他压抑的对希佩的激情,并且这种融合式痴情神秘地在他身上催生了肺痨的症状,促成他待在魔山,接受七年垂死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教育。
把恋爱视为一种如同肺痨般的疾病,是托马斯•曼具有说服力的想象,也毫无疑问反映了他本人勉强压抑的同性爱,而这方面的伟大纪念碑依然是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读者逗留在魔山是因为卡斯托尔普对克拉芙吉亚一见钟情。不管卡斯托尔普的疾病的临床现实是什么,读者都被小说的进展所吸引,因为在恋爱时改变计划、地点或心灵环境这种普通的经验,被精明地与读者自己被诱入魔山的世界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读者(不论性别)是不是非要对婀娜多姿而又谜一般的克拉芙吉亚怀有激情,但认同有着无穷尽的善意和性超然的卡斯托尔普,却是难以抗拒的,因为托马斯•曼的艺术是如此巧妙。我们并非总是像汉斯那样看见、感觉和思考,但是我们永远贴近他。除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中那个与我同名的波迪,现代小说中再没有一个比卡斯托尔普更使读者感同身受的人物。乔伊斯想保持超然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利奥波德•布卢姆反映了乔伊斯自己很多最吸引人的个性特质。爱反讽的戏仿者托马斯•曼,尽管作出了各种相反的努力,也仍不能使自己与卡斯托尔普分离。
由于当今批评时尚既否认作者的现实又否认文学人物的现实(如同所有时尚,这将会过去),因此我敦促读者不要拒绝因认同最喜爱的人物而来的乐趣,如同作者们无法抵挡这类乐趣。我的敦促是有限制的:塞万提斯不是堂吉诃德,托尔斯泰不是安娜•卡列尼娜(他爱她),菲利普•罗斯不是《夏洛克行动》中的“菲利普•罗斯”(不是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然而,一般来说,小说家们不管多么反讽,都会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重新找到自己;戏剧家也是如此。写《反讽的概念》的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指出,莎士比亚是反讽宗师,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就连这个反讽家中的反讽家,也在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中找到更真实和更陌生的自己,如同我在本书其他地方提及的。为什么读?因为你仅能够亲密地认识非常少的几个人,也许你根本就没有认识他们。在读了《魔山》之后,你彻底地认识汉斯•卡斯托尔普,而他是非常值得认识的。
重读《魔山》,我现在可以下结论说,托马斯•曼最大的反讽(也许不是有意的)是在开篇谈到汉斯•卡斯托尔普时说“读者将逐渐认识到他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尽管也很迷人的年轻人”。我已当了四十五年大学教师,我觉得必须说一说我对卡斯托尔普的看法:他是各大学一向宣称(在它们掉进现时的自我堕落之前)却从未找到的理想学生。卡斯托尔普对一切事物,一切可能的知识,都怀着强烈兴趣,但这是本身作为一种善的知识。对卡斯托尔普来说,知识绝不是权力,不管是凌驾别人或他本人的权力;它绝不是浮士德式的知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二〇〇〇年(和之后)的读者来说是,其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体现了一种现已过时但永远重要的理想:培养自我发展,直到个体能够实现她或他所有的潜能。在汉斯身上,渴望认识各种理念和各种人物,是与瞩目的精神耐力糅合在一起的;他永远不是一个仅仅怀疑的人,还是一个绝不被压倒或淹没的人(除了在他对多少有点暖昧的克拉芙吉亚的性激情达到高峰的时候)。塞塔姆布里尼的人文主义雄辩、纳夫塔的恐怖主义规劝,以及皮佩尔科恩的酒神式口吃,全都惊涛般压向卡斯托尔普,但永远不能把他卷走。
虽然托马斯•曼老是强调卡斯托尔普的平淡无奇,但这已变得有点像一个笑话,因为这个年轻的海军工程师天生喜好神秘经验以至超自然经验。他带着一本《海洋蒸汽船》抵达魔山,但他成了各种生命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理学著作的无穷尽的读者,并从这些科目继续走向无休止的“文化旅行”。如果我们还残留着(如果有也是源自托马斯•曼的反讽)任何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普通”的感觉的话,那么这残余也会在美妙的“雪”这一章融化。全书共七部分,而这一章就在第六部分结束前。汉斯独自进行一次滑雪探险时,被困在雪暴中,几乎丢命,接着获得一系列幻象。当幻象消失,他承认“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他断言“为了善与爱,人不应让死亡来统治他的思想”。
这之后,《魔山》进入自己的死亡之舞,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临近。纳夫塔挑战塞塔姆布里尼,要与他用手枪决斗;塞塔姆布里尼朝天鸣枪,愤怒的纳夫塔则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后,可怜的塞塔姆布里尼被粉碎了,他的人道主义教育学亦告终结。酒神式的皮佩尔科恩,这位人格和性宗教的维护者,在面对自己年老的无能时,也自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爱国地去为德国而战,而托马斯•曼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年轻人生还的机会不大,但并不是不可能。
读者几乎可以不理会托马斯•曼,而断定卡斯托尔普的生还机会较高,因为他有某种神奇或迷醉的东西,可以说是不朽的。虽然他看上去也许是普通人的圣化,却显然是通神的,根本就不需要他接受的那无穷尽的文化教导(尽管他是更好的接受者)。汉斯•卡斯托尔普领受神恩,如同托马斯•曼后来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约瑟也将领受神恩。托马斯•曼在向他的主人公告别时对我们说,卡斯托尔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爱情梦”。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此时,在二〇〇〇年和以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读者在寻求理解他时,将会问自己,我的爱情梦或我的情欲幻觉是什么,而这梦或幻觉如何影响我自己的发展或壮大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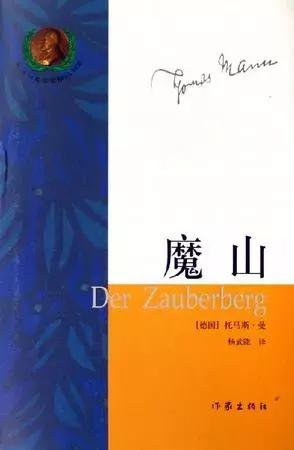
《魔山》选读
这里我们要叙述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因为读者将会了解到,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甚至是惹人喜爱的青年),而是为了故事本身;在我们看来,它是值得大大描写一番的。不过为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着想,我们可得记住这是他的故事,而并非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好久以前,也可以说已完全是历史的陈迹,因此叙述时无疑须用事隔多年的过去时态。
这对故事来说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故事必然在过去发生,我们可以说,它离现在愈远,故事的趣味性愈强,对写故事的人——他对过去的事往往像术士那样,能洋洋洒洒地信手拈来——也就愈有利。对这个故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它像当今许多主题一样,涉及的也是各色各样的人群,而对笔者并无丝毫牵连。它时间上比讲故事的年代早得多,它的年份不能用日子计算,它所贯穿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也无法用太阳的出没来衡量。一句话,故事离现在究竟有多远,同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恐怕是作者想玩弄一下故事情节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透的一种花招吧。
不过我们不能有意蒙蔽事实的真相。我们这个故事离现在这么远,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出现某种转折点之前——这种转折点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上留下很深的裂痕——发生的……它发生在——或者我们故意避而不用现在时态——它曾发生或已经发生在很久之前,发生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也就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里;在这次大战爆发时,有许多事正好从头开始,但一旦开始就几乎不会终止。不错,它是在大战之前发生的,尽管离大战的时间并不太远。不过,故事发生得愈“早”,它不是就愈鲜明地富于“过去”的特色,因而也更为完整,更有传奇性?此外,我们这个故事就本质来说,就处处体现出传奇的风味。
下面我们就要将它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叙述一番——哪个故事会因它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而显得过短或过长呢?我们不怕人们责难,说我们过于追求细节;我们倒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只有详尽的情节才能真正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