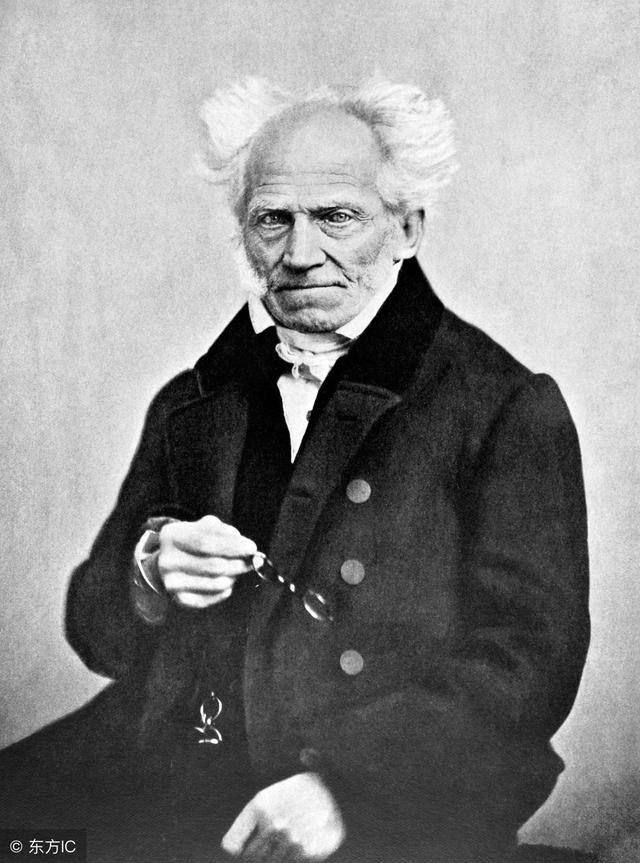
论生存的痛苦与虚无 叔本华 著 韦启昌 译 选自《叔本华思想随笔》
1
我们对痛苦的敏感几乎是无限的,但对享乐的感觉则相当有限。虽然每一个别的不幸似乎是例外的情形,但在总体上,不幸却是规律中的惯常情形。
2
溪水只要没有碰上阻碍物就不会卷起漩涡,同样,人性和动物性决定了我们不会真正察觉和注意到与我们的意欲相一致的一切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对事情有所注意的话,那这些事情肯定就是没有马上顺应我们的意欲,这些事情已经遇到[381]了某种阻碍。相比之下,一切阻碍、抵触或者拂逆我们意欲的事情,也就是所有让我们不快和痛苦的事情,马上和直接就被我们异常清楚地感觉到了。正如我们不会感受到整个健康的身体,而只会觉得窄鞋子夹住脚趾头的一小处地方,同样,我们不会考虑到所有进展顺利的事情,而只会留意鸡毛蒜皮的烦恼。我多次反复强调过的真理——舒适和幸福具有否定的本质,而痛苦则具肯定的特性——正是建立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之上。
与这一道理互相吻合的还有这一事实:我们一般都会发现快乐远远低于、而苦痛则远远超出我们对这些快乐或者苦痛的期待。
3
在遭遇每一不幸或承受每一痛苦时,最有效的安慰就是看一看比我们更加不幸的其他人——这人人都可以做到。但[382]如果所有人都承受着不幸和痛苦,那我们还会有其他方法吗?
历史向我们展示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但除了向我们讲述战争和暴乱以外,别无其他,因为天下太平的日子只是作为短暂的停顿、幕间的休息偶尔、零散地出现。同样,个人的生活也是一场持续不休的争斗——这可不是比喻与匮乏和无聊的抗争,而是实实在在地与他人拼争。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会找到拼争的对手,争斗始终是没完没了,到死为止仍然武器在握。
4
时间每时每刻催逼着我们,从不让我们从容喘息;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后面步步紧跟,就像挥舞着鞭子的狱卒——我们的生存因而平添了不少痛苦和烦恼。只有那些落入了无聊的魔掌的人才逃过了这一劫。
5
但是,正如没有了大气的压力,我们的身体就会爆炸,同样,人生没有了匮乏、艰难、挫折和厌倦,人们的大胆、傲慢就会上升;就算它不会达到爆炸的程度,也会驱使人们做出无法[385]无天的蠢事,甚至咆哮、发狂。无论何时,每个人都确实需要配备一定份额的操劳,或者担心,或者困苦,正如一艘船需要一定的压舱物才能走出一条笔直和稳定的航线一样。
匮乏、操劳、忧心固然是几乎所有人终其一生的命运,但如果人们所有的欲望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已经获得满足,那人们又将如何排遣自己的生活时间?假设人类移居到了童话中的极乐国——在那里一切都自动生长出来,鸽子也是烤熟了在空中飞来飞去,每个人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热恋中人,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她和拥有她——如果是这样,那么,一部分人就会无聊得生不如死,或者,他们会自行上吊了结;而另一部分人则寻衅打架,各自掐死、谋杀对方,从而制造出比大自然现在加在他们身上的还要多的痛苦。因此,对于这样的人类,再没有别的更合适的活动舞台和更合适的生存了。
6
所以,衡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幸福并不是以这个人曾经有过的欢乐和享受为尺度,而只能视乎这个人的一生缺少悲哀和痛苦的程度,因为这些才是肯定的东西。但这样的话,动物所遭受的命运看上去似乎就比人的命运更可忍受了。
人并不比动物享有更多真正的身体享受,除了人的更加发达的神经系统加强了对每一享乐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人对每一苦痛的感觉也相应提高了。在人的身上被刺激起来的情感比动物的情感不知强烈了多少倍!情绪的动荡也深沉得多和激烈得多!但所有这些最终也只是为了获得和动物同一样的结果:健康、饱暖等等。
人和动物之所以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情形。首先是因为人想到了不在眼前的和将来的事情。这样,经过思维的作用,所有一切都被增强了效果;也就是说,由于人有了思维,忧虑、恐惧和希望也就真正出现了。
满足人的需求本来只是比满足动物的需求稍为困难一点,但为了加强其欲望获得满足的快感,人却是有目的地增加自己[385]的需求。奢侈、排场、烟酒、鸦片、珍馐百味以及其他与这些相关之物就是由此而来。除此之外,同样是因为静思回想的缘故,只有人才独一无二地领略到因雄心、荣誉感和羞耻感所产生的快乐——或者痛苦。这一苦乐的源泉,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看法。
争取获得别人良好看法的雄心壮志尽管表现出千奇百怪的形式,但这却是人的几乎所有努力奋斗的目标——而这些努力已经超出纯粹为了身体苦、乐的目的。虽然人比动物多了真正的智力上的享受——这有着无数的级别,从简单的游戏、谈话一直到创造出最高的精神智力作品——但是,与这种智力享受相对应的痛苦却是无聊,而无聊却是不为动物所知的,起码对于处于自然状态之下的动物是这样。也只有最聪明的动物在被驯养的情况下才会受到一点点无聊的袭击。
但无聊之于人的确犹如鞭笞般难受。这种痛苦我们可以见之于那些总是关心填充自己的钱袋甚于自己脑袋的可怜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富裕的生活条件已经变成了一种惩罚,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落入无聊的魔掌。为了逃避无聊的打击,这些人就四处奔走、慌不择路,一会儿到这里旅行,一会儿又到那里度假。甫一抵达某一处地方,就紧张兮兮地打听可供“消遣的去处”,一如饥寒交迫的穷人忧心地询问“派发救济的地方”,因为,当然了,匮乏和无聊是人生的两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满足性欲方面,人自有其独一无二的执拗和挑剔,而这有时候会加强至强烈程度不一的激情之爱。
意欲是琴弦,对意欲的抑制或者阻碍则是琴弦的颤动,认知是琴的共鸣板,痛苦则为音声。
8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憧憬着即将展开的生活,就像在剧院里等候大幕拉开的小孩;他们高兴和迫切地期待着即将上演的好戏。我们对确切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其实是一种福气,因为对于知道真相的人来说,这些小孩有时候就像是无辜的少年犯:虽然他们并非被判了死刑,而是被判了要生活下去,但对于这一判决的含意,这些小孩并不明白。尽管如此,每个人都想活至高龄,亦即进入这样的状态:“从今以后,每况愈下,直到最糟糕的一天终于来临。”
9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视为在极乐的虚无安宁中加进[391]的一小段徒劳无益的骚动插曲。不管怎么样,甚至那些日子混得还相当可以的人随着生活时间越长,就越加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总的来说就是幻灭,不,应该是骗局才对;或者更清楚地说:生活有着某种扑朔迷离的特质。当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在分别了大半辈子、已成白头老翁之时再度聚首,两个老者相互间刺激起来的感觉就是“对整个一生完全彻底的幻灭和失望”,因为看到对方就勾起了自己对早年的回忆。在往昔旭日初升的青春年华,生活在他们的眼里美轮美奂;生活允诺我们如此之多,最终履行的诺言又是屈指可数。在这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之时,这种感觉分明占据了上风,他们甚至不需要用言词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而是彼此心照不宣,并在这感觉基础上叙旧、畅谈。
很值得我们羡慕的人是没有的,很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却难以胜数。[392]
生活就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定额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安息是一个相当恰当的表达。
系统的乐观主义…的奠基人是莱布尼茨。他对哲学作出的贡献我无意否认,但我始终无法让自己设想出那样一种由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事物的和谐秩序。针对莱布尼茨所提出的明显诡辩论据——以证明这一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一个——我们甚至可以严肃、正直地提出相反的论据,以表明这一世界是可能之中的最糟糕者。
乐观主义归根到底就是生存意欲毫无根据的自我赞扬——而生存意欲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发动者,它把自身惬意地显现在自己的作品上面。据此,乐观主义不仅是一种虚假的理论学说,而且还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它把生活表现为一种令人羡慕的状态,人的幸福就是生活的目的。一旦从这一观点出发,那每一个人就都相信自己对幸福和快乐有着最正当的要求。而一旦这些幸福和快乐并没有降临在他的头上——这可是常有的事情——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公,甚至会认为错失了他的生存的目标。但实际上,把劳作、匮乏、磨难、痛苦和最终的死亡视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就像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真正的基督教所认为的那样——则是更加正确的观点,因为正是所有这些痛苦、磨难导致了对生存意欲的否定。
要掌握可靠的罗盘以随时辨认生活中的方向,要能够正确理解生活而不至于误入歧途,最适合不过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习惯于把这一世界视为一个赎罪的地方,因此也就好比是监狱、劳改场、罪犯流放地,而“感化地”就是最古老的哲学家对这一世界的称谓。
人充满许多巨大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言论会招致基督教的反感,我甚至斗胆这样说:“如果真有魔鬼的话,他们就是化身为人,并为自己的罪孽而遭受惩罚。”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存在而遭受惩罚,而且,遭受惩罚的方式因人而异。监狱里的坏处之一就是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与这些犯人不得不朝夕相处对于更为高贵的人来说,个中滋味到底如何是不用我说的了。本性高贵的人,还有天才,在这一世上的感觉有时就跟一个高贵的政治犯的感觉一样:他现在被迫混杂在一群偷鸡摸狗、杀人越货的惯犯当中在橹船上做苦役;所以,这两种人都不愿与其他人交往。
我们会牢牢记住人的处境,并把每个人首先视为只是由于罪孽而存在,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为其出生而赎罪。这恰恰就是基督教所说的人的有罪本性;这因此也就是我们在这一世上所看见的我们的同类的构成基础。除此之外,由于这一世界的构成的原因,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处于痛苦和不满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可无法让人变得更有同情心和更加友好待人。最后,几乎所有人的智力都只是勉强足够为意欲服务。[399]
10
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一观点:这个人的基础本来就是有不如无的东西,是某种罪恶、颠倒、荒谬、被[400]认为是原罪的东西;也正因此,一个人命中注定就要死亡。这个人的根本劣性甚至通过这一典型事实反映出来:无人可以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和检查。从人这一生物,我们又能够期待些什么呢?所以,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会更加宽容地判定他人;而一旦潜藏在人身上的恶魔苏醒过来并向外探头探脑的话,我们也不至于那样大吃一惊;我们也就能够更加珍惜在一个人的身上找到的优点,不管这出自他的智力抑或其他的素质。其次,我们将留意到人的处境,并能考虑这一点:生活本质上就是匮乏、需求和经常是悲惨的条件状态;每个人都得胼手胝足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搏,因此,人不可能总是挂着一副笑脸迎人。
“原谅就是一切。”(《辛白林》,第5幕第5景)我们必须以宽容对待人们的每一愚蠢、缺陷和恶行;时刻谨记我们眼前所见的就只是我们自己的愚蠢、缺陷和恶行,因为这些东西不外乎就是我们所属于的人类的弱点和缺陷。
11
生存的虚无通过下面所有这些而充分显现出来:生存的整个形式;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和相比之下个体在时间和空间的有限;现实此刻匆匆即逝——而现时此刻却是现实的惟一存在形式;所有事物之间依存和相对的关系;一切都是变动不居,没有任何长驻、确定的存在;永恒地渴望而又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一切努力奋斗都遭遇障碍——这就构成了生命的进程——直至这些障碍被克服为止,等等。由于时间的原因,所有一切在每一刻都在我们的手里化为虚无并以此失去其真正的价值。
12
曾经存在过的,现在已经不再;其不再存在就跟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没有两样。但此刻存在的所有一切,在即将到来的另一刻就成了曾经的存在。所以,相对于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过去,最没有意义和最不重要的现在所具有的优势就是确实性。
享受现时此刻并使之成为生命中的目标就是最大的智慧,因为只有现时此刻才是惟一真实的,其他一切都只是我们的想法和念头而已。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最大的愚蠢,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刻不再存在、像梦一样完全消失无踪的东西,永远不值得严肃、认真的努力争取。
13
我们生存的立足点除了不断消逝的现时以外,别无其他。这样,我们生存的形式从根本上就是持续的运动,我们总是梦寐以求的安宁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存就像一个跑下山坡的[403]人——要停下脚步就必然跌倒在地,也只有继续奔跑才可以平衡身子;或者,就像在手指头上保持平衡的木杆;再就是像行星——如果行星停止向前运动,就会撞入太阳之中。因此,活动不息就是生存的特征。
14
我们生活中的情景就像镶嵌砖上粗线条的图案:靠得太近时,这些图案无法造成效果,只能从远距离审视才会发现这些图案的美丽。所以,得到了我们热切渴望之物就等于发现了它的空洞和无用。我们总是生活在对更好的期待之中,与此同时也经常后悔和怀念往昔的时光。而现时此刻则只是暂时被忍受而已,我们只把它视为通往我们目标的途径。这样,在就快到达人生的终点时,回眸往昔,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暂时”地活着;他们会很惊讶地看到:自己不加留意和咀嚼就听任其逝去的东西正好就是他们的生活,正好就是他们在生活中所期待之物。
15
我们正处于精神思想贫乏、无能的时期;它的标记就是人们尊崇各种各样拙劣的东西,并且,人们自创的、形容这一时代的重复词——“当代今天”(jetztzeit)——可谓相当贴切,其自命不凡就好像这一时代就是“特别”的、“杰出”的时代,为了这一时代的到来,在这之前的一切时代都只是搭桥铺路而已。
生命首先就呈现为一个任务,也就是说,维持这一生命的任务,亦即法语的“degagnersavie”[9]。谋生的问题解决以后,我们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回来的却成了负担。这样,接下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如何处理、安排这一生活以抵御无聊,而无聊就[406]像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猛兽,伺机而动、随时扑向每一衣食无忧之人。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得到某样东西,第二个任务则是在争取得到某样东西以后,又不能让我们感觉到这样东西,因为我们对其有所感觉的话,它也就成了一种负担。
如果我们试图统观整个的人类世界,那我们就会看到到处都是永无休止的争斗。人们为了生存不惜耗尽全副的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投入殊死的搏斗,防备着各式各样随时发生的、威胁着我们的天灾人祸。而对付出所有这一切努力所换回的报酬——亦即生存本身——审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生存里面有着某些没有苦痛的间歇时间,但这些时间随即马上受到无聊的袭击,并且很快就被新一轮的苦痛所终结。
我们的本质和存在就在于渴求生活,而假如生活本身真有肯定的价值和真实的内容,那是无法产生无聊的。仅只是存在本身就已经让我们充实和满足。但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并没有感到高兴,除非我们正在争取达到某一目标——因为距离遥远和遭遇障碍的缘故,这一目标[407]显得会带给我们满足,但目标一旦达到,幻象也就会随之消失——或者,除非我们正在从事纯粹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我们从生活中抽身,现在是从外面回头审视这一生活,就像坐在包厢里的旁观者。甚至感官的快乐本身也只在于持续的渴求,而一旦目标达到,快乐也就消失了。一旦不是处于上述两种情形,而是返回存在本身,对生存的空洞和虚无的感觉就会袭上心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聊。甚至我们内在特有的、无法消除的对特别、怪异事情的追求和喜好也显示出我们巴不得看到事物发展那单调、无聊的自然秩序能够中断。甚至上流社会的奢侈、热闹的喜庆和富丽堂皇的排场也不是别的,其实正是为跨越这一本质上贫瘠、可怜的生存而作出的徒劳无功的努力。
16
人的极尽巧妙和复杂的机体就是生存意欲所显示出的最完美的现象,但这些现象最终还得化为尘土,这些现象的整个本质和努力因此也最终明显归于毁灭;意欲的所有争取根本上就是虚无的——这些就是真实和坦率的大自然所给予的单纯、朴实的表达。
死亡的必然性……可以首先从这一事实推导出来:人只是一种现象,因此,并不是“真正、确实的”(柏拉图语)——如果人真的是自在之物,那人就不会消亡了。至于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却只能在现象里呈现出自身——那是自在之物的本性所使然。
我们的开始和我们的结局构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前者产生于肉欲造成的幻象和性欲快感所带来的心醉神迷之中,后者则伴随着所有器官的毁坏和尸体发出的恶臭。在愉快和享受生命方面,从出生到死亡走的也始终是下坡路:快乐幻想的童年,无忧无虑的青年,艰苦劳累的中年,身衰力竭并经常是令人同情的老年,临终疾病的折磨和最后与死神的搏斗。这一切难道没有表明:存在就是失足,恶果随后就逐步和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吗?
把生活视为幻灭是最精确的看法,所有一切都清楚无误地指示着这一点。
17
我们的生活具有某种微观的特性:它是一个不可分的点,它被时间、空间这两样强力的透镜所拉开和拉长,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生活已被放大了许多。
时间是我们头脑中的装置——它透过某种时间上的维持让事物以及我们自身彻头彻尾的虚无的存在披上了一层实在现实的外表。
由于在过去错失机会获得某一幸福或者享受某一快乐而后悔和悲哀,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幸福或者享受到现在还能剩下些什么呢?只是某一千瘪的记忆罢了。对于所有我们真实享受和经历过的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时间形式”完全就是一个媒介——它就像是特意为让我们明白所有尘世间快乐所具有的虚无本质而设。
我们以及所有动物的存在并不是某样牢固、起码是暂时不变的东西,相反,这些只是流动性的存在……,它的存在就在于持续不断的变化,就像水里的漩涡一样。虽然身体的“形式”暂时和大概地存在,其前提条件却是身体物质持续变化,不断地新陈代谢。所以,所有人和动物的首要任务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争取获得适合于流入身体的物质。
如果我们不再从大处审视世事发展的进程,尤其是人类快速的世代更迭及其匆匆一现的存在假象,而是转而观察人类生活的细节…——就像在喜剧里所展现的样子——那么,我们头脑中获得的印象就犹如透过高倍显微镜观察满是纤毛虫的一滴水或者察看肉眼难见的一小块奶酪菌——里面的螨虫辛勤地活动和争斗使我们失声而笑。这是因为正如在极为狭窄的空间展开严肃认真、隆重其事的活动会产生喜剧的效果,同样,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同样的事情也发挥出同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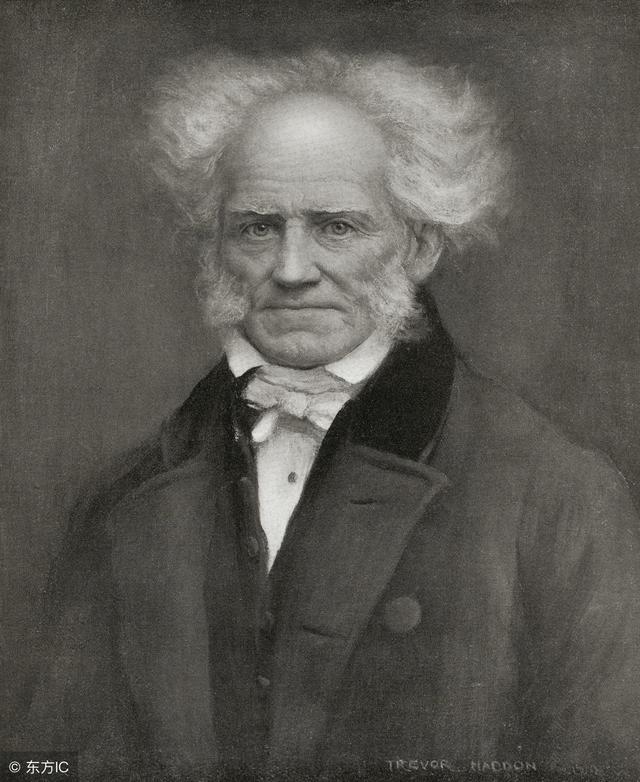
叔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