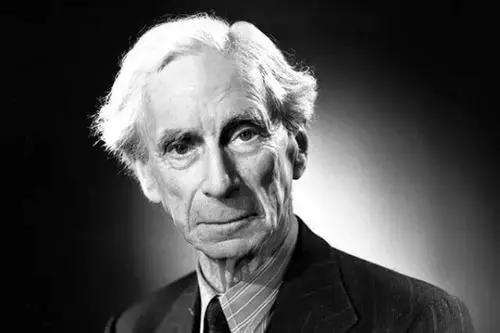
很少人能够快乐,除非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大致能获得与他们在社会上有关系的人的赞同,尤其是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人的赞同。
近代社会有一种特色,即是它们分成许多道德观和信仰各各不同的派别。这种情形肇始于宗教改革,或者应该说源自文艺复兴,从那时以后,事态就愈趋愈分明。先是有旧教徒和新教徒之分,他们不但在神学上,而且在不少比较实际的问题上歧异。再有贵族和中产阶级之别,前者可以允许的各种行为,后者是绝对不能通融的。又有自由神学派和自由思想者,不承认奉行宗教规则的义务。我们今日,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之间又有极大的分野,不独限于政治,抑且涉及生活的各部门。在用英语的国土内,派别多至不可胜计。艺术被有些集团所崇拜,被另一些集团认为魔道,无论如何现代艺术总被认为邪恶。在某些集团中,尽忠于帝国是最高的德性,在别的集团中却是一桩罪行,又有些集团认为是愚事的一种。狃于习俗的人把奸淫看作罪大恶极,但极多人认为即使不足恭维至少也是可以原谅的。离婚在旧教徒中间是绝对禁止的,但多数非旧教徒以为那是婚姻制度必需的救济。
由于这些不同的看法,一个有某些嗜好与信念的人,处于一个集团中时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放逐者,而在另一集团中被认为极其普通的人。多数的不快乐,尤其在青年中间,都是这样发生的。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道听途说的摭拾了一些观念,但发觉这些观念在他或她所处的特殊环境中是被诅咒的,青年人很容易把他们所熟识的唯一的环境认作全社会的代表。他们难得相信,他们为了怕被认为邪恶而不敢承认的观点,在另一个集团或另一个地方竟是家常便饭。许多不必要的苦难,就是这样地由于对世界的孤陋寡闻而挨受的,这种受苦有时只限于青年时期,但终生忍受的也不在少。

这种孤独,不但是痛苦之源,还要浪费许多精力去对敌意的环境维持精神上的独立,并且一百次有九十九次令人畏怯,不敢贯彻他们的思想以达到合理的结论。勃朗德姊妹(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三姊妹皆以小说名世。)在印行作品之前从未遇到意气相投的人。这一点对于英雄式的、气魄雄厚的爱弥丽·勃朗德固然不生影响,但对夏洛蒂·勃朗德当然颇有关系了,她虽有才气,大部分的观点仍不脱管家妇气派。同时代的诗人勃莱克,像爱弥丽一样,也过着精神极度孤独的生活,但也像她一样,有充分的强力足以消除孤独的坏影响,因为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批评他的人是错的。他对公众舆论的态度,读下面几行就可知道。
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不使我作呕的,
是斐赛利:他又是回教徒又是犹太人,
那末亲爱的基督徒,你们又将如何?
(译者按:回教徒与犹太人皆为基督徒所恶,但勃莱克却认为唯有这种人不使他憎厌,足见他的蔑视公共舆论。)

但在内心生活里具有这等毅力的人是不多的。
友好的环境,几乎为每个人的快乐都是必需的。当然,大多人都处在同情的环境之内。他们青年时习染了流行的偏见,本能地承受了周围的信念和风欲。但有另一批少数的人物,其中包括着一切有些灵智的或艺术的价值的人,绝对不能取这种俯首帖耳的态度。假定有一个生在小乡镇里的人,从幼年起就发觉在他精神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全都遭受周围的白眼。假定他要念一些正经的书,别的孩子们就瞧不起他,教师们告诉他这类书是淆惑人心的。假如他关心艺术,伴侣们就认为他没有丈夫气,长辈又认为他不道德。假如他渴望无论怎样体会的前程,只消在他的集团里是不经见的,人们便说他傲慢,并说对他父亲适配的事应该对他也适配。倘他对父母的宗教主张或政治党派发表批评,很可能招惹严重的是非。为了这许多理由,在多数具有特殊价值的青年男女,少年时期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时期。为一般比较平凡的伴侣,这倒是一个快乐和享受的辰光;至于他们,却热望着一些更严肃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特殊的社会集团内,在前辈和平辈身上都找不到这严肃的东西。
这等青年进入大学时,大概能发见一些气味相投的知己,享几年快乐生活。运气好的话,他们离开大学之后可以找到一项工作,使他们仍可能选择一般契合的伴侣;一个住在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大教市里的聪明人,普通总可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集团,可毋需受什么约束或装什么虚伪。但若他的工作迫使他住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尤其不得不对普通人士保持尊敬的时候,例如律师和医生的职业就得如此,那末他可能终生对大半日常遇见的人,瞒着他真正的嗜好和信念。这种情形在美国特别真切,因为幅员广大。在你最意料不到的地方,东、南、西、北,你会发见一些孤寂的人,从书本上得知在有些地方他们可能不孤独,但是没有机会住到那边去,即是知心的谈话也是绝无仅有。在这等情势之下,凡是性格不像勃莱克那么坚强的人,就不能享有真正的幸福。
假如要真正的幸福成为可能,那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减轻公众舆论的专横或逃避它,而且借助了这个方法,使聪明的少数分子能彼此认识而享受到互相交往之乐。

在好多情形中,不必要的胆怯使烦恼变得不必要的严重。公众舆论对那些显然惧怕它的人,总比对满不在乎的人更加横暴。狗对怕它的人,总比对不理不睬的人叫得更响,更想去咬他;人群也有同样的特点。要是你表示害怕,保准你给他们穷追,要是你若无其事,他们便将怀疑他们的力量而不来和你纠缠了。
当然,我并不鼓吹极端的挑衅。倘你在肯新吞(按:系伦敦市区之一)主张在俄罗斯流行的见解,或在俄罗斯揭橥在肯新吞很平常的观点,你一定要受到后果。我所说的并非这样的极端,而是温和得多的背叛习俗的行为,例如衣冠不整,或是不隶属于某些教堂,或是不肯读优秀的书等等。这一类的背叛,要是出之于不拘小节与和悦的态度,出之于自然而非挑衅的,那么即使最拘泥的社会也会容忍。久而久之你可取得大众承认的狂士地位,在别人身上不可原恕的事情,在你倒可毋容禁忌。这大部分是性情温良与态度友好的问题。
守旧的人所以要愤愤然的攻击背弃成法,大半因为他们认这种背弃无异是对他们的非议。假如一个人有充分的和悦与善意,令最愚蠢的人都明白他的行为全无指责他们的意思,那么很多违反习俗之事可以得到原谅。
然而这种逃避物议的方法,为那般以趣味或意见之故而绝对不能获得周围同情的人,是没有用处的。周围的缺少同情,使他们忐忑不安,常常取着好斗的态度,即使他们表面上证明,或设法避免任何尖锐的争执,也是徒然。因此,凡与自己集团中的习俗不和谐的人,常倾向于锋芒外露,心神不安,缺少胸怀开朗的好心情。这些人一旦走到另一个集团,走到他们的观点并不被认为奇怪的派别中去时,他们的性格似乎完全改变了。他们能从严肃、羞怯、缄默,一变而为轻快和富有自信;能从顽强一变而为顺易与;能从自我中心一变而为人尽可亲。
所以凡是与环境不融洽的青年,在就业的时候,当尽量选取一桩能有气味相投的伴侣可以遇到的事业,即使要因之而减少收入也在所不顾。往往他们不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有限,很容易把他们在家里看惯的偏见,误认为是普天下皆是。在这一点上,老一辈的人应该能予青年人很多助力,既然最重要的是对人类具有丰富的经验。

当此精神分析盛行的时代,极普通的办法是,认定一个青年和环境龃龉时,原因必在于什么心理上的骚乱。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桩错误。譬如,假定一个青年的父亲相信进化是邪说。在这个情形之下,使他失去父亲同情的,唯有“聪明”二字。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但并非一定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愚蠢,或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而上述的许多缺点,在某种程度内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中都存在。
伽利莱(十六世纪意大利天文家)与凯不勒(十七世纪德国天文家)有过像日本所称的“危险思想”,我们今日最聪明的人也大半如是。我们决不该祝望,社会意识发展的程度,能使这样的人物惧怕自己的见解所能引起的社会仇视。所当祝望的,是寻出方法来把这仇视的作用尽量减轻和消灭。
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极大部分发生于青年界。倘然一个人一朝选择了适当的事业,进入了适当的环境,他大概总能免受社会的迫害了;但当他还年轻而他的价值未经试炼时,很可能被无知的人摆布,他们自认为对于一无所知的事情有资格批判,若使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胆敢说比有着多少人情世故的他们更懂得一件事情的话,他们便觉得受了侮辱。许多从无知的专制之下终于逃出来的人,会经历那么艰苦的斗争,挨过那么长时期的压迫,以致临了变得满腔悲苦,精力衰敝。有一种安慰人心的说法,说天才终归会打出他自己的路,许多人根据了这个原则便认为对青年英才的迫害,并不能产生多少弊害。但我们毫无应该接受这原则的论据。那种说教很像说凶手终必落网的理论。显然,我们所知道的凶手都是被捕的,但谁能说我们从未知道的凶手究有多少?同样,我们听到过的天才,固全都战胜了敌对的环境,但毫无理由说:并没有无数的天才在青年时被摧残掉。何况这不但是天才问题,亦且是优秀分子的问题,这种才具对于社会也是同样重要啊。并且这也不但是好歹从舆论的专制之下挣扎出来就算的问题,亦且是挣扎出来时心中不悲苦,精力不衰竭的问题。为了这些理由,青春时期的生活不可过于艰苦。

老年人用尊重的态度对付青年人的愿望,固然是可取的,但青年人用尊重的态度对付老年人的愿望却并不可取。理由很简单,就是在上述两种情形内,应该顾到的是青年人的生活,而非老年人的生活。但当青年人企图去安排老年人的生活时,例如反对一个寡居的尊亲再度婚嫁等等,那末其荒谬正和老年人的企图安排青年人的生活一样。人不问老少,一到了自由行动的年纪,自有选择之权,必要时甚至有犯错误的权利。青年若是任何重大的事情上屈服于老年人的压迫,便是冒失,譬如你是一个青年人,意欲从事舞台生活,你的父母表示反对,或者说舞台生活不道德,或者说它的社会地位低微。他们可能给你受各式各样的压力,可能说倘你不服从就要把你驱逐,可能说你几年之后定要后悔,也可能举出一连串可怕的例子,叙述一般青年莽莽撞撞的做了你现在想做的事,最后落得一个不堪的下场。他们的认为舞台生活与你不配,或许是对的;或者你没有演剧的才能,或者你的声音不美。然而倘是这种情形,你不久会在从事戏剧的人那边发现的,那时你还有充分的时间改行。父母的论据,不该成为使你放弃企图的充分的理由。倘你不顾他们的反对,竟自实现了你的愿望,那末他们不久也会转圜,而且转圜之快,远出于你的和他们的意料之外。但若在另一方面,有专家的意见劝阻你时,事情便不同了,因为初学的人永远应当尊重专家的意见。
我认为,以一般而论,除了专家的意见之外,大家对别人的意见总是过于重视,大事如此,小事也如此。在原则上,一个人的尊重公众舆论,只应以避免饥饿与入狱为限,逾越了这个界限,便是自愿对不必要的专制屈服,同时可能在各方面扰乱你的幸福。
譬如,拿花钱的问题来说。很多人的花钱方式,和他们天生的趣味完全背驰,其原因是单单为了他们觉得邻居的敬意,完全靠着他们有一辆华丽的车子和他们的能够供张盛宴。事实是,凡是力能置备一辆车子,但为了趣味之故而宁愿旅行或藏中的人,结果一定比着附和旁人的行为更能受人尊敬。这里当然谈不到有意的轻视舆论;但仍旧是处于舆论的控制之下,虽然方式恰恰是颠倒。(按:一种是怕舆论,另一种是迎合舆论。其为舆论所役则一。)但真正的漠视舆论是一种力量,同时又是幸福之源。并且一个社会而充满着不向习俗低首的男女,定比大家行事千篇一律的社会有意思得多。在每个人的性格个别发展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典型保存着,和生人相遇也值得了,因为他们决不是我们已经遇见的人的复制品。这便是当年贵族阶级的优点之一,因为境遇随着出身而变易,所以行动也不致单调划一。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正在丧失这种社会自由的源泉,所以应当充分明白单纯划一的危险性。我不说人应当有意行动怪僻,那是和拘泥守旧同样无聊。我只说人应当自然,应当在不是根本反社会的范围之内,遵从天生的趣味。

由于交通的迅速,现代社会的人不像从前那样,必须依赖在地理上最接近的邻居了。有车辆的人,可把住在二十里以内的任何人当作邻居。因此他们比从前有更大的自由选择伴侣。在无论哪一个人烟稠密的邻境,一个人倘不能在二十里之内觅得相契的心灵,定是非常不幸的了。在人口繁盛的大中心,说一个人必须认识近邻这个观念早已消灭,但在小城和小乡村内依旧存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愚蠢的念头,既然我们已无须依赖最近的邻居做伴。慢慢地,选择伴侣可能以气质相投为主而不以地域接近为准。幸福是由趣味相仿、意见相同的人的结合而增进的。社交可能希望慢慢往这条路上发展,于是也可能希望现在多少不随流俗的人的孤独逐渐减少,以至于无。毫无疑问,这可以增进他们的快乐,但当然要减少迂腐守旧的人的快乐,——目前他们确是以折磨反抗习俗的人为乐的。然而我并不以为这一种的乐趣需要加以保存。
畏惧舆论,如一切的畏惧一样,是难堪的,阻碍发育的。
只要这种畏惧相当强烈,就不能有何伟大的成就,也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所需的精神自由,因为幸福的要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必渊源于我们自己的深邃的冲动,而非渊源于做我们邻居或亲戚的偶然的嗜好与欲念。
对近邻的害怕今日当然已比往昔为少,但有了一种新的害怕,怕报纸说话。这正如中古时代的妖巫一样骇人。当报纸把一个也许完全无害的人选做一匹代罪的羔羊时,其结果将非常可怕。幸而迄今为止,对这样命运,多数的人还能因默默无闻之故而幸免;但报纸的方法日趋完备,这新式的社会虐害的危险,也有与日俱增之势。这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受害的个人决不能以藐视了之;而且不问你对言论自由这大原则如何想法,我认为自由的界限,应当比现在的毁谤法律加以更明确的规定,凡使无辜的人难堪的行为,一律应予严禁,连人们实际上所作所为之事,也不许用恶意的口吻去发表而使当事人受到大众的轻视。然而,这个流弊的唯一最后的救济,还在于群众的多多宽容。增进宽容之法,莫如使真正幸福的人增多,因为唯有这等人才不会以苦难加诸同胞为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