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和善的问题是融为一体的。对善的问题做不同的概念处理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思想史方向,孵育不同的文明。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思想专注于善的问题,并在和他人的讨论中形成了一套关于善的话语体系,规定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几乎和孟子是同时代人,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也以善的问题为思想主题,给出了一系列关于善的论证,为西方思想史定下基调。这两位思想家对各自的思想传统来说都是奠基性的人物。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发展方向完全不同,我认为,和这两位思想家关于善的处理直接相关。因此,通过分析他们在善的问题上的相关说法,我们可以追踪中国和西方思想的原始分歧点。
柏拉图和孟子所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孟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企图为社会回归一种完善社会秩序寻找道路;而柏拉图也是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政治生活带来的混乱局面,希望为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设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体制。就两者的问题之相似性而言,这是一个混乱如何回归秩序的问题。然而,他们的社会环境以及供他们使用的思想资源很不相同。所以,他们在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采用了不同方式。我想通过深入分析这个“不同”来展示中国和西方思想传统在起点意义上的差异。理解这个差异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西方思想史,也可以推进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深入反思。
柏拉图:善和真理
我们先来分析柏拉图。柏拉图在他的《米诺篇》(77B-78B)中论证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即“人皆求善”。书中的苏格拉底认为,人没有例外都是求善的。这个命题不是观察命题。在观察上,我们看到的是,有人求善;有人求恶。因此,这个命题不是归纳的。毋宁说,这个命题是一个论证命题。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必须提供一个论证来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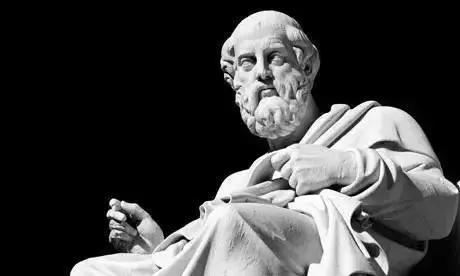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复杂,但力量却非常强大。苏格拉底的这个论证可以称为“排除法”。就观察而言,我们都同意可以把人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求善的,一部分是求恶的。这是一个观察事实。从这里出发,苏格拉底说,对于求善的那部分人,他们是求善的。因此,我们不用管这部分人。对于那些求恶的人,他认为,还是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恶为善而求恶”,一类是“明知恶而求恶”。在这两类人中,那些“以恶为善”的人,当他们在追求恶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是恶的。相反,他们以为在追求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柏拉图认为,在于他们善恶不分,把恶判断为善,从而选择并追求恶。无论如何,他们是在善的判断中追求恶,就其主观愿望而言是求善的。因此,我们应该把他们归为求善的那一类人。
剩下的第二类人:明知为恶而求恶。 对于这种人,他们还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明知为恶但为利而求恶”,另一种是“明知为恶且无利而求恶”。对于“明知为恶但为利而求恶”的这种人,如贪污官员,明知贪污不好,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贪污了,分析他们的动机,我们发现,他们在做决定的那个时刻,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恶的,而是因为它有利可图。因此,决定他作恶的那个因素是有利可图。尽管我们可以说,这个“有利可图”不过是暂时的利益,是当事人目光短浅所致。然而,在这个时刻,主导意识是把这个利益当作最重要的善,并且以此为他的选择根据。显然,他是在善的名义下决定作恶。因此,柏拉图认为,这种人是属于求善的。
根据这个排除法,似乎还有一种人,即:“明知为恶且无利而求恶”。然而,柏拉图的分析表明,这个“种”是一个空项。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人。我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个个例归入这个“种”。柏拉图采用的是逻辑上的排除法。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使用排除法时,总会有一种感觉,即:尚未穷尽所有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也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为此,我想给出一些极端的例子来旁证柏拉图的论证。比如,损人不利己的人在做这事时是要满足自己的某种快感。自杀的人是绝望的,认为他已经无路可走,死是一条出路。有人为了报复社会而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如杀戮孩童,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这类极端的事还很多。然而,人们在做这些事时,没有例外地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一个善的选择,如“快感”、“出路”、“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善的。
与动物不一样,人的生存是在选择中进行的。人的生存是在选择中从这一个时刻进入到下一个时刻的。选择指的是在两个以上的选项中进行选择。为了选择其一,人必须比较选项的善性,给出一个善判断,然后选择那个善。这就是柏拉图的人皆求善的思路。
这个在论证中给出的命题,在柏拉图看来,表达了一个人类生存事实。和观察事实不同的是,这个生存事实是在论证中给出的。在柏拉图看来,除非我们能够在论证中推翻这个推论,否则,这个事实就具有实在性。当然,这个生存事实(人皆求善)和我们的观察事实(有人求善、有人求恶)不吻合。应该如何对待这两种事实的不吻合呢?柏拉图反复指出,那些在观察中表现为求恶的人,就他们的原始意愿而言是求善的。他们的“求恶”在于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善判断。进一步,他们的错误善判断来自他们的错误善观念,即:善恶不分,把恶的当作善去追求。如此看来,这两种事实的不吻合根源于人们的错误善观念。如果人拥有了正确的善观念,做出了正确的善判断,那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求恶现象。
有两件事情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其一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人打败。这场战争是雅典人挑起的,以雅典被占领为结局。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雅典法庭在战争期间处死了十位海军将军。 其一是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忠实追随者,甚至认为他的想法都来自苏格拉底,所以,他的前期作品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发言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两条罪状是:引入新神和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之死
这两件事充分表达了雅典人的自以为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是在自己的现有善观念中做出善判断。在他们的判断中,这些将军们该死;苏格拉底该罚。这是典型的以恶为善的善判断。他们的错误的善判断来自他的错误的善观念。他们的错误的善判断给他们和城邦都带来了灾难。如何避免这种生存上的悲剧?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寻找并确立正确的善观念,然后才能给出正确的善判断。正确的善观念乃是对真正的善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真正的善出发,以善为善,并在追求中得到善。
我们看到,柏拉图是在这个思路中提出真理问题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观念。善观念是善判断的基础。所有符合善观念的善判断都是正确的。逻辑上看,当多种善观念出现并发生冲突时,如果它们不一致,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它们都是错的,或者它们只有一个是对的。它们不可能都是对的。因此,问题可以提出,谁的善观念把握住了真正的善?这个问题引申为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真正的善?其次,凭什么我们的善观念把握了真正的善?前者是认识途径问题;后者是真理标准问题。于是,善的问题就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
在这个真理问题的思路中,柏拉图考察了两种认识论,即信念认识论(在信任情感中接受他人的想法)和理性认识论(依靠自己的判断能力进行推理),认为在认识论上解决善的问题是我们生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认识上找到了真正的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选择时,我们的生存就是以真正的善为出发点,避免了以恶为善带来的悲剧,在追求中得到善,满足自己对善的追求。
柏拉图从“人皆求善”这一生存事实出发,分析了社会上的各种恶的现象,发现人们并非自觉追求恶,而是由于缺乏关于真正的善的认识,在判断中以恶为善,从而导致了人们不自觉地追求恶。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要避免追求恶,就必须认识真正的善,然后从真正的善出发实现对善的追求。
孟子:善和本性
孟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来说,只要按照社会已定的规范行事,就是善的行为。周朝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社会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称为“周礼”。到了春秋时期,周礼受到严重的破坏。从齐桓公九合诸侯开始,各诸侯国追逐自己的利益,无视周礼约束。这里,从周礼的角度看,各国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是一种恶。但是,从各国自身利益来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在孟子看来,这样的社会是人人都在追逐自己利益的社会。

孟子
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一场对话值得我们重视。梁惠王见了孟子的第一句话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里的对话是“利”和“仁义”的对立。我们先来分析“利”字。在孟子看来,国有一国之利,家有一家之利,人有一身之利。就词源学而言,“利”的原始意思是刀刃的锋利,转指一种能力,和作为动词的“善”意义相通,如善战、善言等。正如“锋利”对于一把刀来说是一种“好”或“善”一样,任何有“利”的东西对于拥有者来说就是一种“好”或“善”。显然,“利”仅仅属于拥有者。它不涉及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它可以对他者也是有“利”的(如共同利益),也可以是有“害”的(如敌对双方)。因此,梁惠王谈到的“利吾国”,是要强调增强自己国家的能力。孟子反对人们仅仅从“利”出发来谈论“善”,给出的理由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如果人人都在求利,社会就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每一国家都面临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如果损害他国利益,就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士大夫也这样争利,就会把这个国家带入纷争,损害国家利益。同样,如果士大夫家里的每一个人也在争利,这个家庭的利益也必受损害。因此,从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天下将危,国家将危,家庭将危。天下大乱,则国家无宁;国家内乱,则家庭无宁;家庭无宁,则个人无宁。因此,无论是国家、家庭、还是个人,都不应该从利益出发处理事情。
我们应该从那里出发呢?在孟子的思路中,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可以是互利和谐的,也可以是互损冲突的等等。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社会关系对有某些人有利,对其他人有损。有些社会关系对较多人有利,甚至全体成员都有利。有些社会关系则只对较少人有利,乃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损。因此,寻找到一个好的社会关系,让更多人得到益处,就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个思路上,孟子对梁惠王说:“亦有仁义而已矣”。可见,孟子要求梁惠王先谈“仁义”,实际上是在谈论个人生存和社会治理的出发点问题。换句话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来说,出发点应该是“仁义”,而不是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这里把社会关系归为我们生存的出发点,并不是简单地把某种共同利益(如天下利益、国家利益或家庭利益)当作出发点。他注意到,每个人或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国家有国家利益,家庭有家庭利益,每个人也有自身利益等等。如果从利益出发,上仿下效,各方都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视他者利益。这样一来,国家与国家、或家庭与家庭之间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孟子关心的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社会关系,体会或寻找合适的兼顾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即“仁”是有“义”之“仁”,或在“义”中界定的“仁”),并把这种社会关系固定为社会规范(礼),这样,各方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这便是“仁义礼”的谈论方式。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孟子是在哪个意义使用“仁义”二字的。《诗经》用“仁”来描述一个人的样子,如“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等等。就其原始含义而言,“仁”乃是对人这类存在的描述,意思相当于说,这才是人的样子。一个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才算是人的样子呢?这涉及对人这种存在物的界定。其实,人们在谈论人时,总是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人,但却无法明确表达。如何明确地界定人这种存在就具有某种迫切性了。在先秦文献中常常读到这个界定:“仁者,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仁”就是人应该如此这般的那个样子。
显然,在谈论人应该如此这般的样子时,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一个自我评价,一个他人评价。古文关于“仁”有两种写法,一作“ 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谢文郁)”,一作“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谢文郁)”。 这两种写法反映了古人关于“人应该如此这般”的看法有两条思路。自我评价强调个体的构成。其他动物有身体,但人还有心灵。这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点。不过,这个心灵是不可观察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直接感受到它的存在(自我评价)。这便是“ 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谢文郁) ”(从身从心)这种写法所代表的谈论角度。他人评价通过“ 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谢文郁) ”写法强调人的社会生活,即“两个人”。这后一种写法认为,要理解一个人必须从社会关系出发。可以观察到,人生活在社会中,离开他人便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强调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特征,我认为,便孟子所承传的“ 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谢文郁) ”这种写法所代表的思路。人和人的关系,就其原始状态而言,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意思是说,最原始或最实在的社会关系便是这种血缘亲情。从这一角度看,孟子关于“仁”的理解乃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
孟子反对梁惠王从“利”出发来观看社会,并以此基础为人处事、治理国家。他所主张的“仁政”是要提醒他的听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出发点。“仁”这个字承载了两个要点:我们只能在社会关系中生存(作为生存事实),因而我们的生存必须从关怀社会关系开始(作为生存出发点)。人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已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接受相应的社会规范约束。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父子之间可以有孝的关系,也可以是父子平等的关系,也可以是父亲侍候儿子的关系等等。梁惠王一见面就谈论利益。在孟子看来,这表明他生活在一种以利益为杠杆的社会关系中。这是一种缺乏“义”的社会关系。有些社会关系是有害的,如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有些社会关系是善的适合人的生存的。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关系中,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何为合适的社会关系,并去寻找这样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合适的社会关系便是“仁义”,即:在“义”界定的“仁”。在这个意义,孟子希望梁惠王改变视角,从“仁义”出发:“亦有仁义而已矣”。从“仁义”出发施政就是“仁政”。
关于“义”,先秦的相关文献往往是在“合适”、“合宜”这个意义使用它的。孟子谈到:“义之实,从兄是也。” 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合适”这种意识呢?就现象观察而言,孟子认为,这是从学着兄长的样子开始的。对于开始懂事的孩童来说,父母的教训会让他产生敬畏感。但是,因为父母的爱,他在按照父母的教训做事时常常伴随两种感情:害怕(如果受到惩罚)和好玩(如果受到表扬)。在父母面前,他没有羞耻感,因而不会对自己言行是否恰当这一点有感觉。兄弟之间的年龄相近,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不同于父母之情。这种兄弟之情也是原始性的。对于弟弟来说,兄长的为人处事就是合适的。兄长的言行就是榜样。在这种感情交流中,兄长对弟弟的嘲笑或批评会让弟弟会感觉到自己的说话做事的不合适。这便是原始的羞耻感。一旦出现羞耻感,从这个时刻起,做弟弟的就开始有了“义”的意识,并根据自己对“义”的理解调整自己的言行。这便是最原始的羞耻感,是人追求“义”的原始冲动。所以,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中庸》(章20)也是从“适宜”、“恰当”在这个思路上阐释“义”字的:“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人生活在社会中,从小到大必须学习合适地为人处事。从最简单的羞耻感开始,一个人先是在一些事情上,然后是在许多事情上,最后是在所有事情上,都做的得体。达到了这个程度,他就成了贤者,为众人的榜样。
对“义”作“宜”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我们说,孟子所说的“仁义”乃是指称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亦有仁义而已矣”这种说法的关键点在于,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首先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体会并寻找合适的社会关系,形成规范,共同接受约束。只有这样形成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孟子认为,这种生存乃是以“仁义”为出发点的生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规范的生存,是一种“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的生存。
人在社会中生存,他们可以采纳不同的社会关系和规范。这是现实中的社会。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人们乐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人处事,觉得为人处事就该这样。为什么人一定要从“仁义”出发?为什么一定要在合适的社会关系生存?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给出回答。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在原始情感中指向一种善的生活。因为人是在社会中生活,所以这种善的生活不是一种孤独生活,而是一种善的社会生活。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战争,损害自身利益。从“仁义”出发,体会并生活于合适的社会关系之中,就能够过一种善的社会生活,共同受益。因此,“由仁义行”乃是人的本性做要求的。
我们先来看看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发现,人和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有一些特别的原始情感,主要有四种:“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 这些原始情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同时,它们所指向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作为原始动力(出发点,“端”)推动人在社会中为人处事。其中,“恻隐之心”指的是人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比如,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见他人落难,人会出现自然而然的同情相怜感觉。这种恻隐之心是人的原始感情,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这同时也表明了,“仁”不是外加给人的,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羞恶”是对自己的言行是否合适的原始感觉;“辞让”是行为的自我约束原始意识;“是非”则是思想活动的原始判断。这四种原始感情的前三种都指向人和人的关系。孟子认为,这些原始性的感觉、感情、意识来源人的本性,是自发性的冲动,都是善的。孟子用“可欲之谓善” 来描述这种原始性冲动。
我们注意到,孟子从“可欲”的角度来谈论“善”。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可欲”意思是生存上的“想要”,即生存倾向。有什么本性,就有什么“可欲”。如果“可欲”的就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就必须是善。因此,孟子推论到,人的本性是善。在和告子讨论人性时,孟子谈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这里,孟子实际上是从人的生存倾向向善这一观察出发推论出人性本善的结论的。重构其中的逻辑结构如下:
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是善,遵循自己的本性就能够过一种善的生活;违反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恶的生活。孟子的“揠苗助长”故事很能说明这里的思路。当人逆着自己的本性为人处事时,他就在做一系列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儒家的主流传统遵循孟子的这个思路,发展并丰富了修身养性作为生命的主题,即:要求我们充分体会自己的本性冲动,修正与自己本性不符的情欲、想法和做法,按照本性为人处事。这便是所谓的君子之道。
真正的善和本性之善
人应该如何为人处事?什么是合适的生存?这些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合适或善的问题,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具有普遍性。这类问题的出现往往都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困境(如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等),感觉到无法继续按照现存的社会状态生存下去。然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却引导着不同的个人生存方向和社会发展模式。鉴于柏拉图和孟子各自对中西文化的影响具有出发点意义,简单地比较他们的不同回应思路,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种文化在思维性格上的差异性。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善为人处事。无论是“人皆求善”,还是“可欲之谓善”,都是从生存的角度界定“善”。我称之为生存即善。在柏拉图和孟子看来,我们的社会治理出问题了。我们周围的人在生存上出差错了。如果不加以纠正,这个社会就危险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危险了。如何纠正这个社会的问题和纠正他人的错误?在柏拉图提供的解决方案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思路。人人都在求善,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人们在判断上以恶为善。判断依据思想中的善观念。依据错误的善观念,就会做出以恶为善的判断。因此,纠正的途径就是找到真正的善。只有我们拥有了真正的善,拥有正确的判断根据,我们给出的善恶判断才不会出差错,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保证我们的向善生存。作为判断的根据,善观念乃是一种关于真正的善的知识。也就是说,真正的善这个问题是一个知识论问题。按照这条思路,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并把握真正的善(拥有真知识),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善恶判断,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出差错,我们的生存也就在正道上。于是,作为生存的出发点,真知识(把握了真正的善的知识)问题就是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跟随者的主要关注。这个关注在思想史上称为追求真理情结。
孟子在“可欲之谓善”的说法中完全认可个人在生存上对善的追求。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是在“仁义”这一观察的前提下给出的认可。在他看来,人生活在社会中,善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因而必须把着眼点放在社会关系中,体会何为合适的社会关系,并从此出发设置规范,调整社会生活。这便是“亦有仁义而已矣”的意思。“可欲之谓善”中的“善”归根到底是指向“仁义”的。孟子对于人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不同的生存出发点这一事实有深刻洞察,并在此基础上批评人们在为人处事上忽略了“仁义”这一出发点。在这个思路中,人们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种语境中,社会关系对于人来说无法外在化而成为一个认识对象。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寻找合适的社会关系时无法把自己当作对象来思考。他必须置身于其中,并且作为其中的一员而体会合适的社会关系。因此,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是合适的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生存体验的问题。作为其中的一员,每一个人在体验合适的社会关系时,既是体验者,同时也是被体验者。这一思路可以简述如下:为了说明人必须把“仁义”当作首要关注,以此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出发点(“由仁义行”),孟子在“可欲之谓善”的前提下推论出人性本善的结论。于是,人的生存能否向善的关键点就是发扬本性中的善性。这便是所谓的修身养性。我们称此为功夫论。
这是认识论和功夫论的对立。认识论强调对真正的善的认识和把握。人必须把握住真正的善,并从此出发判断选择,只有这样,人的生存才能满足对善的追求。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真正的善。但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善?如何判断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善?在西方思想史上,问题的焦点是如何认识真理(真理之路)?如何判断我们把握住了真理(真理标准)?在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古希腊人在真理之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欲罢不能,最终在基督教的恩典真理论那里找到落脚点。
功夫论承认人们有不同的善知识。但是,孟子强调,人的生存必须从“仁义”出发,在修身养性中把握合适的社会关系,并通过“礼”来调整自己的言行(“克己复礼”)。这里,生存的关键点是修身养性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路可以和认识论毫不相关。在修身养性中,人们不会追求这样的问题,哪种社会关系才是真正合适的?只要人在修身养性中体验到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他就会按照他所体验到的社会关系去为人处事。当然,他在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但这并不一定会引导他追问“真正合适”这类认识论问题。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员,人只需要着眼于当下的社会关系(“由仁义行”),并在其中体验何为合适的社会关系。人的修养功夫进深到哪个程度,他对合适的社会关系(“仁义”)的认识就达到哪个程度。他在生存中只能按照自己所理解的“仁义”而行。如果他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导致他在处理和他人的关系时出现冲突,那么,他就会反求诸己,进一步修身养性,体验何为合适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到,功夫论的中心关注不是认识论,而是修身养性的功夫,发扬本性中的善性。《中庸》给出了一种相当完整的君子论,即在“诚”中修身养性。
总的来说,柏拉图的“人皆求善”和孟子的“可欲之谓善”都涉及了的人类生存的善的问题。但是,前者追问真正的善而走向了认识论,后者推论本性之善而走向功夫论。这个差异值得我们重视。在思想史上,它导致了中西哲学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性格,引导着两种相去甚远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