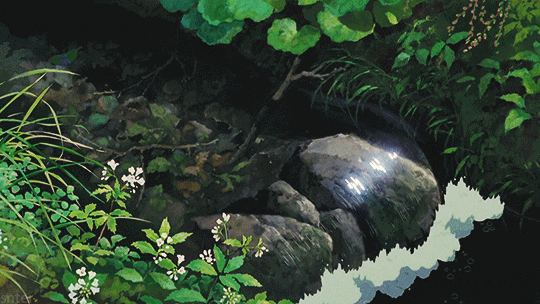
记得曾在什么地方听过一个笑话:一个人善忘。
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务完成后,却找不到自己的腰带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过望,说道:“今天运气真不错,平白无故地捡了一条腰带!”
一转身,不小心,脚踩到了自己刚才拉出来的屎堆上,于是勃然大怒:“这是哪条混账狗在这里拉了一泡屎?”
这本来是一个笑话,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未必会有的。
但是,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涂,却是经常见到的事。

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画家,本来是并不糊涂的。
但是,年过八旬以后,却慢慢地忘事糊涂起来。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认识了,颇能谈得来,而且平常也还是有些接触的。
然而,最近几年来,每次见面,他都会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
从眼镜后面流出来的淳朴宽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其中饱含着疑惑的神气。
我连忙说:“我是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
他点头称是。但是,过了没有五分钟,他又问我:“你是谁呀!”我敬谨回答如上。
在每次会面中,尽管时间不长,这样尴尬的局面总会出现几次。我心里想:老友确是老了!

有一年,我们再次邂逅。
一位有名的企业家设盛筵,宴嘉宾。
当地著名的人物参加者为数颇多,比如饶宗颐、邵逸夫、杨振宁等先生都在其中。
宽敞典雅、雍容华贵的宴会厅里,一时珠光宝气,璀璨生辉,可谓极一时之盛。
至于菜肴之精美,服务之周到,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我同这位画家老友都是主宾,被安排在主人座旁。
但是正当觥筹交错、逸兴遄飞之际,他忽然站了起来,转身要走,他大概认为宴会已经结束,到了拜拜的时候了。
众人愕然,他夫人深知内情,赶快起身,把他拦住,又拉回到座位上,避免了一场尴尬的局面。
前几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富丽堂皇的北京图书馆的大报告厅里举行年会。
我这位画家老友是敦煌学界的元老之一,获得了普遍的尊敬。
按照中国现行的礼节,必须请他上主席台并且讲话。但是,这却带来了困难。
像许多老年人一样,他脑袋里刹车的部件似乎老化失灵。
一说话,往往像开汽车一样刹不住车,说个不停,没完没了。会议是有时间限制的,听众的忍耐也绝非无限。
在这危难之际,我同他的夫人商议,由她写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往他口袋里一塞,叮嘱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礼如仪的常规。
然而他一开口讲话,稿子之事早已忘之九霄云外,看样子是打算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照这样下去,讲上几千年,也讲不到今天的会。
到了听众都变成了化石的时候,他也许才讲到春秋战国!我心里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针办。

我请他的夫人上台,从他的口袋掏出了讲稿,耳语了几句。
他恍然大悟,点头称是,把讲稿念完,回到原来的座位。于是一场惊险才化险为夷,皆大欢喜。

我比这位老友小六七岁。
有人赞我耳聪目明,实际上是耳欠聪,目欠明。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我脑袋里的刹车部件,虽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点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铭是:老年之人,刹车失灵,戒之在说。一向奉行不违,还没有碰到下不了台的窘境。在潜意识中颇有点沾沾自喜了。
然而我的记忆机构也逐渐出现了问题。
虽然还没有达到画家老友那样“神品”的水平,也已颇为可观。在这方面,我是独辟蹊径,创立了有季羡林特色的“忘”的学派。
我一向对自己的记忆力,特别是形象的记忆,是颇有一点自信的。
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至今记忆犹新,招之即来。
显现在眼前、耳旁,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移到纸上,即成文章。

可是,最近几年以来,古旧的记忆尚能保存;对眼前非常熟的人,见面时往往忘记了他的姓名。
在第一瞥中,他的名字似乎就在嘴边、舌上。然而一转瞬间,不到十分之一秒,这个呼之欲出的姓名,就蓦地隐藏了起来,再也说不出了。
说不出,也就算了。这无关宇宙大事、国家大事,甚至个人大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而且脑袋里断了的保险丝,还会接上的。
些许小事,何必介意?
然而不行,它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像着了魔似的,走路、看书、吃饭、睡觉,只要思路一转,立即想起此事。
好像是,如果想不出来,自己就无法活下去,地球就停止了转动。我从字形上追忆,没有结果;我从发音上追忆,结果杳然。最怕半夜里醒来,本来睡得香香甜甜,如果没有干扰,保证一夜幸福。
然而,像电光石火一闪,名字问题又浮现出来。古人常说的平旦之气,是非常美妙的,然而此时却美妙不起来了。
我辗转反侧,瞪着眼一直瞪到天亮。其苦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不知道是哪位神灵保佑,脑袋又像电光石火似的忽然一闪,他的姓名一下子出现了。
古人形容快乐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差可同我此时的心情相比。
这样小小的悲喜剧,一出刚完,又会来第二出。
有时候对于同一个人的姓名,竟会上演两出这样的戏,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

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老了。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对我来说,并不难得,我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然而忘事糊涂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我认为,有的,而且很大。
自己年纪越来越老,对于“忘”的评价却越来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的水平。
苏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他是把悲和欢、离和合并提。然而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
这是深有体会之言。
悲总是多于欢,离总是多于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赋予人类以“忘”的本领——我宁愿称之为本能——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么多的悲和离的重压下,能够活下去吗?
我常常暗自胡思乱想:造物主这玩意儿(用《水浒》的词儿,应该说是“这话儿”)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严肃,又油滑;既慈悲,又残忍。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话真说到了点子上。

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
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像初产生时那样剧烈残酷地折磨着你。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
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
因此,我必须给赋予我们人类“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儿大唱赞歌。

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圣人、贤人、哲人、诗人、阔人、猛人、这人、那人,能有这样的本领呢?
我还必须给“忘”大唱赞歌。试问:如果人人一点都不忘,我们的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
遗憾的是,我现在尽管在“忘”的方面已经建立了有季羡林特色的学派,
可是自谓在这方面仍是钝根。
真要想达到我那位画家朋友的水平,仍须努力。
如果想达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个笑话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我并不气馁,我并没有失掉信心。
有朝一日,我总会达到的。
勉之哉!勉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