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大益文学,作者不一
谈到俄国文学,一座绕不过的高山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小说《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群魔》故事原型是1869年发生在莫斯科的著名“涅恰耶夫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旁听生,在国外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相识。回到莫斯科后,建立起反政府秘密组织“人民惩治会”,并建立了几个秘密“五人小组”,小组成员多为学生。他的专制与独裁引起了小组内部诸多不满,使得小说人物沙托夫的原型伊万诺夫想要退出组织。最后在涅恰耶夫的煽动哄骗下,小组成员由于害怕伊万诺夫告密而暗杀了他。
小说主要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个真实事件展开的,但更为深刻和沉重,描写了上帝缺席后,一群在善恶模糊地带游荡、在虚无主义中徘徊的荒谬而痛苦的灵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群虚无主义者,本文中笔者主要想聊聊小说中的两位自杀者——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
自杀是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也是古今中外诸多文学著作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学意象。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掷地有声地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不少自杀者形象,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以及小说《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便认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不可否认,这样的思想具有一种崇高的超越性,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人之神性的体现,就如纳博科夫在其小说中提到:“一个下决心要自杀的人就是一尊神。”自杀的确可以视为人对神的挑战与反叛,神是不能自杀的,因而自杀的人就做到了神不能做到之事,这也是自杀这一行为哲学意蕴的一种体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是在深渊与神性的彼此蚕食中思考这个问题的,因而他笔下的自杀者有着更为复杂的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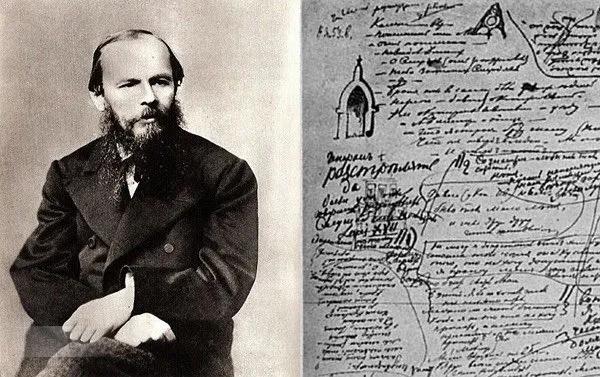
基里洛夫
基里洛夫在《群魔》中所占的篇幅不算多,但他对于自杀的看法以及自杀前与韦尔霍文斯基的对话却十分经典,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个非常突出和典型的自杀者形象。基里洛夫是一位信仰无神论的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秘密组织的一位成员。但他的任务是当组织中的人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当局追捕罪犯时,他便以自杀出来顶罪。在与小说叙述者“我”的聊天中,基里洛夫就有谈到他对于自杀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因为人们怕死而引起的疼痛,认为谁若能战胜疼痛和恐惧,谁就可以成为上帝。“任何一个想要得到最大自由的人,他就应该敢于自杀。谁敢自杀,谁就能识破这骗局的奥秘。此外就再不会有自由了;这就是一切,此外一无所有。谁敢自杀,谁就是神。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到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一切。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一次也没有。”欧茨认为基里洛夫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上帝,一个勉为其难的牺牲者”。在基里洛夫的话语中,他是在以自杀证明自己超越集体意志的个人意志,并彰显自己的绝对自由意志。“我必须开枪自杀,因为我能完全、彻底地为所欲为的顶点就是自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自杀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正如尼采那声惊世骇俗的“上帝死了”一般,基里洛夫似乎在以这种方式朝自己的上帝开枪,并使自己成为新的上帝。
他是否真是这样一位反叛上帝的尼采式人物呢?笔者认为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十九世纪许多俄国作家笔下人物都逃脱不了虚无主义的内核,这些虚无主义者无不行走在自欺的荒野之上,以求内心安宁。基里洛夫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位虚无主义者,他的虚无主义思想在他自杀前与韦尔霍文斯基的对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自杀行为中更是包含一种自欺。究其缘由,大概正如伊琳娜·帕佩尔诺所认为的,基里洛夫深陷二律背反——“对上帝存在着的道德需求和对上帝不存在的经验认识之间的二律背反”。他不能面对没有上帝的荒谬世界,却又无法信仰上帝,残酷虚伪的世界需要上帝,于是他选择自杀成为上帝:“对我来说,没有比没有上帝更高的思想了……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在世界史上,只有我一个人头一次不愿想出个上帝来。”他为自己的自杀披上了超越性的外衣,但讽刺的是他的自杀实际上在为他所蔑视的韦尔霍文斯基这类革命者的罪恶服务。
同为俄国作家的契诃夫也在小说中描写了一批自欺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或是在对过去的模仿游戏中维持着脆弱的记忆外壳,或是将未来置于超越性之上,并将超越性完全建立在仪式化的行为之上,以此来完成抵抗虚无的自欺。基里洛夫的自欺有所不同,他的自欺建立在他的自杀逻辑之上,他将自杀视为一种绝对超越性的行为,他有着似乎接近神性的自杀逻辑,却用自己的自杀来包庇杀人犯,让他眼中如此伟大的自由意志去成全一个卑鄙罪恶的谎言,何其讽刺。他紧紧抓住自杀这一行为的哲学性与神性,来彻底否认现实的一切,推翻现实一切,以此试图逃离死亡与现实的虚无带来的恐惧。但事实上他此举反而将现实与自我都更加虚无化了,他没有变成上帝,虚无与荒诞反而成为了新的上帝。正如斯捷潘诺维奇形容他的,他被自己的思想吃掉了。同时他以完成秘密组织的任务为由不断延宕自杀,更是将自杀这一行为不断变成他心中成全自我神性的一种纯粹仪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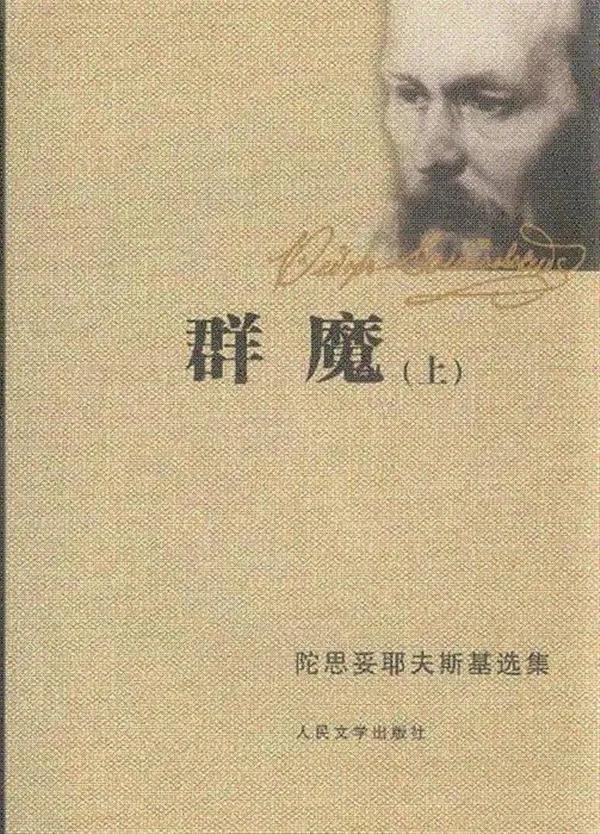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人到底能不能成为上帝?面对这个问题,大概首先需要谈到一个在我们的文化里不太熟悉的话题:现代哲学语境下,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舍斯托夫在《钥匙的统治》中指出:“当人们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时才转向上帝。”加缪更是指出,在舍斯托夫的思想里上帝其实是“记恨的,可憎的,不可理喻的,矛盾百出的”,“上帝的伟大,在于叫人摸不着头脑;上帝的证据,在于不通人情世故”。也难怪尼采会高呼上帝死了,转而发出虚无主义的叩问:人可否毫无信仰地活着?那么人真的能成为上帝吗?当人失去一切可以依托和信仰的东西,失去一切限制,超越一切神圣性,人就会成为上帝吗?还是会在精神边界的荒原上被一种毫无限制的虚无所吞噬?笔者也无法回答这个横亘千百年的叩问。但或许第二位自杀者斯塔夫罗金触及了这个问题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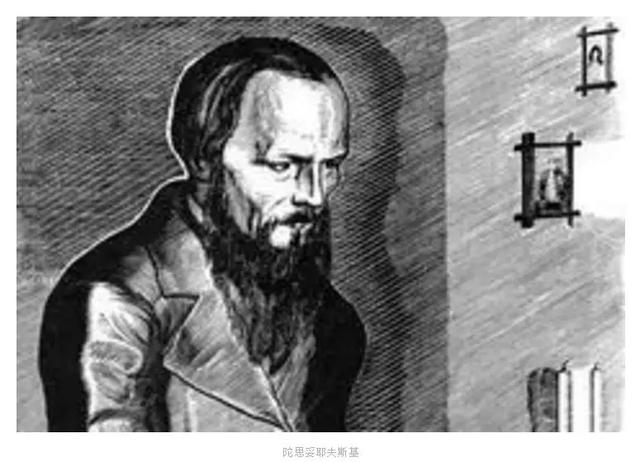
斯塔夫罗金
斯塔夫罗金是与基里洛夫完全不同的自杀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群魔》中真正的主角,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群魔》中的其他人物只是展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载体,“而(他)对斯塔夫罗金的了解却如同了解恶与毁灭”。在小说中,斯塔夫罗金似乎是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解构世间一切的概念,不在乎善恶,对爱与恨都保持冷漠,对生活中的一切人与事都麻木不仁。他像是超越一切概念的,彻底无依无根的绝望漂泊者,漂泊在深渊与神祗那一线之隔间。小说的描写中斯塔夫罗金是一位风流倜傥、潇洒俊美的贵族男子,所有人都迷恋他,韦尔霍文斯基视他为偶像,视他为上帝,认为他就是新的真理。所有人都爱他,又都恨他,他似乎成为了一个被架构起来的虚无的上帝。但他又是一个绝对矛盾的人物,所有的悖论似乎都在他身上聚集。
你当然不会说他是一个好人,他四处拈花惹草,干尽苟且之事,害死过不少人,强奸了一位幼女,并间接造成了她的自杀。可同时,你又很难说他是一个恶人。因为他所有的恶行都具有一种表演性,这个人物的荒诞性恰恰在于他与他所呈现出的行为中间有一道很深的裂痕,他一边施恶,却一边审视自己的恶,甚至以这种审视为快。有如他自己提到的,他人生中许多耻辱、卑鄙和可笑的经历除了激起他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常常让他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快感,“我在偷东西时就会感到一种狂喜,因为我意识到我这个人竟会卑鄙下流到这种地步。我喜欢的不是卑鄙下流,但是我喜欢因痛苦而意识到我卑鄙而出现的狂喜”。他行为的表演性让他与自身存在,甚至整个世界的存在都隔着一层解构的深沟。他永远在对岸观望,但他的观望又不是纯粹的冷漠,而是一种自我折磨。在小说后半部分他交予神父的自白信中,他也呈现出一种忏悔的表演。神父这样形容他的叙述:“在您的叙述中,有些地方被您的措词强化了;您似乎在欣赏您的心理,而且抓住每个枝节不放,您只想用您心中原本没有的冷酷无情来使读者惊叹。”不同于狄德罗《拉摩的侄儿》中的拉摩,借忏悔的表演实际上在为自己洗脱罪恶。斯塔夫罗金借忏悔完成一场审美和精神意义上的表演,实际上却是一种自戕式的救赎。他不断放大自己的恶,以求得一种精神平衡。
在对斯塔夫罗金的描写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让笔者印象深刻。在他强奸了未成年小女孩马特廖莎并猜到马特廖莎会自杀时,小说有一段斯塔夫罗金对当下那刻所感所见极其细微的描写。他听到了一只苍蝇在头顶嗡嗡叫,听到了窗外院子里驶进一辆大车,听到院子另一扇窗户里住着的裁缝大声哼唱小曲。最后他看到了洋绣球叶子上的一只很小的红蜘蛛。诸多不相关的生动细节充斥着他的感官。但恰恰是这不相干的细节成为了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完美虚无主义外壳上的一道裂缝。这个小蜘蛛扎根在他心里,连同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一起。这些细节成为了他的痛苦,成为了他心里的幽灵。以至于在很多年后,他在希腊列岛做了一个美妙的梦,然而在梦的最后,他又看到了那只小蜘蛛:“但是忽然在那明亮耀眼的光束中,我似乎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它渐渐变成一个形体,蓦地,我清楚地看到一只很小的红蜘蛛。我马上想起它就在洋绣球的叶子上,那时候也是夕阳西下,一束斜辉照进了窗户。好像有什么东西刺进了我的胸膛……”
最后斯塔夫罗金的自杀实际上也是对这一细节的回应,他一辈子都在找寻弥合这一裂缝的救赎之道,可他没有任何信仰,一直漂泊在一切精神的边缘地带,于是只能在无数疯狂荒诞的行为中游荡。基里洛夫的自杀表面上是崇高的,但实际上是虚无的,斯塔夫罗金则相反,他的自杀表面上是令人诧异的甚至荒唐的,连他自己都说:“我害怕自杀,因为我害怕表现出舍己为人。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骗局——是无尽无休的骗局中的最后一个骗局。”但他的自杀却反而触碰了崇高领域。《圣经·新约》中有描写一根扎进人肉体的刺,一根不断攻击人,提醒人不要自高的刺。克尔凯郭尔一生都在抚摸这根刺,不断以这根刺来唤醒思想里的痛,“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可见,斯塔夫罗金的心里也有这样一根刺,而那个小蜘蛛就是这根刺。这根刺让他的种种荒诞行为变成了精神苦修。因而他是最荒诞最虚无的人,是最蔑视上帝以及世间一切的魔鬼,却又成为了最接近上帝的圣徒。

回到题目中的问题:谁敢自杀,谁就是神吗?
笔者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给出答案,他笔下的自杀者似乎也都不会是能够成为答案的人物。无论是想要自杀成为新上帝的基里洛夫还是被韦尔霍文斯基视为上帝的斯塔夫罗金,他们都在失去上帝的精神荒原与善恶边界痛苦摸索着、徘徊着,虽然他们自称什么都不信仰,却依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寻求解救之道。在斯塔夫罗金与吉洪神父的对话中有一段十分有趣:
“你信仰上帝吗?”斯塔夫罗金忽地贸然问道。
“信。”
“不是《圣经》上说,只要你信,命令这座山移开,它就会移开吗……不过,这全是扯淡。然而我终究想好奇地问一下:您能不能移动山?”
“上帝吩咐,我就能移开。”吉洪低声而又克制地说,又开始低下了眼睛。
“嗯,这不等于上帝自己在移开吗。不,我是说您,您,因信仰上帝而赏赐您?”
“也许我不能移开。”
“‘也许?’这倒不坏。为什么您要疑惑呢?”
“因为我不完全信。”
……
“既然不完全信仰上帝,那可不可以信仰魔鬼呢?”斯塔夫罗金笑了起来。
“噢,太可以了,而且常常如此。”吉洪抬起眼睛,也微微一笑。
“我相信,您认为这样的信仰毕竟比完全不信要强……噢,您这牧师啊!”斯塔夫罗金哈哈大笑。吉洪又向他微笑了一下。
“相反,完全的无神论比世俗的淡漠要强。”他愉快而朴实地加了一句。
“啊,原来您是这样。”
“完全彻底的无神论者与达到完全彻底的信仰仅一步之差(就看他能不能跨越这一步了),而一个淡漠的人则什么信仰也没有,除了恶劣的恐惧。”
可以看出,即使是宣称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在乎的斯塔夫罗金也不断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摇摆,他说着不信仰一切,却还是好奇着上帝是否真的能让人移开一座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正是俄国十九世纪那个动荡的年代,新旧时代的交替撕扯着普通人的灵魂,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更是让人们的精神生活彻底陷入一种琐碎的虚无之中,信仰的荒芜啃噬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虚无主义。但许多虚无主义者似乎只是将无信仰状态作为回避精神虚无的一种方式,他们无法在理性上做到不去试探自己的神,却也无法真正接受一个完全无信仰的精神世界,他们都不是上帝,也不会是上帝,但他们都是撕扯着的、反抗着的苦修者。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依然令人触动、震撼,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在触摸一些深刻的人性内核:人的自由、人的信仰,以及终极问题——人的存在。我想,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