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嘉映(1952—),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并留校任教;1983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主要专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象》、《哲学科学常识》、《思远道》、《泠风集》、《从感觉开始》等,译著有《哲学研究》、《存在与时间》、《哲学中的语言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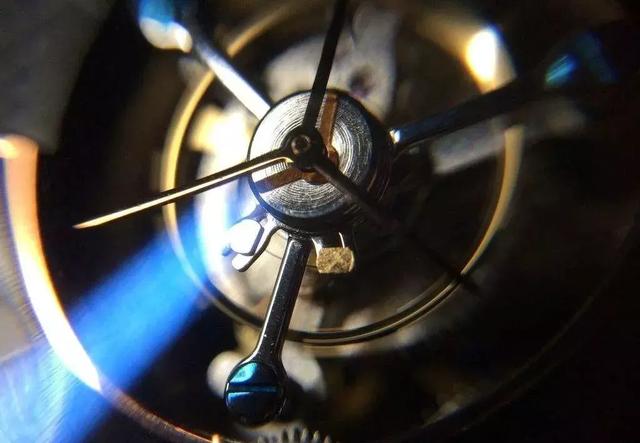
存在(Sein)同存在者(dasSeiende)有别。存在是最高的普遍性,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但存在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因为族类是用来区分在者的,所以,从族类上说,无所不包的普遍性没有意义。存在又是不可定义的,无论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定义,都会把存在弄成了存在者。最后,存在是不言自明的:存在就是存在,无法证明亦无须证明。但康德曾说:哲学家的事业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
但如何追究呢:存在不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不是某一类存在者的抽象共性,也不是存在者的一部分或属性。所以定义法、归纳法、演绎法,都不中用。我们简直不可能离开存在者谈存在,那就得找出这样一种存在者来:对它来说,存在本身是首要的,至于作为什么东西来存在则是次要的。人,就是这种存在者。人不同于其他存在者,因为人在他的存在中同存在本身打交道。只要人存在着,他就对他的存在有所作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就对存在有所领悟,无论明确还是含混。
如果人同他的存在不发生关系,人就不存在了。唯因人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悟、有所作为,人才存在,人才“是”人。人的这种存在称为生存(Existenz)。过问自己的存在是人的特点,追究存在就必须从人着手。
如何了解人?当然要就人的基本情况来了解人。人的基本情况就是——人生在世(In-der-Welt-Sein)。人同世界不能一刻分离,离开世界就谈不上人生。因此,人生在世指的就不是把一个独立于世界的人放进一个世界容器中去。人生在世指的是人同世界浑然一体的情状。在世就是烦忙着同形形色色的存在者打交道。人消融到一团烦忙之中,寓于他所烦忙的存在者,随所遇而安身,安身于“外”就是住在自己的家。人并不在他所烦忙的事情之外生存,人就是他所从事的事业。
传统认识论独独见不到这种浑然天成的生存状态,结果提出了“主体如何能认识客体”这样的蠢问题来。这个问题暗中先行设定了一个可以脱离世界而独存的主体。然而,存在的天然境界无分主客。首先是活动。活动中就有所体察。认识活动只是存在的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次级的存在方式,它把所体察的东西当作静观的对象来作一番分析归纳,这才谈得上各有族类、界限分明的物体。
人对面是种种物体,人自己也成了众物体中的一个物体。于是,生存碎裂成主体、客体等残肢断片,而认识却无能把他们重组为生命,倒反来问“主体能否超越自身去认识客体?”甚至“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先就把存在局限在一部分物体即主体中,存在自然达不到客体了。
但由生而在世的人来提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毫无意义。我们在烦忙活动中与之亲交的世界才是真的世界,知识所描绘的世界则是智性化了的世界残骸。人不在“主体”中,而在世界中,在他所从事的事情中,人于何处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有所领悟,他就于何处实际生存。为了避免把人误解为一个主体物,宜把人称作“存在于此”,或“此在”(Dasein)。
人作为此在不是孤立的主体,人溶浸于世界和他人之中。同样,他人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主体。人都是此在。而就人溶浸于他人的情况来看,此在总是共同此在(Misdasein),在世总是共同在世。即使你避居林泉,总还是一种在世,你的存在依旧由共同在世规定着。共同在世并非指很多孤立的主体物连陈并列,遗世独立也不是指无人在侧。共同在世提供了特立独行的背景和可能。大隐可隐金门,这是在很多人中独在,他人这时以冷漠的姿态共同在世。“在人群和喧嚣中随世沉浮,到处是不可共忧的、荣华的奴仆,这才是孤独!”(拜伦语)
实际上,人生所在的日常世界就是这种炎凉世态。在日常生活中,此在总得烦神与他人打交道。人们无情竞争、意欲制胜,结果都要被他人统制——被公众的好恶统制。“一般人”(das Man)实施着他的真正独裁。“一般人”如何做、如何说、如何喜怒,此在就如何做、如何说、如何喜怒。甚至“一般人”如何“与众不同”,此在就如何与众不同。每个人的责任都被卸除了,却没有哪个“一般人”出面负责,因为人人都是一般人,人人都要一般齐。
这个“一般齐”看守着任何挤上来的例外。一切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草创的思淹没在人云亦云之中,贪新骛奇取代了特立独行的首创精神,不知慎重决定自己的行止,只一味对事变的可能性模棱揣度——这些东西组成了此在的日常生存模式:沉沦。沉沦并不是一种堕落。从没有一个纯洁的人格堕入尘寰那回事。
人总沉沦着。人的日常存在寓于日常世界,从日常世界来领悟自己。但领悟自己并非是对一个固定空间中的现成事物的认识。人首先在现身于世之际领悟自己。人活着,虽然人们不知为什么。此在在,而且不得不在,这一现象首先在情绪中开展出来。
情绪是基本的生存状态之一。哲学却一向轻视情绪。虽然人生在世总带着情绪,甚至静观认识也带着情绪;虽然情绪比认识更早地领悟着存在。情绪是此在的现身: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此在已经在此。至于对情绪的反省认识,则不过浮在存在物的表面上打转,达不到情绪的混沌处,达不到存在的深处。
情绪令此在现身,把此在已经在此这一实际情况显露出来。只要人存在着,就不得不把“已经在此”这一实际承担起来,无论他是怨天尤人、随波逐浪,抑或是肩负着命运、敢作敢为。存在哲学把这种无可逃避的生存实际称为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人并不创造存在,人是被抛入存在的;人由于领悟其存在而得以存在。人看护着他的存在。
最根本的情绪是畏,因为畏从根本上公开了人的被抛状态。畏不同于怕,怕总是怕具体的坏事,而畏之所畏者却不是任何存在者。其实,当畏来临,一切存在者都变得无足轻重,只剩下一片空无。
怯懦的世人怕直面空无,唯大勇者能畏。此在日常沉沦着,他做工、谈情、聚闹、跑到天涯海角去游冶。他在逃避:逃避空无,逃到他所烦忙的事物中去,逃到使他烦神的一般人中去。这却说明,他逃避的东西还始终追迫着他。他到底逃不脱人生之大限——死。
死就是空,畏就是直面死亡。畏从根本处公开了被抛状态:人归根到底被抛入死亡。生向着死。躲避死,也依然是沉沦着向死而在。存在同死亡联在一起;生存之领悟始于懂得死亡。死亡张满了生命的帆,存在的领悟就是从这张力领悟到存在的。
人因他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而得以存在。鲜明或含混地领悟着方生方死的背景,人来筹划他的存在。人永远在可能性中。人不是选择可能的事情,人所选择的是他本身。人是什么?那要由他自己去是。正因为人就是他所将是的或所将不是的,所以他才能说:成为你所是的!存在的领悟,存在的筹划,即人的生存本身,永远领先于人的现成状态。人在成为状态之际已经超越于状态了。
所以人只能说:“我是”,而说不定“是什么”。浮士德不能喊出“请停留一下”,一旦停留,他的生存就完结了。
于此可以提出存在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存在先于本质(der Vorrang der Existenztia vor der Essentia)。拘于字面,这话可译成:是,先于所是。这意思是:如果竟谈得上人的既成状态,那么这一既成状态也必须从人的不断领先于自身的能够存在(Seinkoennen)得到了解。即使只为保住现成状态,也总要从可能性方面来作筹划。而在由畏公开出来的抛向死的境况中,不断领先于自身的存在之筹划就突出醒目了。此在先行到死来筹划他的在此。
而死亡是每个人自己的无可替代的可能性,所以,领悟着死来为存在作筹划,就是从根本处来筹划各种可能性了。进入畏之境界,万有消溟,人也就无存在者可寄寓;唯悟到人无依无托,固有一死,才能洞明生存的真谛:立足于自己来在世。
人本身就是可能性。他可以选择自己:可以获得自己,也可以不获得自己,或者失去自己。唯因人天然可能是本真的人,才谈得上他获得自己或失去自己。立足于自己来在世,这一决断令人返本归真。但本真的存在并非遁入方寸之间,或遗凡尘而轻飏。只要人存在着,他就总在世界中,总烦忙于事物,烦神于他人,总对他的存在有所领悟、有所作为。
决断反倒是要把人唤出,挺身来为他的作为负责,脱乎欺惘,而进入命运的单纯境界。唯畏乎天命的大勇者能先行到死而把被抛状态承担起来,从而本真地行于世,有其命运。无宗旨的人只在偶然事故中打转,而且他碰到更多的机会、事故,但他不可能有命运。综上所述,可见此的存在包括三个主要环节:1.领悟着的筹划;2.被抛入状态;3.沉沦。
第一点是决定性的。如前所述,若对其存在无所作为,此在就丧失其存在了。而筹划总是先行于自身从可能性方面来筹划。此在从可能性、从“先行到死”,来归自身。换言之,此在首先在将来中。“是,先于所是”。没有将来的能够存在,就谈不上存在的既成状态。
人对其存在有所筹划,但他不创造存在。人是被抛入存在的。人已经在了。筹划就是从可能性方面来把存在的被抛状态承担起来。“已经存在”是从将来的可能方面出现的:此在在将来仍如其曾在;我将依然故我。所以,此在的曾在,共同此在的历史性,都是从将来方面展开的。
人从将来的筹划承担起他的历史而寓于当世。人只要存在,就必烦忙种种存在者,他正沉沦于存在者之中,从而把筹划着的历史性现在化了。通俗观念沉沦于当前而不自知,于是它把此刻突出出来,把生动的时间性敉平为一连串前后相继的此刻。这种“一般齐”的时间之流对生存漠不关心,只不过在我们身外均匀流逝着。存在哲学则主张,时间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将来,时间性对存在来说性命攸关。死生亦大矣,而死生的意义都要靠时间来说明。时间烛照着生存,照明了人的生死整体——烦(Sorge)。
烦是生存结构的整体。这个生存整体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呈现出来的。若吾生也无涯,人如木石悠悠无尽,又何烦之有?在烦中,将来突出出来作为生存的首要意义。为现在烦,为历史烦,归根到底是为将来而烦。于是烦也就指明了生存整体的那种无功无就,死而后已的情形。
《存在与时间》立旨以人为本来阐释存在。人就在而且就是人。没有一条神诫或自然法则指定我们应当怎样是一个人,天上地下并无一处把人性规定下来。人性尚未定向,它始终还在创造着。人性既非制成品,也不是尚待实现的蓝图,那我们何从察知人性呢?——我们已经在了,在种种努力之中;已经烦着,并领悟着烦。烦在设身处地的情绪中现身,在筹划中领悟,在语言中交流,在存在中展开着存在本身。但什么都无法把定烦。
烦永不是定形的局面。烦之领悟也不是。人性问题或者存在问题的答案,不似方程的根,求出来便摆在那里。思领悟着在,并始终领悟在。它不提供“结论”,而只是把存在保持在“存在的疏明”之中。








